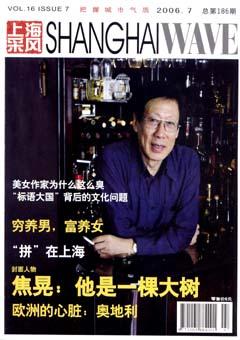維權過度之弊
林德清
“維權”一詞現在很時髦,好像一夜之間,人人明白了自己無上無邊無限的權力,誰不把咱的權力放在眼里,立刻讓你法庭上見。至于權力有還是沒有,多大還是多小,則很少有人精算和論證。以至于弄得一說維權,大伙就都興奮起來,而提起官司的那方作出勝券在握狀,只等著捷報傳來。
殊不知,已經潛伏著維權過度的險情。
單說幾樁知名度頗高的近案。一是霍元甲的后代欲告李連杰,二是陳永貴的兒子狀告史學家吳思。前者風聲大雨點小,暫時還沒有看到判案。后者二審已下,不能說蓋棺論定,也至少塵埃落定。以史學筆法撰寫傳記的學者吳思用翔實的材料寫成的《毛澤東的農民——陳永貴》因其中幾個細節讓永貴大叔的家屬覺得有傷顏面,遂挺身“維權”。哪怕有九十九處是“正面”的,只要有一處“負面”,立刻就維權沒商量。而堂堂法庭面對這文化含金量甚高且影響到國家人文建設的案例,卻極少垂詢真正有見地的公共知識分子或者史學專家,以簡單的是與非或有與無的質詢一錘定音,弄得有識之士大鳴不平。
先是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挺身而出,章以《往事并不如煙》確立了傳記文學大家的地位,她對吳思的敗訴痛心疾首,在“大驚”之余,對吳思說:“這是個原則問題,我是堅決支持、同情你的。我能為你做些什么?你需要我做些什么?有陸健東(撰寫著名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作者)麻煩于昨,有吳思敗訴于昨,誰將敗訴于明?可能是我,可能是其他的人。法律和知識界應該聯合起來,抵抗這種濫施的權力。”在她看來,吳思有寫陳永貴的權力,陸健東也有寫陳寅恪或別的什么的權力。現在家屬一告狀,法院就判作者敗訴,又是賠款,又是登報道歉,學者出示的大量證據,法院輕率地棄之一旁,更談不上聽取學術界內行的意見,這是對史學的極大傷害。著名學者雷頤也在北青報上撰文指出,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史學家還要面對的困境之一是人物研究經常會遭到傳主親屬、后人的種種“干擾”,他們總是通過種種途徑、想方設法要抹去傳主的不足和缺欠,非把傳主塑造成“樣板戲”般的“高大全”不可;如果可能,甚至干脆“封殺”令他們不滿、不快乃至憤怒的史學家的研究成果。他認為,歷史學家吳思的 “敗訴”,就是這種“怪現狀”的再次表現。倘循此為例,研究者將動輒得咎,很難對近現代的歷史人物進行客觀深入的研究。這樣,對歷史人物的“研究”將不得不“隱惡揚善”,充滿溢美之辭;人物研究將蛻化為單純的歌功頌德樹碑立傳,成為“忠孝節義”的旌表,學術研究將大受損害。
學術研究是一個國家文化建設、文化積累的重要方面,法制建設的作用之一就是要為學術的發展提供相應的制度保障,為學術的繁榮創造適宜的條件和環境,而不是相反。沒有學術的繁榮發展,還談何民族、國家的精神文明建設,談何民族、國家的文化積累和繁榮發展!此案讓人不由想起那位受到宮刑依舊直筆寫史的司馬遷,假如司馬遷被形形色色的“維權者”(那時的“維權者”可是操持著史記官的性命呀)乃至其后人所嚇倒,那么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史記》一定是歌功頌德的文字牌坊,價值盡失。假如到了今天,我們還不得不悲壯地重提司馬遷,并且號召史學家隨時準備“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豈不嗚呼哀哉!
所謂維權過度之弊,就是因錯誤劃分權力界線而損傷人文環境。誰的權力需要維護?誰的權力本不存在?能夠一錘定音的人一定要搞清楚,落錘之前務必垂詢真正的有識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