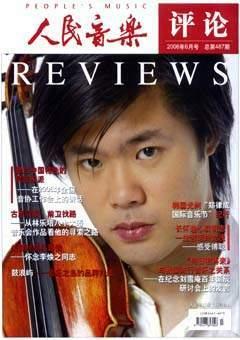長懷逸心淡明志 一生苦詣終覺淺
張 棟
傅聰,一個在中華大地上涌動了近半個世紀的名字,他曾使多少人“以懷明志”,又曾使多少人“望塵莫及”。“要知修行讀《家書》,常使斯人淚滿襟”,它表達了多少仁人志士一生的夢想和追求。
當時踏著秋寒的暮靄來到我們中間,使我們每一個追夢之人非常近距離地感受他,聆聽他的教誨,享受他的藝術人生。
一、用生命解讀音樂,用音樂慰藉蒼生
在音樂界乃至整個文化藝術界,半個世紀以來,傅聰是接受各種訪談和采訪最多的思想家和鋼琴家,光有文字記載就不下百萬字,《傅雷家書》在中國可稱之為老百姓家中書柜案頭的一本“國書”,它影響了中國幾代知識分子,它的人文精神一直在激勵著今天的人們為之勵志和進取。
一個民族優秀的資質,是以先人和今人經歷的痛苦和戰勝痛苦的能力所界定的,要理解這一切,需要一生感情的付出和播種,而傅聰堪稱付出和播種感情的睿智之人。幾十年來,他感情深處背負著博大深邃的東方文化,靈魂深處又時時承受著西方基督文明的沖撞,內心還要熬煎著塵埃及世俗帶給他的種種痛苦。面對一個70歲老人敏捷的肢體和他精髓的講解,聽著他琴鍵上流水般的聲音,常使我在他神采飛揚的講座中思緒萬千,一個以三點一線(琴房、音樂廳、飛機場)占據了一生大部分時間的人,一個在東西方藝術文明的長河中不停飄泊的人,一個一生坎坷的人,是什么力量在支配著他如此“忘我”,從他以下追及一生的鋼琴藝術生涯中,我們不難看出傅聰“憂國、憂民、憂藝術”的赤子情懷。
傅聰是一個言語較少多為“靜思”的人,只有在音樂的對話及交流講座中,我們才可以看到一個真正而又單純的傅聰;才可以看到一個滔滔不絕、激情四射、文化淵博的藝術大師的真正面貌。大師一生我行我素,是一個駕馭自我能力很強的人,唯獨面對音樂,才可看到他一顆虔誠的心靈,他常說:“我是一個音樂的奴隸。”亨德爾、貝多芬、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等等,他們的音樂,帶給我們多的是美的感受和心靈間的滌蕩與共鳴,而對傅聰來說,從某種意義則是一種無可名狀的“痛苦”,因為他解讀了他們一輩子。天地間一些未知的東西,在知與不知間是一種追求和幸福,一旦癡迷到“造化”的境界,則是痛苦,因為他讀懂了別人無法讀懂的境界。正如李民鐸對傅聰的評價,他是一個“解天書的圣人”。
傅聰是把中國的文化藝術和哲學與西方音樂藝術融匯并結合得非常完美的人,他的文學造詣和音樂功底同樣的深厚,是一個有著極高學養的文人式的鋼琴家,他的藝術造詣不僅體現在鋼琴上,而且在室內樂及各種音樂風格體裁上都是音樂中人所不敢想象和無法比擬的。我們僅從以下幾位音樂家的影子中就可以捕捉到他博大的美學思想。
肖邦——傅聰用心血追及了一生。可以說在東西方他是最有發言權的人之一,肖邦的瑪祖卡也好,還是《二十四首前奏曲》以及《練習曲》《敘事曲》等等,傅聰都挖掘到了極致,他不僅僅是以“師古人”的美學思想在效仿肖邦,而更是以“師造化”的遐思給肖邦的音樂賦予新的“空”......“靈”......他用“熟讀后主詞”和黃賓虹繪畫中的“故國之情”的意境去解讀肖邦。歐陽修的“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被傅聰認為這是對肖邦最好的寫意。
莫扎特也是傅聰最喜歡的音樂家之一,他常把莫扎特比喻成賈寶玉和孫悟空。他認為在莫扎特的音樂里面有一種大慈大悲,有一顆博大的仁愛之心,赤子之心,非常的細微,所以,從這一點,他很像《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同時,莫扎特又是音樂天賦和才華超群的人,他的音樂千變萬化,如果給他一個主題,他可以想怎么編就怎么編,而且立刻就能編得非常好,這一點真像孫悟空。而且,莫扎特的幽默、俏皮、童真很像中國人,中國人的“天人合一”跟莫扎特有著很多相似之處,而且能入能出。像歌劇《后宮誘逃》中的悲劇美和中國戲劇中的人文美學思想很近似。莫扎特的音樂充滿了人世間無限的想象和詩意,與中國文化有一種內在的聯系,所以,從某種意義上,傅聰認為:中國人應該比任何民族更懂得莫扎特。
貝多芬的音樂那豐滿的樂思和音響在我們的理念中總是有一種悲壯與命運的抗爭。在傅聰的音樂思想中,同是一種抗爭,意義則不同,他認為從這一點倒很像中國的杜甫,他是在和一種人間的世俗與習慣在抗爭,悲憤之中充滿了理想與激情的抗爭,抗爭到了頂點就有一種“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的意境與輝煌,可以說貝多芬多首鋼琴奏鳴曲中可以解讀到許多他的影子。
對于舒伯特,傅聰認為他更像中國的陶淵明,在他的音樂里面體現出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一生的理想和返樸歸真的追求與愿望。德彪西的音樂則更有一種“浩浩風波起”和“白鳥悠悠下”的東方美學境界。
傅聰在音樂上的嚴謹和超脫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他是一位既忠實于原作而又不拘泥于原作的人,在他眼里沒有絕對的“forte”和“piano”,更沒有絕對的“con brio”和“lamentabile”。在講座中他用豐富的樂思和肢體語言,一會兒熱淚放眼笑談每一句樂思,一會兒又依譜循聲細摳每一小節,“輕”與“重”,“快”與“慢”都細化到不能再細,音樂中的閃光點和每一句樂思常常折射出他無窮無盡的美學思想,激情飛揚之處,他天真得忘乎所以,行云沉靜之際,又見他淚眼閉目遐思,顯現出他內心深處無限的“憂愁”,“傷感”和“孤獨”,也只有在此時此刻,我們才可以看到真正的傅聰,才可以看到他飄逸的音樂靈魂,他用這顆飄逸的心慰藉自己,慰藉著每一個善良之心。
二、虛懷若谷勤追日,不憐夕陽轉頭空
26年前,傅聰返回上海的那天,我們很難知道他當時的心情,“平反昭雪”,是當時經歷了浩劫的那個年代利用率最頻繁的四個字,傅聰失去了父母,國人失去了一對善良和為之敬仰的楷模。每每談起《傅雷家書》,傅聰總是避而不談,后來他都盡量不去碰它,因為一看,他整天都無法工作,太傷感了,有時候他甚至覺得這個世界很悲涼。1982年,從他被同時聘為上海音樂學院和中央音院的客座教授那天起,他以一顆赤子之心奔波于大洋兩岸,不停地演出,不停地講學,用音樂這個不朽的靈魂寄托他的哀思和理想,講述著音樂中一個又一個傳奇而富有真情的故事。
傅聰一生建樹頗多,是舉世公認的鋼琴家,但他一生謙遜恭讓,虛懷若谷,從不自滿,父親的一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成了他一生的銘鑒。一個70歲的老人每天還要堅持練琴8小時,最多的時候達到14小時,他的所為使我們深深地感到驚恐乃至汗顏,可以說他對每一個從事鋼琴藝術的人來說,是一種震撼,這在世界上恐怕都是絕無僅有的。一個音他可以在琴鍵上領悟半天,他不由使我想起佛典中“世尊拈花”的故事來,他總是想尋找和領悟那最好最美的感覺,超越自我,超脫靈魂,這種“心齋”已達到了“忘我”的境地。傅聰對音樂的理念,既有“行而不流”的儒家文化的修養,又有“水流心不靜,云在意俱遲”這種虛空、心靜的佛學境界;同時,他又在時時追求一種原天地之美和不在人為,重天然的“道”家理念,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在他思想中非常博大、深遠。
他對鋼琴的癡迷和練琴使雙手傷痕累累,常常戴著手套,有時還要靠打封閉或纏繃帶來維持彈琴,他對物質生活別無所求,常常穿著非常簡便的唐裝,可對音樂的虔誠之心容不得任何蔑視。在北京、西安等地就因為記者的隨意拍照和劇場的不安靜因素,傅聰中斷了演出,他認為,這不僅僅是破壞了音樂,而更嚴重的是侵犯了遠道而來聽他音樂的聽眾之心。他視聽眾為上帝,在上海音樂學院賀綠汀音樂廳,有一次傅聰就坐在我前一排,我就親眼目睹了他由于聽眾的來回走動,作為聽眾的他拂袖而去的事情。傅聰一生淡泊名利,有很多政治文化界的名人和國際音樂大師都是他的朋友,他也常參加一些國際文化交流和國際大賽的評委工作,可是這些對他來說都是過眼煙云。他常以“師古人,師今人,師造化”來銘訓自己,常把自己定在一個很高的標準苦苦修行,從未憐惜過自己,也從不考慮身后之事,科技和物質文明所帶來的成果,他從不獵涉,也不去享受,好像一切對他都是多余的,他有時甚至覺得技術革命所帶來的CD等音像制品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音樂的一種破壞。假如人可以再活500年,我敢斷言,這500年對傅聰來講,除了音樂還是音樂。
三、心底無私天地間,一身傲骨猶悲情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從《傅雷家書》中感受最多的是那句“先為人,次為藝術家,再為音樂家,終為鋼琴家”的思想和教育理念,在這樣一個溫良而有修養的人文家庭里,傅雷告訴人們的首先是立人之本,做一個有修養的人,做一個富有愛心和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尤其是要做一個慎終追遠,明辨是非的人。家之遺風,影響了傅聰的一生,給了傅聰極大的生存空間。就人文修養,傅聰常說:“你彈肖邦可以用唐詩的意境去抒發情感,而明天也可以用古希臘的建筑或雕塑去解讀,不同的修養,不同的文化境界,才能有品位,有追求。”言語間,充分顯示了藝術的“空筐”結構。傅聰正是有了博大的人文底蘊,才使他自如地暢談音樂,使他能平靜地面對許多不公甚至讓他痛心的東西。特別是自己的國家不美好的事情最使他為之痛心,也表現出了他憂國、憂民、憂藝術的拳拳赤子之心。
傅聰是一個有名的敢抒己見,敢正視聽,敢于批判的個性中人,不管怎么尖銳,怎么得罪人,怎么不中聽,他都是實實在在地和盤端出,這種精神和傲骨在當前音樂界乃至整個藝術界中,是難能可貴的,尤其是對一些大師級的甚至一些頂尖級的人物或演奏家,他也是不遺余力地批評指正,不喜歡就是不喜歡,像拉赫瑪尼諾夫,當今演奏大師波格雷利奇等等。對一些國際性的音樂比賽和權威性的國際鋼琴比賽,在他是評委的情況下,也是直言坦誠,不計后果。他恨不能把自己所有的感悟和真情用音樂的方式毫不保留地托付給他人,讓人脫離世俗的偏見和虛偽,多一點真情實感。按老莊之學,叫做任性而行,也叫直道而行。感情真者,性格也必然直率,大師力圖以解讀音樂的心靈,改變其人為虛偽的屬性,使之成為合乎情性、順乎自然的一種純真的人性。
音樂可以興,可以怨,聽亨德爾、海頓、莫扎特的音樂,可以喚起人們樸素而純真的天性,給人以心靈的平衡;貝多芬帶給我們的是悲憤和理想,有時傷感,但仍可以看到光明,可以重塑我們驅散陰暗的勇氣;聽肖邦、門德爾松、德彪西,可以使我們回歸人間多情,憂郁的本性。而聽傅聰彈琴,聽他講學,總覺得是慰藉和澆灌著干涸的心靈,一次又一次喚起我們無數次的激情。一個以音樂為生命的人,以“師今人”的現實主義理念,為我們又垂范著一個“師古人、師造化”的理想之美。
閱盡人間春色秋風,踏遍世上荊棘坎坷。世間美好的山川景色,傅聰的足跡是屈指可數的,而他起伏跌宕的人生閱歷,真可謂荊棘坎坷,當我的筆尖在紙上無數次地落上落下的時候,在我的眼前總是飄動著一雙布滿傷痕的雙手,在黑白琴鍵上抬起落下,當我每每看到他老人家為我題寫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穩重而又滄桑的八個字的時候,總是思緒萬千,眼淚在眼眶不停地旋轉,你一生苦詣還嫌易淺,但天地之大,人生短暫,又何能窮盡?傅聰,我所敬仰和崇敬的人,多么希望您不要再飄泊,回來吧!回到生你養你的土地,因為這里有愛你和尊敬你的人。
后記
2004年下半年,我作為高級訪問學者的身份,赴上海音樂學院學習,恰逢傅聰來上音講學,有幸的是我不僅能近在咫尺聽他彈琴講學,同時還承擔了他講學中一些事務性工作整兩個多月。
曾記得一本《傅雷家書》使我實現了彈鋼琴的夢,又使我懂得了許多做人的尊嚴。兩個月過去了,總是有一種沖動時時撞擊著我,我要把全部的感情和情懷寫出來,雖然是一篇斷言殘簡,但是我不得不以肢解的感受仰視我一生最尊敬的人——傅聰。
同時,我要非常感謝我的老師,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教授、鋼琴演奏家周鏗,他身居國外多少年,是他架起了一座座東西方鋼琴藝術的橋梁,舉辦了許多國際間的鋼琴藝術交流活動,為推動中國鋼琴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在此,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謝和敬意。
張棟 西北民族大學音樂舞蹈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 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