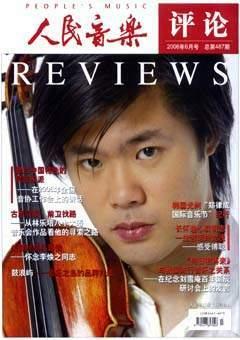《何日君再來》與中國流行音樂之關(guān)系
對于中國人民來說,二十世紀(jì)二十至四十年代是一個比較復(fù)雜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經(jīng)歷了大革命失敗、抗日救亡、八年抗戰(zhàn)、解放戰(zhàn)爭等,因此政治、商業(yè)、殖民等因素必然會對劉雪庵的流行音樂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不可避免的影響,使得他的流行音樂作品顯得錯綜復(fù)雜和撲朔迷離。在如此前提下,要想對劉雪庵的流行音樂作品作出一個盡可能接近客觀、公允的歷史評價,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劉雪庵主要活躍于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樂壇。相應(yīng)的,他的流行音樂創(chuàng)作①也主要集中于這一時期。在此階段,他創(chuàng)作了《早行樂》②《何日君再來》《采蓮謠》《彈性女兒》和《雙雙燕》③等歌曲,引起了當(dāng)時的音樂界和社會的關(guān)注,并得到了褒貶不一的口碑。
對于中國人民來說,二十世紀(jì)二十至四十年代是一個比較復(fù)雜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經(jīng)歷了大革命失敗、抗日救亡、八年抗戰(zhàn)、解放戰(zhàn)爭等,因此政治、商業(yè)、殖民等因素必然會對劉雪庵的流行音樂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不可避免的影響,使得他的流行音樂作品顯得錯綜復(fù)雜和撲朔迷離。在如此前提下,要想對劉雪庵的流行音樂作品作出一個盡可能接近客觀、公允的歷史評價,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鑒于此,本文將嘗試以《何日君再來》一首歌作為切入點,努力從該歌曲和中國流行音樂的四個關(guān)系出發(fā),去走近劉雪庵和中國流行音樂,并試圖作出盡可能接近流行音樂藝術(shù)本身的客觀評價。
與黎錦暉“時代曲”的關(guān)系
今天關(guān)于《何日君再來》這首歌的產(chǎn)生過程已經(jīng)比過去明朗多了。雖然有人說它是“中國版本的《歸來吧蘇連多》”⑦,也有人說它是“美麗頹廢的罌粟花”,但最終在歷史上造成的影響卻和黎錦暉的“時代曲”殊途同歸。
1927年—1936年,是中國流行音樂史上的黎錦暉時代,也是中國流行音樂開始大踏步登上中國音樂的歷史舞臺之時。
在黎錦暉創(chuàng)作的這批“時代曲”之中,當(dāng)以《毛毛雨》《妹妹我愛你》《桃花江》《特別快車》和《落花流水》幾首歌曲最具代表性。客觀地說,這些歌曲歌詞輕佻,音樂格調(diào)不高,在當(dāng)時產(chǎn)生了消極的影響。
然而盡管如此,黎錦暉的諸“時代曲”也并非毫無藝術(shù)價值。他比較注重歌詞的通俗易解,旋律的民族風(fēng)格和朗朗上口,詞曲的有機融合。比起傳統(tǒng)民間情歌,他的“時代曲”做了更進(jìn)一步的嘗試和探索,尤其是考慮到了普通城市市民階層的審美趣味。這些都為他的“時代曲”的傳播創(chuàng)造了條件。
當(dāng)黎錦暉的“時代曲”在社會上流行之時,劉雪庵還是國立音專的一名學(xué)生,但早已步入電影音樂界并開始他的音樂創(chuàng)作。面對輕歌曼唱的《桃花江》《毛毛雨》等“黎派黃色音樂”,他奮筆疾書寫下了如下的話:“僅僅禁止播放是不夠的,應(yīng)該采取積極措施。如征求愛國歌曲,把各地的民歌收集起來,根據(jù)現(xiàn)在的作曲技巧予以改編、整理、發(fā)揮。這不只適合民眾的口味,而且將來可以把握住這種新奇樂風(fēng),創(chuàng)造一派國民音樂,也可以為我國藝術(shù)爭得相當(dāng)?shù)匚弧!?sup>④很顯然,劉雪庵對黎錦暉的“時代曲”是深惡痛絕的。
但正像上文所言,黎錦暉的“時代曲”在藝術(shù)上并非是毫無可取之處。這一點,劉雪庵以自己不久后的音樂創(chuàng)作實踐給予了肯定。1936年他在聽了一場“黎錦暉個人作品音樂會”后,受其中一首歌曲《永別了小弟弟》的曲調(diào)的啟發(fā),不禁浮想聯(lián)翩,對母校和同學(xué)的依依惜別之情涌上心頭,便在歡送畢業(yè)班同學(xué)的茶話會上即興創(chuàng)作了一首探戈舞曲《何日君再來》,從此該曲不脛而走,廣為流傳⑤。后來黃嘉謨?yōu)樵撉钤~后,“新”《何日君再來》借助歌詞的文學(xué)拐杖將原曲的想象空間做了一定程度上的縮小,適應(yīng)了市民階層受眾的欣賞品味。由此可見,黎錦暉的“時代曲”對劉雪庵的流行歌曲創(chuàng)作多少還是有點影響的,也許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連劉雪庵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就這一點而言,1980年《北京晚報》發(fā)起的關(guān)于這首歌曲的討論中的某些觀點也不是空穴來風(fēng):“在三十年代,它是《桃花江》《特別快車》等靡靡之音的繼續(xù)。在烽火連天的全民抗戰(zhàn)中,確實是‘一邊是嚴(yán)肅地工作,一邊是荒淫無恥,《何日君再來》是與前者格格不入的,這正是它能在淪陷區(qū)暢行無阻的根本原因。”⑥
今天關(guān)于《何日君再來》這首歌的產(chǎn)生過程已經(jīng)比過去明朗多了。雖然有人說它是“中國版本的《歸來吧蘇連多》”⑦,也有人說它是“美麗頹廢的罌粟花”,但最終在歷史上造成的影響卻和黎錦暉的“時代曲”殊途同歸,以至于后來劉雪庵自己都不得不承認(rèn):“歌曲中不健康的成分,反映了我當(dāng)時在人生觀上存在的問題。后來這首歌曲被人肆意處理,這不是我的原意,但產(chǎn)生的惡劣后果,卻使我痛心。”⑧
與賀綠汀等進(jìn)步作曲家流行音樂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
打倒“四人幫”已4年了,社會風(fēng)氣起了根本的變化,而且黨中央又公布了《關(guān)于黨內(nèi)政治生活的若干準(zhǔn)則》。但是要想在一個早上肅清十年浩劫時期的習(xí)慣勢力是不可能的。錯劃右派得到改正的劉雪庵也只好默默無言地蹲在他的小屋里,忍受著繼續(xù)向他射來的冷箭。
三十年代不僅僅有黎錦暉的“時代曲”,同樣屬于賀綠汀等進(jìn)步作曲家創(chuàng)作的流行音樂。這也是當(dāng)時中國流行樂壇出現(xiàn)的一個非常特別的現(xiàn)象。
這一時期,賀綠汀等進(jìn)步作曲家一方面創(chuàng)作了《游擊隊歌》《嘉陵江上》(賀綠汀曲)、《抗敵歌》《打回老家曲》(任光曲)、《開路先鋒》《義勇軍進(jìn)行曲》(聶耳曲)等大量的抗日救亡歌曲,另一方面也開始涉足流行音樂創(chuàng)作。正如梁茂春所言:“當(dāng)時的進(jìn)步音樂工作者和專業(yè)音樂工作者都是反對‘黎派音樂的,但他們也吸取了黎派音樂的某些長處,如詞曲的緊密結(jié)合,鮮明的民族風(fēng)格等。他們采用了流行音樂這一形式,創(chuàng)作出許多好的、具有重要意義的作品,并使流行音樂這一體裁也成為當(dāng)時群眾救亡歌詠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⑨
而劉雪庵則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人物。一方面他和賀綠汀同為國立音樂專科學(xué)校作曲系同學(xué),也寫過《長城謠》《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救亡作品,另一方面也寫了諸如《何日君再來》《早行樂》等有著消極影響的流行歌曲。由于這些特殊的原因,他似乎既可以被列入涉足流行音樂創(chuàng)作的進(jìn)步或?qū)I(yè)音樂家之中,也可能會被視為與黎錦暉為伍的流行音樂作曲家。此外,劉雪庵和賀綠汀等進(jìn)步作曲家又都在排斥黎錦暉的“時代曲”的同時,同樣部分地吸取了“黎派音樂”在創(chuàng)作上的長處,如對五聲音階的運用、旋律易于上口、考慮到市民階層的審美需求等等。
盡管直到現(xiàn)在《何日君再來》還存在著眾多非議,然賀綠汀在八十年代的一番話卻又是那么地耐人尋味:“現(xiàn)在,打倒‘四人幫已4年了,社會風(fēng)氣起了根本的變化,而且黨中央又公布了《關(guān)于黨內(nèi)政治生活的若干準(zhǔn)則》。但是要想在一個早上肅清十年浩劫時期的習(xí)慣勢力是不可能的。錯劃右派得到改正的劉雪庵也只好默默無言地蹲在他的小屋里,忍受著繼續(xù)向他射來的冷箭。對一個人的評價必須實事求是,一棍子打倒和全盤肯定都是錯誤的。人們應(yīng)該從嚴(yán)重的錯誤和挫折中吸取教訓(xùn),老老實實按照《準(zhǔn)則》精神辦事,我們的國家才真正會有無限光明的前途。”⑩
與抗戰(zhàn)期間淪陷區(qū)流行音樂的關(guān)系
當(dāng)政治、殖民、商業(yè)、娛樂和藝術(shù)等多種因素紛紛滲透到像《何日君再來》這樣的一首流行歌曲之時,當(dāng)以黃嘉謨{12}為代表的“軟性電影”論者加盟到流行音樂創(chuàng)作隊伍之時,當(dāng)以淪陷區(qū)的小市民階層為流行音樂的主要受眾群體之時,流行音樂作品自然會存在粉飾太平、遠(yuǎn)離社會現(xiàn)實的問題,也自然會誤導(dǎo)受眾“今朝有酒今朝醉”。
1936年后,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風(fēng)起云涌,黎錦暉的“時代曲”逐漸淡出歌壇,取而代之的是抗日救亡的歌聲響徹大江南北。然此時在淪陷區(qū)卻依然能夠感受到流行音樂的脈搏,尤其是在“孤島”上海。至40年代,侵華日軍占領(lǐng)了整個大上海,上海再次成為中國流行音樂創(chuàng)作的中心,并引起歐美流行音樂界的關(guān)注。
這一時期,在流行歌曲創(chuàng)作方面比較活躍的作曲家有黎錦光、陳歌辛、姚敏、梁樂音、嚴(yán)工上等。由于此五人在當(dāng)時流行音樂界的影響,被稱為流行歌曲的“中國五人幫”。其中,以黎錦光與陳歌辛的影響最顯著。
相比之下,劉雪庵的《何日君再來》由于具備近似的特點和風(fēng)格,再加上日本歌星李香蘭{11}以其特殊的身份對這首歌的演繹,使其在淪陷區(qū)的影響絲毫不遜色于上述流行歌曲作品。眾所周知,此時的《何日君再來》和黎錦光、陳歌辛的流行歌曲作品一道被敵、偽加以利用,使得諸流行歌曲作品呈現(xiàn)出比三十年代初期黎錦暉的“時代曲”更為復(fù)雜的情況。
當(dāng)政治、殖民、商業(yè)、娛樂和藝術(shù)等多種因素紛紛滲透到像《何日君再來》這樣的一首流行歌曲之時,當(dāng)以黃嘉謨{12}為代表的“軟性電影”論者加盟到流行音樂創(chuàng)作隊伍之時,當(dāng)以淪陷區(qū)的小市民階層為流行音樂的主要受眾群體之時,流行音樂作品自然會存在粉飾太平、遠(yuǎn)離社會現(xiàn)實的問題,也自然會誤導(dǎo)受眾“今朝有酒今朝醉”。如此看來,《何日君再來》和淪陷區(qū)的流行音樂作品被浴血奮戰(zhàn)的抗日軍民和追求進(jìn)步的人們視為“靡靡之音”和“宣揚了及時行樂的不健康的情調(diào)”{13}是再合情合理不過了。
與八十年代以來流行音樂的關(guān)系
作為當(dāng)代人,我們很難從某一個方面去孤立地看待《何日君再來》和同時期的流行音樂及其作曲家劉雪庵、黎錦暉、黎錦光、陳歌辛等人,我們只能用歷史的、多元的、立體的眼光去重新審視他們、聆聽他們。
1949年以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流行音樂幾乎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了。三四十年代中國流行音樂的創(chuàng)作中心已然在不知不覺中一路南下,輾轉(zhuǎn)到了中國的東南沿海兩地——香港和臺灣。這就為后來八十年代“港臺流行音樂”的卷土重來埋下了伏筆。
1967年,中國大陸正在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此時的革命人民似乎早已忘記了劉雪庵和他的《何日君再來》。然而在海峽的彼岸,臺灣歌星鄧麗君出了她第一張個人專輯《鳳陽花鼓》。在這張專輯中,制作方宇宙唱片公司就收入了《何日君再來》這首歌,但不知為何并沒有用《何日君再來》的歌名,而是改了一個名稱——《幾時你回來》{14}。鄧麗君的這張專輯的出現(xiàn),悄悄地傳達(dá)出兩個信息:1.《何日君再來》在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臺灣也受到了一定的官方限制;2.時隔三十年《何日君再來》依然在民間頗受歡迎。
八十年代初期,《何日君再來》伴隨著鄧麗君的歌聲一道跨海而來。由于近三十年與流行音樂絕緣,大陸的青年受眾甚至誤以為《何日君再來》是鄧麗君的“主打歌”或“原創(chuàng)音樂”作品。但老一輩的受眾由于曾經(jīng)耳聞目睹了《何日君再來》的消極影響,依然視其為“精神污染”。與此同時,“臺灣校園歌曲”這一嶄新的體裁以更加公開的方式堂而皇之地進(jìn)入了中國大陸流行歌壇,其中尤以《鄉(xiāng)間小路》《外婆的澎湖灣》和《龍的傳人》等作品影響最大。如果說鄧麗君的歌聲是發(fā)揚光大了劉雪庵、黎錦光、陳歌辛等作曲家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作品的風(fēng)花雪月、郎情妾意的淺吟低唱風(fēng)格的話,那么此時的“臺灣校園歌曲”就是在前者的基礎(chǔ)之上又賦予了流行音樂以日本、歐美國家和臺灣本土文化的新氣息,呈現(xiàn)出比前者更為獨特的情況。
時至今日,中國流行音樂的受眾已然由初創(chuàng)時期的小市民階層轉(zhuǎn)為人民大眾群體,創(chuàng)作題材也由原先的局限于卿卿我我、顧影自憐擴(kuò)大為既有委婉哀怨的傾訴又有鏗鏘陽剛的歌頌,表演舞臺已由早期的歌樓舞廳酒吧延伸至電視“走秀”和國家級慶典晚會,創(chuàng)作主體也由原先的少數(shù)專業(yè)音樂家涉足發(fā)展到相當(dāng)數(shù)量的專業(yè)作曲家和職業(yè)“音樂人”共同加盟。如此看來,近八十年來,中國流行音樂創(chuàng)作已經(jīng)取得了長足進(jìn)展,中國流行音樂界也相應(yīng)地發(fā)生了諸多變化。但靜下心來細(xì)想,從《桃花江》《何日君再來》《夜來香》和《玫瑰玫瑰我愛你》等歌曲到今天的《是否愛過我》《揮著翅膀的女孩》《看我72變》和《老鼠愛大米》等作品,我們?nèi)匀荒軌驅(qū)ひ挼教幱谥袊餍幸魳钒l(fā)展史兩極的諸作品之間的共同之處:
諸作品都能夠最大限度地考慮到自己的接受對象——大眾。這種“以人為本”的思想又直接決定了這些作品在旋律上注重優(yōu)美抒情、在風(fēng)格上注重民歌因素、在音域上注重適中、在伴奏上注重多元、在演唱上注重獨特、在宣傳上注重包裝等。這是中國流行音樂一脈相傳的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所決定的,這也是我們應(yīng)該在今后的流行音樂發(fā)展中發(fā)揚光大的。然而,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在今天的流行樂壇上仍依稀可見三四十年代流行音樂的痼疾,如殖民地性、無病呻吟、緋聞炒作、粗制濫造和“娘娘腔”等問題。這是流行音樂作為文化快餐和大眾藝術(shù)在發(fā)展的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如何解決這個痼疾,怎樣才能最終避免這些問題,這是擺在二十一世紀(jì)中國流行音樂諸家們面前的一道難題。
毫無疑問,劉雪庵的《何日君再來》是一首電影插曲,而且還是一首由他人代為“倚聲填詞”的歌曲。電影插曲的屬性決定了《何日君再來》是為特定的劇情、場景而進(jìn)行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有些電影插曲離開電影畫面后,其本身在思想和藝術(shù)之間并無沖突,而有些電影插曲脫離電影劇情后,其很有可能在思想和藝術(shù)之間出現(xiàn)相脫節(jié)的問題。如果再被李香蘭、渡邊河瑪子等具有特殊身份的歌星在淪陷區(qū)或日本等地推波助瀾地傳唱的話,這種“脫節(jié)”的問題自然會愈來愈突出,消極影響也就會越來越嚴(yán)重。
作為當(dāng)代人,我們很難從某一個方面去孤立地看待《何日君再來》和同時期的流行音樂及其作曲家劉雪庵、黎錦暉、黎錦光、陳歌辛等人,我們只能用歷史的、多元的、立體的眼光去重新審視他們、聆聽他們。
這是對歷史最客觀的學(xué)習(xí)和解讀方法!
①由于至今何謂“流行音樂”尚沒有一個令學(xué)術(shù)界達(dá)成共識的概念,此處的“流行音樂”主要指當(dāng)時在市民階層流傳廣泛、膾炙人口的歌曲。
②電影《小姐妹》插曲。
③《彈性女兒》和《雙雙燕》分別為電影《彈性女兒》的主題歌和插曲。
④劉雪庵《怎樣才能徹底取締黎錦暉一流劇曲》,上海《音樂雜志》,1934年第3期。
⑤劉學(xué)達(dá)《“翻”開塵封的歲月》,《金陵敘事》網(wǎng)站,2005年8月8日。
⑥張魁堂《一段回憶——歷史是涂抹不了的》,《人民音樂》1980年第11期。
⑦日本作家渡邊龍策在他著作《馬賊》里提過《何日君再來》,說它是中國版本的《歸來吧蘇連多》。
⑧沙青《訪著名作曲家劉雪庵》,《北京晚報》,1980年7月27日。
⑨梁茂春《對我國流行音樂歷史的思考》,《人民音樂》1988年第7期。
{10}賀綠汀《應(yīng)該還他本來面目——從〈何日君再來〉談到劉雪庵》,《北京晚報》1980年8月20日。
{11}李香蘭是生于中國的日本人,本名山口淑子,“李香蘭”是她唱“滿洲新歌曲”時用的中國藝名。
{12}黃嘉謨是《何日君再來》的詞作者,是三十年代“軟性電影”的代表人物,其經(jīng)典論點是:“電影是給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給心靈坐的沙發(fā)椅”。
{13}黎莉莉《幸存者有責(zé)任講實話!》,《北京晚報》1980年8月4日。
{14}徐天翔《何日君再來——當(dāng)代(近現(xiàn)代)中國音樂系列關(guān)鍵詞之二》,《天籟》2005年第2期。
項筱剛 中央音樂學(xué)院講師,博士
(責(zé)任編輯金兆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