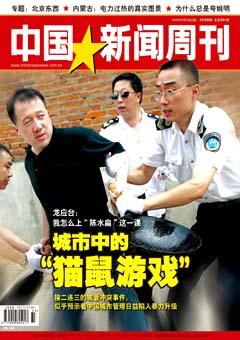“整個內蒙古都是熱的”
蘇 琦 郇 麗
電力過熱折射出的是內蒙古整體經濟的高速運行,從煤到電到煤+電+重化工,內蒙古的狂飆突進一度讓人發出了中國經濟重心北移的驚嘆
美國著名漢學家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中預言道,工業和鐵路的發展,將徹底打破千年來游牧經濟和精細農業間的對峙性消長與糾結,從而將內蒙古與長城以南的中國徹底融為一體。
拉鐵摩爾的斷言來自于上個世紀30年代他在蒙古草原的長期考察。其時蒙古草原正面臨著日本侵略的現實威脅,以及蘇聯和內部分裂勢力的影響,但拉鐵摩爾卻樂觀地看到,在蒙古草原和傳統農耕區之間一種新型親密關系構建的可能性。
幾十年后的今天,現實正以激昂的姿態印證和拓展著拉鐵摩爾的預言:內蒙古不僅通過煤與電和整個中國的經濟緊密結合在一起,近年來更憑借“揚眉吐氣”(羊煤土氣)的資源優勢成為全國的資本洼地,動輒令數千億資金為之神魂顛倒——2005年,內蒙古全年企事業單位自籌和社會投資達到2000億元。
同樣傲人的還有GDP和財政收入。2005年,內蒙古全年實現生產總值3822.8億元,同比增長21.6%,全年實現財政總收入536.3億元,增長43.6%。
事實上,自2003年以來,內蒙古的GDP和財政收入增幅一直名列全國第一。和山東、山西一起,內蒙經濟的躍進,令經濟學界發出了中國經濟重心正在北移的驚嘆。
然而,在宏觀調控大背景下,在中央三番五次要求各地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呼聲中,內蒙古速度屢屢令高層為之蹙眉——僅2005年一年,內蒙古自治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就完成2688億元,增長48.6%。
因此,在相關人士看來,電力違規事件只是一個導火索而已,“豈止電力過熱,整個內蒙古都是熱的。”而在8月16日的國務院常務辦公會上,針對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的批評中就有“對國家宏觀調控的決策執行不力”。
其實,就連內蒙古自治區政府自己也已經開始對連年的高速增長感到些許“不自在”了。在今年初,自治區政府主動“踩剎車”,將2006年的GDP增長率定在15%左右(去年21.6%),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5%左右(去年48.6%),財政收入增長20%左右(去年43.6%)。
按內蒙古發改委人士的話說,“之所以這么安排,就是為了給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預留較大的空間,以不斷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防止經濟增長出現大的波動。”
然而,從今年上半年的態勢來看,內蒙的經濟引擎仍熱度難減。一季度,全區實現生產總值535.7億元,同比增長19.8%,高于年初定的15%。而固定資產投資仍舊增勢如虹,全區城鄉規模以上單位完成固定資產投資達74.2億元,同比增長67.8%。
在解釋內蒙古經濟為何取得“開門紅”時,自治區發改委主任呼爾查對媒體強調了重點項目的作用,“一季度經濟的高效運轉,可謂是亮點頻出。特別是重點項目建設,由于各地區、各部門早部署、早安排、早啟動,進一步加快了進度。一季度累計新開工項目209個,規模達到138億元,尤其是自治區重點推進的重化工項目、電源項目和鐵路項目建設取得重大進展。”
對于內蒙古各級政府來說,重點項目的作用是扎扎實實的。在中國現有稅收體制下,有投資就有財政收入,不管有沒有產出,地方上只要有大項目就有投資稅,建了工程就能有稅收。以前文提到的蘇里格電廠為例,烏審旗一位分管工業的副旗長說,蘇里格發電項目的建設每年使該旗增加財政收入6000萬元。此外,該項目還提高了烏審旗的知名度,推動了招商引資,對全旗的工業起到了有力的輻射帶動作用。
而無論重化工項目、電源項目和鐵路項目,這一切的核心是煤。
僅僅10年前,對于內蒙來說,坐擁煤海并沒有意味著太多的財富和喜悅。受制于運力不足,內蒙當年多少有些無奈地提出了“煤從空中走”的戰略,即利用煤發電供經濟發達地區使用,號稱“西電東輸”。
好運氣總在人們意想不到的時刻全部到來。2001年以后,隨著中國進入新一輪經濟快速增長期,煤炭價格大漲,電力緊張導致用電需求大增,這給內蒙古經濟的增長帶來了立竿見影的刺激——修鐵路,修公路,倒煤炭,建電廠,一時間各種一夜暴富的故事漫天飛舞。
接下來,由汽車和住房消費而激發的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高耗能產業的勃興更將內蒙的優勢集中釋放——就近的煤炭,便宜的電力,伸手可得的原材料,這一切令從國企到民企,從央企到地方企業,從銀行資金到民間資本的投資項目如雨后春筍般四處涌現。
等到了第三波煤化工和天然氣化工投資高潮時,內蒙古經濟運行只能用炙手可熱來形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