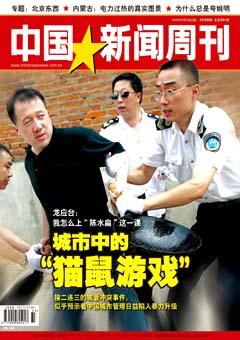《建筑師》,大師的高峰體驗
顏 榴
《建筑師》是易卜生晚年的劇作,今由林兆華、濮存昕、陶虹搬上國內戲劇舞臺。從劇本到舞臺設計,基本沒有什么商業元素,卻從中體會到更純粹的來自戲劇的美麗
這是一部寫給男人的戲,如果制作人在廣告上標明“為50歲以上成功男士而做”,不失為一個好賣點。確切而言,惟有那些已過中年、在事業上到達過巔峰、又走入頹唐的“建筑師們”,最能體會到男主人公的心境和苦楚,更何況還有一個年齡相差30歲以上的男女的愛情!
隨著濮存昕的公益形象日漸深入人心,人們有時幾乎忽視了他作為一個舞臺劇演員的魅力。更多的時候,這種對于角色的渴望僅僅糾纏著演員本人,因為在今天,那些個豐富而深刻的角色(往往出自西方戲劇名作)越來越難以在舞臺上矗立起來。這也是當濮存昕變成易卜生筆下的建筑大師時,連眼眶里都蓄積著力量的原因;也是他那么堅定地跟隨林兆華的結果——是“大導”選擇了這樣一個非常晦澀的劇本,讓他在此次的表演過程中終于尋到一個才情釋放的爆發口,去體驗精神的冒險。
很多時候濮存昕只是坐在椅子上說話,至多腿擱在腳蹬上或者放下來,雖然他的內心在經歷風暴,身上卻沒有劇烈的動作,他的感情投入和臺詞功力是無懈可擊的。當他開口時,別的角色也同時加了進來,造成一種和聲般的效果,導演的意圖非常明顯,建筑大師和他身邊的人在進行著一場心智的較量,他們各自吐露著心跡,卻聽不到別人的聲音。
這種舞臺意識流的手法著實有些大膽,為捕捉情節前來看戲的觀眾一定是有些茫然了。當陶虹到來時,沉悶的空氣改變了,她像一只小鹿般撩撥起老人青春的意緒,然而他們之間的談話恐怕又要讓人失望了,他們確乎只是在談,言語中不夾雜一個“愛”字,既沒有彼此的思念,也沒有肉體的欲望,身體也始終保持著距離,但是這種忘年戀已然超乎了世俗的愛情。那也許是老易卜生本人、老歌德、老海德格爾都曾親歷過的高峰體驗吧。
就觀賞性而言,易卜生晚年的劇作大不如早年和中年,《玩偶之家》《群鬼》掀起世界性的熱潮,也給中國戲劇帶來深刻的影響,而他晚年的象征主義戲劇在現代的中國得不到回應也屬正常。今天,中國觀眾接受《建筑師》也仍有一定障礙。但若是戲劇總要迎合著人們、討好著人們,懶得去打開一扇扇人性的窗口,那它還是早早死亡好了。致力于發掘西方戲劇寶藏的林兆華導演一向敢于顛覆人們既定的審美范式,排演《建筑師》依然可以看作是對他的戲劇理想的堅守。
通過服裝造型,該劇基本國際化了,尤其是濮身上的那件馬甲在他穿來頗有大師風度,年近七旬的“大導”對時代潮流的敏感甚至超過不少中年同業者,《白鹿原》請出最樸拙的老農民登臺,《建筑師》邀出時尚界的名流加盟,一戲一格,皆言之成理,因而他的戲在任何時候,總葆有那個時代最鮮活的氣息,這是人們最終服膺于他的原因吧。
一把紅椅子、逼仄的大背板以及最后打開的天梯十分凝練,象征意味恰到好處。
天性寬厚善良的濮存昕和天性樸實可愛的陶虹在角色的氣質上還少了那么些挪威山精的氣息,這是有可能在服飾造型上加以彌補的。使濮的頭發灰白些既能增大年齡感又加強了時尚的意味,陶虹的服飾和發型若往哈日的路子上靠一靠,則可能吸引今日的少女一族。劇中索爾尼斯和希爾達之間的年齡差別越大,越可以有更多的想象空間,本來縈繞在他們之間的,可以是愛情,也可以不是愛情。
不過有一點匪夷所思的是,在首都劇場這個中國話劇的最高殿堂,一向仁慈的林導吸納了很多熱愛戲劇的朋友來加入表演,可如果業余與專業演員的反差太過明顯,將直接削弱一臺戲的整體水準。畢竟舞臺僅憑真誠缺乏技巧是無法打動觀眾的,這對觀眾不太公平了。
兩年前的《櫻桃園》與眼下的《建筑師》都是林兆華戲劇工作室推出的作品,怎么讓這樣的作品得以留下來,成為可以反復上演的保留劇目呢?演員的使用是一個關鍵,林導當然明白個中要害。這便是在中國,即便是這樣一位一出場便博得喝彩的大師級導演也會發生這樣的失誤,可見我們的戲劇界實在是有著太多的難言之隱了。
(作者為國家話劇院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