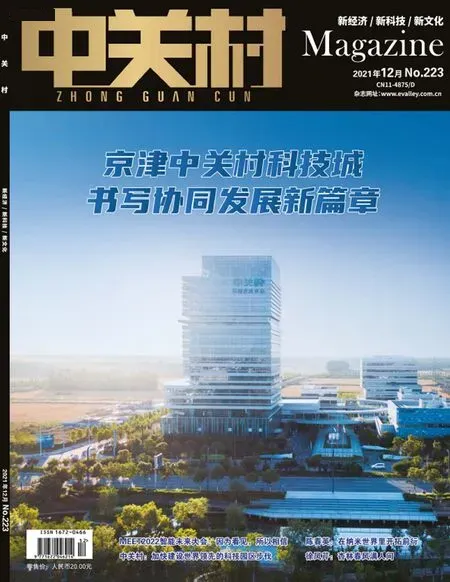1969年的白菜
王宏甲

困難有很多。卻沒想到,在那到處可種菜,并且沒有一戶農民不種菜的小村,竟會買不到青菜。
難于想象嗎?你想,村里連小學教員、醫療站醫生、供銷點售貨員、糧食購銷站的工作人員都種菜。只有上級派來的工作隊不種菜,但他們吃“派飯”,還有誰需要買菜呢?在那些遠離集鎮的窮鄉僻壤,那關于青菜買賣的概念生長得起來嗎?
我插隊的那個地方不是西北或東北,是后來作為經濟特區的福建。約八百年前,宋朝在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今寧波),還有廣州,設市舶司,那是掌檢查出入海港的船舶,征收商稅,管理外商的官署。這多少已有些后世海關的味道。
我插隊的山區在閩北,遠離大海,聽不見濤聲。但閩北是從海邊通往南宋京都的要道,七八百年前,那里古老的驛道早已被經商的車馬踏出一條并不荒涼的商道。我插隊的村莊離那商道不足百里。
十七世紀,歐洲人喝到的第一批茶葉,就是從這片土地上由荷蘭人經爪哇運往歐洲多國的武夷茶。那以后,這里的農民曾使千年種糧的土地飄揚起茶葉的清香。迄今,在村莊古宅殘破的大石門楣上,還清晰可見雕龍鐫鳳的形象,石獅、石馬、石鹿、石麒麟栩栩如生。那形象出現在這種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并非皇家皮鞭逼迫下的工藝。那形象在告訴我們,這片窮鄉僻壤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較為繁榮的時期,那形象該是當時鄉村經濟培育的藝術。
村莊里還流傳著明代西洋傳教士到此布教的故事。真不明白是什么力量驅使著那些洋人,遠涉重洋到這樣的偏僻地方來建教堂。比起他們,我們告別故鄉的路程,不及他們遙遠了。
洋人消失的時候,教堂被當地農民改造成了廟宇,塑進中國菩薩。我們去插隊的時候,菩薩不見了——在我們到來的前兩年,被鄉村紅衛兵搗毀了——單剩下立菩薩的土臺子。洋人留下的大鐘,則在大煉鋼那年被砸碎填了高爐……那時刻聽著遙遠的故事,不免想,當初那些洋人也該向當地農民買青菜罷,茶葉能買賣,青菜也必能買賣。但是,我們來的時候,村莊里找不到一個賣菜的人。
不管時光過去多久,那些日子都站在記憶中。
我最初吃的青菜,是農民送的。分給我們種菜的“自留地”,由于各種原因,我們往往種得不景氣。至今記得第一個把一顆大白菜賣給我的是一位無妻無子的孤老頭。
那時刻那顆大白菜被剝去外皮,被洗得相當白凈,躺在一個竹篾編制的大土箕里,土箕懸掛在一根晾曬衣服的竹叉上。小村的白日,人們都出工去了,相當安靜。那時刻有一頭母豬在墻上蹭癢,一蹭一蹭地把那根竹叉要蹭倒了。竹叉就立在門外。這白菜為什么掛在門外,莫非要賣?
我轉進門去,就看到了那老漢。就問。老漢不置可否。躊躇著說,要,就拿去吧。我給了錢。我不記得給多少錢。老漢也不在乎給多少錢。總之,我成功了。應該說他和我都成功了。
那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那個日子我把大白菜抱回去猶如捧回一個紀念杯。我向我們的同學宣告這項收獲。那個日子,我們餐桌上漾動的喜悅不亞于歐洲人喝到武夷茶拿破侖吃到四季豆。
但是,我們很快就領略到,那位孤老漢把菜賣給我是需要勇氣的。因為在這個民風極為淳樸的山村,村頭村尾很快就流動起對賣菜老漢的評說。最寬容的意見是:一個孤人,老了,還有病,也是沒有辦法。
小村當然不是沒有買賣關系。大規模的買賣活動發生在夏收和秋收。農民們集體擔著糧食賣到國家設置的收購點去。那里的收購員用手把捏著我們種出的果實,然后宣布等級和價格。有權去數鈔票的是生產隊的出納員。生產隊則以“預支”的形式,每月向農戶預支若干元人民幣,那人民幣來自信用社的貸款。農民們主要用于購買鹽巴、火柴、肥皂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添置新衣一般在冬天“分紅”之后,那時刻農民以“結算的方式”獲得了轉換為貨幣的勞動分配。一年一度的“分紅”,周轉期比水稻的生長期更長。當中國有八億人口時,六億農業人口接受這一分配形式。
我們去插隊落戶,那就是我們共同的經濟生活。那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當我們在自然條件適合種植菜蔬的村莊卻遭遇買不到青菜的難題之時,中國的經濟意識為生產意識所取代的情狀,該是相當普及相當獨特了。那些窮鄉僻壤里的商品意識,已萎縮到一個不能再干涸的形態,那就是我們生存其中的經濟基礎。而買不到青菜的困難,實際已是:我們遇到的一切其他困難的基礎。
但是我們來了。我們同農民們共同完成的一項為生存而發生的行為,使這些窮鄉僻壤里的菜蔬有了價格。

不久,鄉村里流傳:“吃糧靠集體,用錢靠自己。”這不全是由于我們同農民之間發生的買賣關系。在那些離集鎮較近的鄉村,以及遠離集鎮的鄉村,都有村姑村婦,老漢,也有男性青年,正一次次向城鎮出發,營造出一個又一個自發的買賣場所。這些中國農民,是向集貿市場發起進攻的主力軍。
我們不是英雄。至少我不是。在“用錢靠自己”受到當時“正統”輿論批判的時日,我們一些知識青年秉承大隊工作隊的旨意,曾把若干白日和夜晚投放在大隊部的大長桌上,構思漫畫寫墻報,然后貼在小村宣傳欄的土墻上,去教導村民安心生產。
但是,我們仍然要吃青菜,還要吃雞蛋,只有很少的知青像農民那樣養雞。我們不是有意識的叛逆者。我們只是由于要存在下去,是生存的本能起來反叛我們,默默無聲卻相當有力地修改我們的行動和意識。當集貿市場在城市遭到封閉的日子出現時,成千成萬置身于偏僻鄉村的知識青年同農民之間的買賣關系從未間斷過,這種關系使鄉村的雞蛋一直顛撲不破地有價格,使那部分產品變成商品。
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持續十余年。我們在那里催發的不僅僅是與菜蔬買賣有關系的意識。
油燈搖曳的夜晚,我們的吉它伴著我們憂傷的歌聲,在我們的住處響起,那就是這片土地千年不曾有過的旋律……那時刻,我們的屋里屋外都坐著不同年齡的貧下中農。
我們唱的有不少是異國歌曲。那些能夠超越國界,超越年齡,超越職業的旋律,大約就是藝術的生命。
那屋里屋外都存在的靜靜的凝聽,也許不只是在聽我們的憂傷,說不定也會想起他們自己,甚至想起他們祖母的古老故事。
當然也唱那些昂揚雄闊的歌,比如“雄偉的天安門,壯麗的廣場,第一面五星紅旗升起的地方……”那時刻不是我們自己唱,是在小隊部里使農民們好比在解放初期的夜校里,再度開放自己的歌喉。
還有我們青春期在鄉村發生的戀愛故事。我們的雙唇也曾熱烈而真實地吻上鄉村異性青年的雙唇……即使我們自身的處境是多么難以從容,但我們帶去的城市文化,對鄉村往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產生的沖擊是多方面的,是以往的任何文化教導所不曾達至的。當我們終于從那片土地上撤退的時候,也曾使那里的農民,尤其是鄉村男女青年感到猶如失去一個時代。
我們回來的時候,不是凱旋。
歷史從未對我們的歸來留下“凱旋”之類的字眼。
我們是去接受再教育的。但是,我們也把我們的知識和寶貴青春播種在那片土地上了。應該說,中國數以千萬計的知青,牽動了那個時代幾千萬父母心的你們的兒女,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遠沒有到來的時日,你們的兒女已經用自己在鄉間的生存,使商品意識在相當遼闊的土地上獲得一定程度的復蘇,使這個犁下有深土的民族在多方面孕育出新的文明因素,使那些土地上遠遠多于知青的人們也悄然萌生出革新自己生活的愿望。
一切時代的進步,都不能缺少經濟生活和社會意識中被注入新的活躍因素。中國知青把青春植入農業國的土地,已然是在為一個偉大民族未來的改革,蘊蓄著走向改革的因素。
所有的凱歌都是用熱血和青春去鋪排出音符。

我們沒有凱歌。
但我們付出了熱血和青春。
那的確是幾千萬新中國締造的一代兒女,用青春去譜寫的一支歌。
后記:
這篇文章寫于1992年底。這年冬天,我在寫這篇文章時感覺到內心深處有誰在給我一種異乎尋常的指引。筆下的插隊生活,本來是青春時期最艱難的日子,艱苦、勞累、困惑、期待,乃至心靈的痛苦和搏斗,都曾經充滿了那段歲月,但描述那段歲月卻令我振奮,為什么呢?寫出這篇文章后,我自己閱讀了很久,然后我發現自己在寫這篇文章時獲得了一個重要的世界觀,就是可以從經濟基礎的視角來認識這個世界。所謂世界觀,是人認識世界的一種方法,我由此知道,認識世界可以有多種方法,換句話說,我豈不是可以擁有多種世界觀嗎?這年冬,我感覺到自己獲得了一種世界觀,是發現從經濟基礎的視角去認識世界,世界在我的眼前變了。在過去的很多歲月中,我們探討民主、藝術、政治、思想、觀念,等等,常常就藝術談藝術,就民主談民主,可能慷慨激昂,激憤不已。但我在寫出這篇“白菜”后,突然發現,從前的許多慷慨未免作“空中樓閣”之談,失卻基礎。譬如不必用怎樣慷慨激烈的語言論述“文革”的種種災難,從一棵“白菜的命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片歲月中我們整個民族經受的莫大損失。正是這種從經濟基礎的角度去看世界的眼光的獲得,那以后我寫出了《現在出發》(含從現在開始去認識世界的意思),接著寫出了《智慧風暴》《中國新教育風暴》《貧窮致富與執政》等。所以我很看重自己1992年寫的這篇文章,我曾經反復閱讀,其情形可以描述為,自己學習自己寫的文章。它是我寫作生涯,也是我人生認識這個世界的一個轉折點。
(作者系著名作家,著有《無極之路》、《智慧風暴》、《新教育風暴》、《貧窮致富與執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