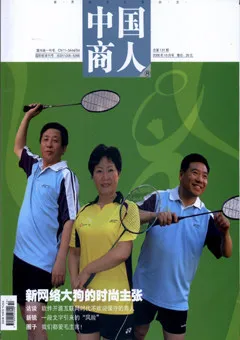王銘 儒雅商道

寧波東錢湖有一大片綠,這綠色世界里有一位精神矍鑠、慈眉善目的長者,在夕陽或者朝暉里揮桿,或者沿著小道踱來踱去,找一個滿意的角度架起照相機……
這片令人神往的綠就是寧波啟新高爾夫球場,而這位長者正是球場的主人——王銘。
結緣高爾夫
筆者在啟新高爾夫的咖啡廳見到了王銘,和所有熱愛高爾夫運動的人一樣,黝黑的膚色,一件短袖的T恤,五月的寧波還有點寒意,何況又在球場,這使王銘顯得格外健康和精神。一直以為王銘是港商,一開口卻是軟軟的京腔,外加一副特厚重的眼鏡,顯得學者味十足,完全不是概念中外資大商人的形象。
“儒商?這好像是在說我不會做生意吧?”當我們向王銘闡述了我們此行的目的——通過采訪幾位儒商來完成我們對新儒商文化的考究時,王銘哈哈大笑,而采訪就在這樣的氣氛中開始了。
王銘194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他的父親是著名僑領、全國僑聯駐會副主席王源興,9歲那年王銘跟隨父母回到北京,就這樣,王銘在北京開始了他的學業。1967年從清華大學汽車設計與制造專業畢業后,王銘成了長春汽車研究所的一名鈑金工,5年后回到北京,在第二汽車廠負責汽車測試。1975年,王銘在海南島試車時連車帶人翻下了深溝,雖然,人車兩全,但從此以后,王銘沒再繼續他的專業生涯。
1978年,王銘到了香港,在那里第一次知道了“傭金”是什么,他的第一桶金就是兩萬元傭金。于是王銘成立了外貿公司,輾轉在朝鮮、臺灣、廣州、北京做雨傘綢布貿易,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再后來到香港做起了房地產,資本雄厚了之后又投資了北京賽特集團。
談到王銘為什么最后選擇了高爾夫,選擇了寧波,故事就變得越來越精彩了。
王銘在1983年得了一場大病,病愈之后,經朋友推薦,在書畫之余就開始了高爾夫運動,既對身體有利,又可以修心養性;慢慢地就開始沉浸在這個運動中,成為一個鐵桿高爾夫迷了,同時也成了許多頂尖球場的會員和座上賓。正因為如此,1998年,當王銘得知寧波正準備招商籌建一個高爾夫球場的時候,便欣然前往這個對他來說完全陌生的城市。
高爾夫球場是投資大,回報慢的長期投資,作為一個商人,王銘當時的心態是謹慎的,也因為從來沒有做過類似的項目,僅僅是一個高爾夫運動的愛好者,來寧波更多的是一次交流,但緣分兩字似乎一開始就緊緊地把王銘和寧波聯系了起來。
在前往寧波的飛機上,王銘坐在頭等艙,飛機降落后,王銘習慣性地擦擦眼鏡,一不小心把眼鏡掉到前排的座位底下。這時候,前排一個面目友善的中年人不聲不響地俯下身子撿起來,微笑著遞給王銘。王銘道了聲謝,那人仍然笑容可掬,謙讓了一下,各自下了飛機,王銘自然對寧波人有了點好印象。第二天,在考察完寧波東錢湖后,當晚鄞縣的領導請王銘吃飯,討論有關球場的投資事宜,飯局前,王銘被告知寧波市長也要親自過來一趟。
當晚餐開席一會兒,市長張蔚文來了。
“呀,是你呀!”王銘伸出手去,旁邊的人感到奇怪:“怎么,你跟我們市長認識?”王銘笑了笑,“認識,他昨天給我撿了眼鏡”。時任寧波市長(現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浙江省高協主席)的張蔚文也說“是呀,咱們這叫有緣分呀”。
飯局上,王銘更加感覺到了張市長的誠懇:市長坦言寧波缺一個高爾夫球場,前段時間有一個銀行系統的國際會議想到寧波來開,但聽到沒有高爾夫球場就不來了。市里及當地政府已經與十多位投資家接觸過,來看的不少,但至今沒有一個落實。因建高爾夫球場投資巨大,所占場地巨大,所以,當時全國有高爾夫球場的城市都不多。聽到這里,王銘也直截了當地表達了心中的憂慮:主要是政府辦手續難,很長時間連手續都辦不下來,投資風險和成本就會變大。
接下來的事情就更戲劇性了。
張市長立馬拍板:“王先生如果您來投資,我以市長的名義向您保證,7天之內一定幫您辦好所有的手續。”
“那好,我就給你搞一個”。王銘脫口而出。
就這樣,一個寧波商業上的經典故事就這樣誕生了:兩億多的項目考察當天拍板,第三天簽合同,第四天付定金,一星期辦好所有手續,一年時間球場落成。
這就是張市長撿眼鏡的故事,也是寧波速度、啟新速度的奇跡。王銘是幸運的,但同樣幸運的還有寧波。
沒有傳奇的商人

作為一個商人,王銘的成功是有其必然性的:他從小天分極高,在他9歲的時候就自主選擇留在了北京,而無論小
學,還是初中、大學,王銘都一直輕松地就讀于最好級別的學校;北京師大附中、北京男四中和清華大學等。王銘下海的年代又是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大飛躍的經濟年代;而王銘的父輩又留給他深厚良好的社會資源。
相比于某些白手起家的巨富商賈和90年代之后出現的新型產業的草根商業英雄,王銘的成功沒有太多的傳奇性,他利用他所擁有的各方面的商業資源和條件,順應改革開放年代的經濟發展模式,達到了他現有的商業高度。富有太多傳奇性的創富歷程是不可模仿或難以借鑒的,而像王銘這樣的標準的商業軌跡,卻正好是大部分商人值得遵循的模式。
可能也因為這樣,王銘始終是低調的,他無數次用這樣簡單輕閑的敘述方式,對朋友和媒體講他的創業史,在他的語調里,似乎每一樁生意、每一步都是自然的。再加上花甲之年的王銘已經有了歸隱之心,對于他自己的人生軌跡有了一種歸納后的簡單和肅靜。
儒雅商道
不管王銘喜不喜歡友人贈送的“儒商”的美譽,接觸過王銘的人都不自覺間為這位具有很深文化素養的商人所觸動,而想到“儒”這個詞。
在啟新高爾夫,除了高爾夫界元老和高爾夫運動崇尚者,文藝界的泰斗、大師、新秀也都是這里的座上賓,圍棋界的、象棋界的、書畫界的朋友們,王銘在這里以文會友。
而無論是圍棋、象棋,還是書畫,王銘都可以稱得上高手,與專業人士有得一拼。而他所有的技藝,都是無師自通,自在自得。
早在上學期間,王銘就迷上了棋,一迷就是30多年。1988年舉行的“五糧液”象棋攻擂賽上,王銘作為一名業余選手,先后戰勝了中國女子象棋冠軍胡明,中國象棋大師閻文清,榮獲中國棋院頒發的中國象棋榮譽大師稱號,自后,王銘就任了中國圍棋協會顧問,中國象棋協會顧問、世界象棋聯合會副主席等棋界職位。
1983年,王銘得了一場大病,病愈后靜心休養期間,王銘又開始畫畫了,這一畫就畫出了一本《彥甫畫選》,得到黃永玉大師作序,黃胄大師作后記。黃永玉在序中說:“……我總覺的他這號人不畫便罷,若認真動起手來,就一定會有特別的東西弄出來……”,而黃胄說他的畫是“大家風范”,兼有各位大師的風格。
王銘以文會友的性格早在年輕時候就開始了,在“黑云壓城城欲摧”的特殊歲月里,王銘和一些正直的畫家大師相交甚密,結下了患難友情;王銘也從不以畫價比高低,論輕重,只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畫藝,筆耕不斷。
王銘在北京是出了名的玩家,花甲之年,他又出人意料地玩起了高爾夫,時任浙江省高協副主席。“我就靜靜地在這里安度晚年,蠻好的。”2002年,王銘又一次玩起了照相機,2004年出了一本《綠之夢——彥甫攝影選》:啟新的每一個精彩的角度,那些巧奪天工的球洞,都是王銘照相機中最完美的素材。
而王銘的琴棋書畫技藝,并不是眾人眼中的王銘“儒”的全部,這些只不過是其表象。我們不妨把“儒商”解釋為“秉承儒家文化的商人”,而儒家文化的內涵在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王銘身上,我們可以很強烈地感受到一種讀書人的操守和固執,正如王銘自己所言,只要他答應別人的事情就盡量去完成,這就是儒家的誠信。
王銘也曾遭到一些對他不甚了解的人的非議,一位和王銘私交甚好的當地官員告訴筆者,其原因就是王銘做人十分率直,不愿意講很多潛規則。不過,這些應該是王銘的可愛之處,在經歷了商場的風雨之后,儒者王銘以一種氣定神閑和返樸歸真,經營著他心中的“綠色世界”,可謂是透悟了“儒”的本質和精神。
最后談論起高爾夫運動,在王銘的介紹下,我們第一次知道,認為高爾夫是一項昂貴的貴族運動,其實是錯誤的過時的。于是我們提出,要以一個媒體人的職責來宣傳高爾夫應該是一項平民化的、健康的運動,王銘平靜地說:“不要去告誡他們,不要告誡!”因為,在王銘的意愿里,健康之路也應該是一條自悟、自省的路。
如果可以,請在一個清新的早晨或者傍晚,到東錢湖散步,如果你看到一位精神健碩的長者在從容地消磨時光,那他可能就是王銘,不妨走近打個招呼,王銘會帶你走遍高爾夫運動場,跟你慢慢地聊起往事,介紹高爾夫的種種樂趣,你也會明白,在這喧鬧的都市里,如何真正地以清澈明亮的心融入大自然,而非口頭的標榜“大隱隱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