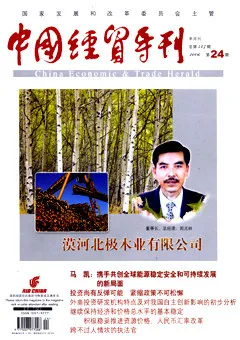多次性微調:使經濟增長率不“冒頂”
當前,在本輪經濟周期中宏觀調控又表現出一個新特點,即宏觀調控多次性或多階段性的特點。在此,擬對這一特點及其政策涵義作一分析。
一、 我國經濟增長出現的新軌跡
在我國上一輪經濟周期中,谷底年份1999年的經濟增長率為7.6%。隨后,2000年和2001年經濟增長率分別回升到8.4%、8.3%,從而進入新一輪經濟周期。2002—2005年,經濟增長率分別為9.1%、10%、10.1%和10.2%,今年預計為10.5%左右。這樣,2000—2006年,本輪周期已連續7年在適度經濟增長區間內(8—10%左右)平穩較快地運行;其中,2003—2006年連續4年在10%略高的位勢上平穩較快地運行。我國經濟增長出現的這一新軌跡,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發展史上還是從未有過的。
二、本輪經濟周期中三次比較集中的宏觀調控
在本輪經濟周期中,針對投資和經濟增長偏快而比較集中地出臺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已進行了三次。
第一次比較集中的宏觀調控是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重點是2004年4月至5月。主要針對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部分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過熱。
第二次比較集中的宏觀調控是2005年上半年,重點是2005年3月到4月。主要針對房地產投資規模過大等問題,出臺了“國八條”、“新國八條”、“七部委八條”等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
第三次即目前這次比較集中的宏觀調控,是今年4月至9月。主要針對房地產業發展中仍然存在的突出問題,以及針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并呈加劇之勢,出臺了“國六條”、“九部委十五條”等措施,央行于2006年7月和8月兩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等。
一般說來,宏觀調控是針對經濟運行中的“熱”或“冷”,為熨平經濟波動而不斷進行的。但就針對經濟運行中投資和經濟增長偏快而比較集中地出臺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而言,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前四個經濟周期中,都是一個周期對應一次比較集中的宏觀調控。例如,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個周期中,對應著1979—1981年的宏觀調控;在第二個周期中,對應著1985—1986年的宏觀調控;在第三個周期中,對應著1989—1990年的宏觀調控;在第四個周期中,對應著1993年下半年—1996年的宏觀調控(1997—1999年是為了抵御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克服國內需求不足而進行的宏觀調控)。在這幾個周期中,通過宏觀調控,經濟增長率由周期波動的上行道隨即轉入下行道,由經濟過熱轉入經濟調整。為什么在我國以往的經濟周期中,比較集中的宏觀調控都是一次性的,而在本輪經濟周期中,卻呈現出多次性或多階段性的特點呢?
三、以往周期中的一次性宏觀調控
以往經濟周期中的宏觀調控,都是在經濟增長已陷于全面過熱而難以為繼時,才不得不進行的被動調整。
總結中外歷史上經濟波動與宏觀調控的經驗教訓,可以得出一些帶有規律性的認識。就經濟波動的一般規律而言,經濟增長過熱,即我們常說的“大起”,必然導致隨后的“大落”。因為在“大起”中,對資源的高消耗和環境的高污染,造成對經濟正常運行所需各種均衡關系的破壞,這就必然引起“大落”。“大起大落”的要害在于“大起”。宏觀調控的目的正是為了防止“大起大落”,平抑經濟波動,而其中的關鍵又在于及時地防止“大起”,也就是及時地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或由局部過熱轉為全面過熱。這就要求及時地“削峰”,使經濟增長率的“峰位”處于適度增長區間的可控范圍內,不致因經濟增長過熱而損害資源和環境,損害經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我國以往經濟波動中經常出現的“大起大落”,就是因為沒有很好地認識和把握上述經濟波動的一般規律,沒有及時地防止“大起”,而是等到經濟增長率已沖出上限警戒線,經濟增長已陷于全面過熱而難以為繼時,才不得不進行被動調整。如1978年經濟增長率高達11.7%;1984年經濟增長率高達15.2%;1987年經濟增長率高達11.6%;1992年經濟增長率高達14.2%。在這種調整中,需要集中和大力度地出臺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較大幅度地收縮經濟增幅,以迅速扭轉過熱局面。因此,也呈現出峰谷落差明顯、一個周期對應一次比較集中宏觀調控的特征。
四、本輪周期宏觀調控呈現出多階段性的特點
(一)宏觀調控水平的提高和經濟波動態勢的變化
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進行的、本輪周期第一次比較集中的宏觀調控,不像以往那樣在經濟增長率已突破11%之后,才進行被動調控,而是在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部分行業出現局部過熱時,就適時適度地進行了主動調控。這一主動調控,由于見事快、動手早,防止了經濟增長由局部過熱轉為全面過熱,避免了我國歷史上多次因“大起”而導致“大落”的局面,由此延長了經濟周期在適度高位運行。
2005年上半年,針對房地產投資規模過大等問題進行的本輪周期第二次比較集中的宏觀調控,又一次防止了局部問題轉為全局問題,進一步延長了經濟周期在適度高位運行。
由于宏觀調控水平的提高,以及由此形成的經濟周期適度高位的延長,即經濟波動態勢的變化,就有可能在一輪10年左右的中程周期內,出現幾次經濟運行的偏熱或偏冷,即幾次小峰或小谷。因此,需要針對一輪周期內的不同階段和問題,適時適度地多次進行相應的微調。今年第一季度和上半年,經濟增長率分別上升到10.3%和10.9%;而第二季度單季與上年同期相比,經濟增長率高達11.3%,經濟運行再次出現偏快傾向。為了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使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良好勢頭繼續保持下去,在本輪周期中實施了第三次比較集中的宏觀調控。
(二)宏觀調控體制基礎的變化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在本輪經濟周期中,宏觀調控的對象自主化和市場化了。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的擴張與收縮主要取決于中央政府自身的行為。中央政府用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進行擴張,又用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進行收縮,自己調控自己。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和企業,大家“齊步走”。在控速降溫的宏觀調控中,經濟增長率很快就會降下來。
而現在,宏觀調控的體制基礎已發生很大變化。宏觀調控的對象之一的市場經濟主體——企業,其投資和經營行為已自主化和市場化了;宏觀調控的另一個重要對象——地方政府,它們的一些經濟行為也自主化和市場化了。企業和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有一個觀望、認識、理解、消化的過程。
與此同時,目前我國的經濟運行仍帶有原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些特點。例如,一些地方政府盲目大干快上的擴張沖動而又缺乏必要的約束,一些企業包括民營企業的投資實際上只負盈不負虧的軟預算約束等。此外,還帶有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一些特點。例如,企業行為的非法制化、非理性化等。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與經濟增長“高溫”降速較慢相對照的是,經濟在“升溫”時卻又升得很快。特別是遇到“十一五”規劃開局之年、黨政領導班子換屆、舉辦奧運會等推動因素,經濟增長很容易趨向過熱。這表明在本輪經濟周期的適度高位運行中,宏觀調控主要是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而在目前體制環境下,這不是一次性比較集中的宏觀調控就能萬事大吉的,而要不斷緊密跟蹤經濟形勢,針對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新問題,適時適度地多次進行微調。
(三)房地產業特殊性和經濟增長制約因素的變化
在本輪經濟周期中,房地產業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柱產業,直接涉及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切身利益;同時也是宏觀調控所涉及的重點產業。目前,我國以住房為代表的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既是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加快的結果,也是居民購買力不斷積累的結果。在未來二三十年內,房地產業的發展對于相關產業乃至整個經濟增長具有持久的推動力。
當前,在以房地產業及其相關產業所帶動的經濟增長中,制約經濟增長的因素也發生了新變化。過去每當經濟過熱時,主要的瓶頸制約是煤電油運和重要原材料的短缺;而現在隨著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發揮,這些短缺因素已逐步緩解,這有利于經濟在適度高位的持續運行。
在由房地產業及其相關產業所帶動的經濟增長中,制約因素已由煤電油運和重要原材料的生產短缺轉換為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制約。自然資源的制約,包括土地資源、能源資源、礦物資源和水資源等的制約。如果房地產業及其相關產業發展過熱,引起自然資源的大量消耗和環境的嚴重污染,仍然會給整個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危害。因此,對房地產業的調控需要慎重操作,既不能力度過大,使其一蹶不振;也不能力度不足,使其盲目擴張。特別是對住房這種特殊商品,我們的調控經驗還比較欠缺,也有賴于一系列法律法規和管理規則的不斷完善。這決定了對房地產業及其相關產業的調控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的,而要不斷有節奏地進行。
五、政策涵義
為延長經濟的適度高位運行,在一輪周期中針對經濟運行中的問題多次進行微調,并不意味著前一次微調沒有起作用,也不意味著這次之后不再需要新的微調。國際上,也有這種在一輪周期中多次進行微調的先例。例如,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國經濟經歷了長達120個月的超長增長。以年度GDP增長率看,這個經濟周期的適度高位運行歷時9年,其中就出現了4個小峰。美聯儲針對經濟運行中幾次出現的過熱苗頭,多次進行微調,保證了美國經濟的持續超長增長。
在多次性微調的情況下,宏觀調控的目標取向或評估宏觀調控的效果,不像過去那樣是使經濟增長率大幅度地壓縮下來,而是使經濟增長率不“冒頂”,即不突破適度增長區間的上限(從我國目前國情看大體為11%左右),從而使經濟在適度高位平穩運行的時間盡量延長。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經濟學部副主任、經濟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