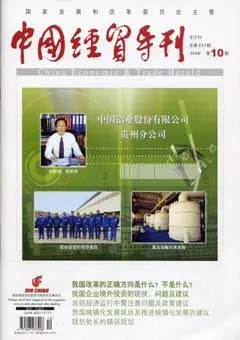謹防城市化的消極后果
中國社科院拉美所課題組
城市化是國家發展和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時也有可能帶來某些負面后果。我國正處于城市化的加速期,拉美國家城市化進程中有些經驗教訓很值得關注。
一、堅持走城鎮化道路,防止“大城市化”
“城市化”與“城鎮化”不過一字之差,卻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方針。拉美地區城市化最主要的失誤就是“大城市化”、“超大城市化”。1950—1980年,拉美經歷了一個城市化加速期,城市化率由41.6%提高到65.6%;1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由7個增加到48個;有10多個國家的首都分別集中了全國人口的40—66%;墨西哥城的人口由300萬人增加到1500萬人,圣保羅由250萬人增加到1350萬人,里約熱內盧由290萬人增加到1070萬人,布宜諾斯艾利斯由530萬人增加到1010萬人,都成為世界級超大城市。這種城市化模式帶來了大量負面后果。
大城市具有就業機會多,城市基礎設施相對充足等優勢,不僅對移民吸引力大,自身擴張成本也低。但若不加節制,到一定時候就會面臨資源、環境及各種社會問題的嚴重困擾并為此付出高昂代價。中心城市對于推動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發展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功能,人們因此往往過分熱衷于發展這類城市。但是,這類城市如果集中了過多的人口和資源,就會對邊緣地區的發展產生排斥效應,進一步加劇地區發展的失衡。中小城鎮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產物,凡是偏遠、落后地區,城鎮發展也滯后。堅持城鎮化道路就要求在加快地方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努力推動中小城鎮的發展,這應是我國城市化的主要著力點。我國是人口大國,搞“大城市化”、“超大城市化”既不現實,其后果也不堪設想。
二、堅持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并舉,擴大城市就業
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否實現向城市的有效轉移,關鍵是能否在城市獲得就業機會。拉美國家在解決城市就業問題上有兩點教訓:一是對正規經濟部門,特別是現代工業部門創造就業的能力估計過高;二是忽視非正規就業。在戰后年代,拉美的主流思想是片面強調進城農民應在城市正規部門獲得“生產性就業”,看不起,甚至排斥非正規就業,如對自主創業規定過高的“門檻”和繁雜的手續,對非正規就業不給予政策支持等等。實際情況卻是,包括現代工業在內的城市正規經濟部門根本滿足不了就業需求,上世紀50—70年代,拉美城市非正規就業的勞動力始終占城市就業勞動力的20%左右;90年代以來,拉美各國就業彈性普遍下降,城市新增就業崗位更是60%以上靠非正規部門提供。事實證明,擴大非正規就業是解決城市就業問題的一條重要渠道,我國也不例外。
非正規就業在傳統上有兩大缺陷,一是不受國家勞動法和其他法律的約束;二是沒有社會保障。鑒于非正規就業的重要性,有必要采取相應措施促進非正規經濟和非正規就業的健康發展。第一,把非正規就業納入國家勞動法和其他相關法律的管理范圍,對諸如壓低工資待遇、惡意拖欠工資、任意延長工作時間、不提供必要的勞動保護、使用童工,等等,都應予以法律追究,以保護非正規就業職工的合法權益。第二,把非正規就業職工逐步納入相應的社會保障計劃之內。第三,要努力改變人們傳統的擇業觀念。第四,繼續加大對自主創業的政策支持力度。第五,加強對非正規經濟活動的工商行政管理。
三、防止出現大規模城市貧民窟現象
拉美地區平均城市化率已達75%,部分國家已超過80%。城市化率高,人口過分集中于大城市,城市就業問題又解決得不好,結果造成大量城市貧困人口。這些貧民買不起住房,大都在城鄉結合部自行搭建簡陋住所,逐漸形成大規模的貧民窟,其帶來的后果難以盡述。2001年,拉美城市貧民窟居民達到1.27億人,占城市人口的1/3。貧困人口在大城市大量集中,也是拉美國家容易發生社會動亂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要選擇適合國情的農業發展模式
城市化一頭連著工業化,另一頭連著農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產業化把農村富余勞動力排擠出來。工業化推動城市經濟發展和城市規模擴張,把農業剩余勞動力吸收過來。一頭“吐出”,一頭“吸進”。“吐出”得過多、過快,城市化就可能“超前”或“失控”;“吐出”得過少、過慢,城市化就可能“滯后”。拉美城市化過程出現“無序化”局面的歷史背景是,大量土地和其他農業資源被少數人壟斷,大大壓縮了中、小農戶的發展空間。拉美各國(除古巴外)政府不是通過社會變革去調整農業資源的配置,而是提倡走農業“技術現代化”道路,即提倡私人大地產通過機械化、化學化、綠色革命等演變成現代大型私營農牧場,進一步減少農業勞動力。拉美各國政府幾乎都把農村向城市移民視為緩解農村社會沖突的“排氣閥門”,于是就出現大規模的自發移民潮。由于農業發達地區都是大型農牧場,人煙稀少,不利于中小城鎮發展,落后、邊遠地區人口相對密集,但中小城鎮發展又受到限制,這股移民潮就沿著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的“三級跳”路徑,迅速向大城市集中。拉美國家人均農業資源擁有量比中國多得多,但沒有被有效利用。占主導地位的大型農牧場雖然產業化程度較高,但經營依然粗放,效率比較低。
綜觀發達國家的農業經營模式,基本上都以家庭農場為主,既符合農業生產自身的特點,效率也比較高。我國基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農業精耕細作、單產高的傳統不能丟,可選擇的農業經營模式可能是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拉美國家在認識上存在這樣一種傾向: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例越低,農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越小,現代化程度就越高。這種簡單模仿發達國家的傾向是認識上的一個誤區。我國如此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都要在較短時間內靠城市化這個單一渠道來解決是不現實的。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適度加快城市化結合起來,是現階段我國最可行的選擇。
五、要防止“隱性城市化”
“隱性城市化”是指,農村勞動力在非農化過程中未能實現地域轉移,或者雖然實現了地域轉移,但其農民身份并未改變。這就涉及到我國農民進城打工的現象。當前我國的城市每年為上億農民提供工作機會,是對社會的一大貢獻。而且,這種農民工大規模在全國范圍內流動的現象短期內恐怕不會消失。這就涉及到兩個問題。
第一,農民工長期在城市做工,為城市和企業做出貢獻,但他們除了得到一份工資收入外,享受不了一般市民和企業職工的福利待遇。城市和企業所享受的這種“低廉的勞工成本”并不是真實的成本,諸如農民工的住房、醫療、養老、培訓、子女受教育等本屬于勞動成本的支出,卻要由農民工自己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來承擔。這種情況長此下去,城市和企業自然愿意維持現狀,而不愿讓農民工成為市民和正式職工,從而會阻礙城市化取得實際進展。
第二,取消戶籍制度限制對于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必要的,但還不夠。農民移居城市面臨的更大困難是城市的“生存風險”,即一家人究竟能不能在城市生存下來。如果對這種風險沒有把握,他們也不會輕易脫離農村,而寧愿繼續目前這種外出打工的方式,這同樣會影響城市化取得實際進展。
(執筆:蘇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