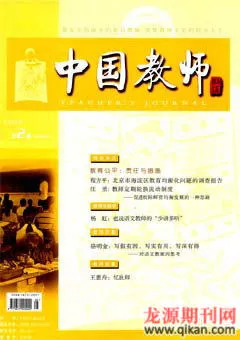教育,請關注孩子的“冒險力”
一個留美歸來的老師曾經感嘆,中國優秀學生和北美的優秀學生最顯著的差別在于他們所定下的目標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對于中國學生來講,目標必須是現實的,是短期可以實現的。他們追求肯定可以實現的目標,過著風平浪靜的生活,盡管艱苦勞碌,但是可以沿著一條確定的軌跡平穩地駛向成功的彼岸。對于北美學生來說,其目標是他們狂放不羈、自發性的美夢。
筆者無意于指責我們的孩子平庸,而頌揚人家的孩子的偉大。但從民族性格上看,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冒險”的誤解和“冒險”精神的缺失。
冒險是一種精神狀態,是對未知神秘世界探尋和勇于戰勝各種難以料想困難的動力。從遠古時代起,從人類初來到這個世界時,我們的冒險活動就開始了。人類每一次生存空間的擴大,都是冒險成功的結果。成功的冒險,緣于人類對新環境的適應;失敗的冒險,緣于人類對新環境的不適應。冒險就是犯難,它是知難而上的一種力,這種力不安分守己,守成就是對它的限制,它需要往生疏的地方尋找表現的機會。通過冒險,人類早已躍入太空,但也因此付出相應的代價。迄今為止,美國已發生了兩次航天飛機爆炸事件,航天英雄長眠于太空。如何看待太空“冒險”呢?從里根總統在“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出事后三天后發表的電視講話中可窺見一斑:“英雄之所以稱之為英雄,并不在于我們稱贊的語言,而在于他們始終以高度的事業心、自尊心和鍥而不舍地對神奇而美妙的宇宙進行探索的責任感,去實踐他們真正的生活以至獻出生命。”“在痛苦中我們認識到了一個意義深遠的道理:未來的道路并不平坦,整個人類前進的歷史是與一切艱難險阻斗爭的歷史。”既然冒險是必要的,那么犧牲也就在所難免。害怕冒險是當不了真正的英雄的,害怕冒險的民族注定難以躋身于世界強民族之列。
瀏覽網頁,發現中國的冒險家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令人汗顏。在當代,“徒步走中國”的余純順算一個,“萬里長江第一漂”的堯茂書算一個,再往前找大約就是鄭和、徐霞客、張騫他們了。倒是那些金融投資的、房地產方面的冒險家為數不少。相比之下,像挪威這樣的北歐小國在近代就出了第一個到達南極的阿蒙森、第一個孤舟闖太平洋的海爾達爾、第一個橫跨格陵蘭冰原的南森等等一大批國際級探險之“星”。“神五”升空,楊利偉成為進入太空的第一位中國人,我們自豪,但是我們的自豪必須用理智加以約束——在楊利偉之前,已經有412位外國宇航員將他們的腳印留在了太空。珠穆朗瑪峰是世界第一峰,位于我國和尼泊爾交界,但世界上第一個登上珠峰的人是新西蘭的埃德蒙·希拉里!如果中國的高山、長河多要由外國人來征服,這是中華民族恥辱和悲哀。人類不僅和自然界之間存在競爭,在自己的內部也存在著競爭。今天征服了你的精神,明天就可能征服了你的軀體。人類的演進史暗含著一條驚人的邏輯:沒有冒險力與征服力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
玫瑰需要種植和培育,小草卻不需要,因為它是自然界最固有的東西。孩子們的冒險力就如同這小草一樣,用“培養”“澆灌”這樣的態度對待,實在是高抬它了。它不需要。它需要的是尊重——你甚至可以拔它,但請你千萬手下留情,不要把它拔光了!冒險力是各種陽剛力量和智慧的復合。而我們的學校和家庭,除了在不能替代的學習與考試外,孩子生活方面的壓力已經被他們萬無一失地用“愛”給消解了。最為極端的是中考、高考時家長的表現:換著花樣給孩子做好吃的,守著孩子讓他休息好,更有甚者,曾有家長讓人設法去捉考場附近大樹上的知了,甚至寫信建議飛機停飛……生活在“真空”中的孩子連一般的抗壓能力都不具備,基本的生存適應能力都沒有,還能奢望他們為了國家利益去冒險嗎?馬卡連柯曾告誡人們:“一切都讓給孩子,犧牲一切,甚至犧牲自己的幸福,這是父母所能帶給孩子的最可怕的禮物。”我們傳統的文化中,講究安逸,安土重遷,“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這些都是對自由表現的冒險力的束縛。教育是需要氣度的。當前一些學校為了“安全”,所有的出游都被視作洪水猛獸,甚至連校內的組合器械都拆了,踢足球也被作了限制。這是一種因噎廢食的“不作為”行為。汽車發明以來,死于車禍的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多,能禁止開汽車嗎?我們要允許學生“冒風險”,進行一些他們必須進行的活動。學校應該在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的前提下,落實安全責任,不留事故隱患,對師生進行各種形式的法制教育、安全教育,以生動活潑的形式讓學生、教師了解、理解競技體育活動中存在的潛在危險,并使之認真遵守學校的各項規章制度及體育運動規程,但卻沒有理由剝奪學生自由活動、接受鍛煉乃至“冒險”的權利。我們的責任是監督、教導學生,使之免于可以預見的傷害。
一位法國父親的做法能夠給我們以很好的啟迪。他的兒子課余酷愛高山滑雪,而且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他的希望是有朝一日代表法國去出征冬季奧運會。一個寒假,兒子和他的女朋友去阿爾卑斯山滑雪,雙雙墜落在600多米深的峽谷里,再也沒有回來。這位父親曾經告誡兒子,高山滑雪是一項極其危險性的運動,但卻從來沒有阻止過他,他一向尊重兒子的愛好,因為他愛兒子。愛意味著尊重一個人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對孩子最好的“攙扶”就是“不扶”。如果不是出于自私的話,我們有什么理由壓抑孩子自由生長的包括“冒險”在內的各種“人”的力量呢?當然,我們所應尊重的“冒險力”不惟是肉體和氣力上的,日常的生活及學習中,我們也應該允許并提倡孩子們靠知識、靠智謀、靠信息去一次次走進、走出“險境”。一般情況下,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礎,精神、能力發育不良的人是不配也不能去實踐人類光榮而艱巨的冒險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