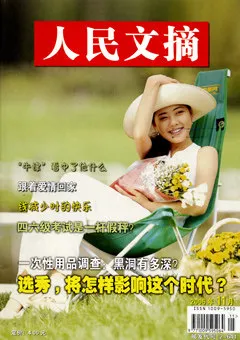10萬韓國人在北京
在北京,提到望京,人們會很自然地與韓國人聯系起來。如今那里聚居著大約6萬韓國人,加上五道口等地區,在北京居住的韓國人已接近10萬,成為在北京外籍居民中規模最大的一個族群。
到中國去
1992年,中韓建交,一些韓國企業的駐華代表陸續來到北京,禹東碩就是其中之一。他所在的公司專門為在華韓國企業代理廣告。在禹東碩看來,韓國人大規模遷居北京,與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不無關系,在那之前,生活在北京的韓國人不超過1000人,基本都住在亞運村附近的外國人公寓里。
“以前長安街兩側有很多韓國企業的廣告牌,都是我們公司代理的,1998年前后,許多企業支撐不下去了,被迫撤離。”金融危機也增加了韓國人的就業和生存壓力。禹東碩注意到,與韓資企業的退潮相逆,一些普通韓國人涌向中國。
穩健而強勁的經濟增長,足夠的工作機會,高性價比的生活,這些對韓國人越來越有誘惑力。因為有著相近的文化傳統,而且與中國的朝鮮族居民語言相通,韓國人在華生活顯然更容易適應。到中國去學語言,去學中醫,甚至去做生意,許多韓國人為此心動,這其中就包括深相好。
1999年,深相好到北京工業大學商學院學習了一年漢語,學成之后,他和哥哥一樣選擇留在北京經營餐館。
望京韓國住戶第一人
1997年,作為北京市最大一塊規劃住宅區,望京的開發隨著望京新城101號樓的崛起而展開。由于開發商恰好是禹東碩的朋友,他被邀請到101號“試住”。
“那時候,周圍連柏油路都沒有,下雨天到處是爛泥。”禹東碩清晰記得,窗外滿眼是被推土機掀開的土地,只有零星幾個未來得及拆除的水泥乒乓球臺,表明這里過去并非蠻荒之地。最初的幾個月,101號樓如同戳在大工地上的樁子,突兀而孤單。
兩個月以后,第一班公交車開通了,三個月以后,望京新城101號迎來了第二戶韓國房客。“我們并不認識,但后來成了好朋友。”
到2006年,望京地區的總人口接近20萬,韓國人就占了大約三分之一,望京是北京第一個以中產階級為目標消費人群的高檔社區,其價位雖超出普通北京市民的承受力,對于在華韓國人而言卻極其便宜——同等面積的二室住宅,亞運村外國人公寓的月租金為2000美元,而在望京只需要2000元人民幣。在韓國,雇一個保姆的費用,折合成人民幣至少要每月8000元,而在北京,請一個朝鮮族保姆只需要800元。與禹東碩一樣,多數在華韓國人的工資,遠不如在韓國從事同等工作。“但是,在中國每月掙3萬,或許可以剩下2萬,而在韓國即使能掙8萬,大概也要花掉8萬。”一個更為直觀的例子,讓禹東碩深感北京生活的低成本——從漢城打車去機場,需要大約人民幣1000元,在日本東京,這筆費用大概為2000元,而在北京,則低于100元。
巨大的誘惑不斷吸引著新的追夢人。他們或者舉家搬到北京,或者獨自奮斗,他們與這座城市、這里的人接觸,交流。
未過磨合期的鄰居
來自天津的石婕是北京某外企的白領,禹東碩入住望京的那年,她也在望京西園四區擁有了自己的房子。過去的三四年間,她眼看著一批批“老望京”搬走,一批批韓國人住進來。如今,石婕在望京西園三區又買了房子,原來的住宅租給了韓國人。
房子租給韓國人之后,石婕總是擔心中國鄰居會和他們發生矛盾。“韓國家庭一般孩子多,有的還在屋子里滑滾軸,四區房子隔音又差,會顯得非常吵鬧;韓國青年夜生活豐富,有時候到了半夜,馬路上還有韓國青年人騎著大馬力的摩托車,樓下的大鐵門,偶爾會有伴隨著韓語的砸門聲。”
細微的文化差異也會導致誤解。
韓國人習慣于把鞋子放到房門外,而中國鄰居覺得這占用了門前的空間,污染了空氣,甚至感到晦氣——按中國人的習俗,只有家里死了人,才會把鞋放到屋外;韓國人的生活垃圾一般放在門口,中國鄰居最初會把它理解為不講衛生的行為;韓國人在外訂餐,吃完了會把碗放在門口等待餐廳服務生拿走,中國鄰居覺得這樣有礙觀瞻。
韓國人也需要“忍受”中國人的生活習慣——他們不明白廣場上為什么有那么喧鬧的大秧歌,為什么中國家庭炒菜有那么重的油煙,為什么中國人會把寵物狗帶進電梯……
禹東碩說,在這種混居社區,肯定有一個融合的過程,而他強調,韓國人更應該努力適應當地的習俗。
夢里不知身是客
2003年,深相好與北京女孩李娜完婚。夫妻倆把這個中韓合壁的家也安在了望京。
在韓國人最為集中的望京西園三區和四區,韓國住戶的比例甚至超過了50%。在社區周圍,韓國用品超市、餐館、棋館、跆拳道館一應俱全,甚至可以買到專供韓國人使用的國際長途電話IP卡。望京地區的路標有望以中、英、韓三語標識……即使一個對漢字、漢語一竅不通的韓國人,生活在這樣的社區也絲毫不會感到人在異國的落寞。
反倒是生活在望京地區的中國人,偶爾會懷疑自己身在何處。在望京社區論壇,一位叫“與狼共舞”的業主曾發帖說:“我坐420(公交車)回西園三區,過花家地那站的時候,突然發現車上除了我、司機、售票員外都是韓國人。猛然間發現我竟然像外國人,呵呵。”
禹東碩一直讓女兒就讀于中國人的學校,而他本人也結識了很多中國朋友。為了學好漢語,家里一直沒有安裝衛星電視接收器。“將來老了,我會到海南生活。離開祖國太久,我已回不去了,因為那邊再沒什么朋友。”
身在北京,韓國人也會時時流露對這座城市的感情。2001年7月13日的晚上,得知北京申奧成功,望京新城居民自發組織了歡慶隊伍,人們盡情地舞蹈、歡呼、游行,活動一直持續到凌晨時分。而這次活動的組織者,就是居住在小區里的韓國人。
一個更開放的都市,無疑要迎接越來越多的外國鄰居,并學會與之融洽生活。有專家指出,比起那些高聳的建筑群,它才真正代表著“國際化大都市”的概念。
目前在青島、大連、上海、煙臺、沈陽、天津等中國沿海城市,也有越來越多的韓國人聚居,并形成自己的群落。每年7月,北京、上海、青島、沈陽等城市的韓國人還要分別組隊,進行在華韓人足球友誼賽。
“韓國人從來沒有這么大規模地遷居國外,我們也需要學會怎么適應新環境。”身為望京“韓國村”的入住第一人,禹東碩從不掩飾對北京、對望京的好感,人在異國,他更愿意選擇入鄉隨俗。
(舒 靜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