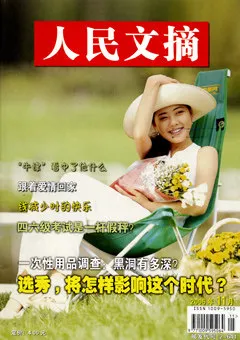有時,放棄也是一種前進
鋼琴大師陳宏寬,生于臺灣,長于德國,執教美國,定居加拿大,現任上海音樂學院首任鋼琴系主任。這個“國際人”年輕時曾創造了極其輝煌的成就,在世界最重要的九大鋼琴賽事中,他榮獲了七個大獎,是國際樂壇上獲獎最多的鋼琴家之一,并與世界上諸多馳名樂團和指揮家合作,被加拿大皇家音樂學院授予“最佳藝術家”稱號。
鋼琴家除了訓練、表演、教學,還需要休閑。喜歡動手的陳宏寬的休閑方式就是做手工,具體地說,是做木匠,修葺自家的老房子。陳宏寬借助一架折疊梯子,登上了高高的房頂,一番敲敲打打,大功告成,他滿懷喜悅雙手扶著梯子往地面撤退,突然,梯子的伸縮部位失靈了,折疊的部分倏地掉落了下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像斷頭臺的鍘刀落了下來”,不偏不倚,正中他的雙手!
悲劇就是這樣發生的。
彼時,陳宏寬的大腦一片空白。隨后,他的手腫了起來,他甚至不敢去醫院,便用腫脹的雙手去摸索鋼琴,但是,漸漸地,他的手越來越不聽使喚,后來醫生告訴他,他的右手患了“肌張力不全”,從此將告別鋼琴演奏。
讓一個鋼琴家失去他靈巧敏捷的手,豈不是讓他去死嗎?陳宏寬嘗試了很多方法,但效果甚微。疼痛如豐沛的雨水淋漓而下,苦悶、絕望和恐懼像張黑色的大網纏繞著他,以致他面對鋼琴,那臺被他視為生命的,是他歡樂源泉的,情人一樣的鋼琴,都感覺不舒服。一年半后,已經被逼上絕路的他一下釋然:“要是真沒辦法,放棄就好了。”
輕輕抖落。
好似禪悟。
放棄——悲壯而智慧。
我通過電視看到了這個訪談,聆聽了這段溫情而深沉的回憶。這個長發藝術家除了對音樂懷著朝圣般的虔誠,還有著戰士般頑強的斗志,孩童般澄明的心地,以及哲學家一般的理性。
“心有所系毫發重,心無旁騖一身輕。”陳宏寬將鋼琴徹底放棄了,不練,不想,不看。就這樣波瀾不驚地過了一年多,然后,他開始一個手指一個手指地練習按動電視遙控器上的按鈕,奇跡發生了,神經組織方面的內傷漸漸痊愈,他再次獲得了演奏的能力。1998年,他在美國的獨奏音樂會上曲驚四座。之后,他彈完了貝多芬32首奏鳴曲,并在世界巡演,成為貝多芬作品的權威演繹者之一。
陳宏寬是全世界一萬五千個同類病例中,極少數復原的一個。為什么很多鋼琴演奏者手指受傷后無法恢復?那是他們無法放棄。
全在心魔!
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走不出困境,就在于舍不得放棄。我們緊緊咬住設定的目標和眼前的蠅頭之利,意亂神迷。殊不知退一步海闊天空。譬如,當柔媚的河流遇到兇悍的沙漠,它將憑借風的力量,變成水蒸氣,看似放棄,卻在跨越沙漠后,再度形成一條浩浩蕩蕩的河流。暫時的放棄,不是潰敗,不是逃避;而是休整,是養精蓄銳,是欲擒故縱。陽光的輕塵里,世事流變,等待的,是更加凌厲的反攻。
有時候,放棄也是一種前進。
(張 揚摘自《江淮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