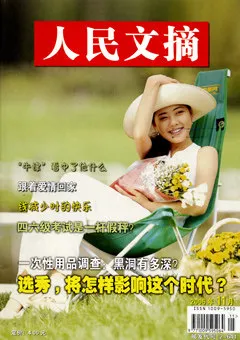被遺書改變的人
幾年前,歡鏡聽被賦予了一個很特殊的使命——代死囚寫遺書。也正是因為如此,歡鏡聽得以忠實地記錄了一百多名死刑囚犯最后的心聲。
第一次因害怕而劃破稿箋紙
這是歡鏡聽第一次近距離地接觸死刑犯。幫死囚寫遺書的程序很簡單,就是讓死囚口述,歡鏡聽記錄,寫好后再由歡鏡聽念給死囚聽,得到他的認同。
一張藍色床單平整地鋪在死牢的木地板上,一疊雪白的稿箋紙整齊地碼在床單上。床單這頭坐著歡鏡聽,床單那頭坐著艾強(化名),一個不滿20歲的死刑犯。
“我那個筆尖連續劃破了好幾張稿箋紙,寫不下去。”當兩個人面對面坐下來的時候,歡鏡聽異常緊張,而艾強卻很輕松。當艾強看到歡鏡聽因為手發抖而劃破幾張稿箋紙的時候,他笑了,對歡鏡聽說:“哥啊,明天上路的是我又不是你,你害怕啥子啊。”歡鏡聽看著艾強笑,自己也笑了:“我坦誠地跟他講:‘我是第一次給死囚寫遺書,我是感到很害怕。’”
為了緩解緊張的氣氛,歡鏡聽拿出一包香煙。歡鏡聽告訴記者:“我知道,被判了死刑的人,基本上都要抽煙。可我自己不抽煙。”當歡鏡聽把香煙遞給艾強后,那個小伙子卻激動起來,他說:“哥,謝謝你,謝謝你。”這讓歡鏡聽有點莫名其妙,艾強跟他解釋說:“這是死牢里的一種習俗,一個死刑犯在被執行死刑之前,如果旁邊有一個人能夠給他一支煙抽,就表明他來世可以投胎到一個好人家。”
而那時候他也是囚犯。
文學青年商海失足入獄
1965年12月中旬,歡鏡聽出生于四川省永川縣朱沱鄉金翠村,1971年遷居重慶江津德感壩五里坡。
白天胸前掛著一個打了補丁的布書包,身后背著豬草背簍,夜晚腰間夾著書本,肩挑籮筐到江津火車站撿煤炭花,其間常常通宵達旦在火車站的月臺上倚著一根電線桿,借助路燈看書——歡鏡聽就這樣度過了童年。
在站臺邊開書店的大伯是歡鏡聽走進文學殿堂的領路人。13歲那年,他對大伯說:“將來我要當作家。”
14歲,歡鏡聽在火車站當起了挑夫,16歲,他進入當地一家建筑工地打小工。空閑之余,他開始寫小說、短文。17歲生日那天,他以“啼鳴鳥”的筆名將自己寫在作業本上的處女作《滾》,投向了一家文學刊物。歡鏡聽19歲加入重慶市作協,成為重慶市最年輕的作協會員;21歲,他成為四川省作協會員。
1987年,歡鏡聽來到海口,他撞進了海南《天涯》雜志社。雜志社沒有收留他,主編送了他一本薄薄的小冊子《美麗的寶島——海南》。回到旅店,歡鏡聽閱讀這本幾角錢的小書。不經意間,他發現了一個商機。在接下來的十多天里,他包租了一輛三輪車,跑遍海口大大小小的書店,把積壓的小冊子一堆堆地搜羅到海口秀英港出售。歡鏡聽在海南賺到了第一桶金。
手中有了錢,歡鏡聽退出郵市。1991年10月中旬,歡鏡聽應邀出任原先工作過的集團公司下屬的商貿公司總經理,并兼任兩家工廠廠長。在理順了公司的內部事務后,歡鏡聽與一位老職工遠赴新疆、青海等地,重點清討過去被拖欠、詐騙的貨款。
導致他走向失足的,也正是這次西北之行。為了彌補虧空,歡鏡聽在若干的假單據上簽上自己的姓名,讓會計入了賬。
1996年10月15日,歡鏡聽被江津市人民法院以侵占公有財物罪判處兩年有期徒刑,押往重慶看守所服刑。
為130名死囚寫遺書
入獄不久,歡鏡聽擔任了專門負責監區安全的犯人后勤組長,和死囚打交道。
艾強是歡鏡聽第一次代寫遺書的對象。歡鏡聽說:“他的遺書是留給母親的。”歡鏡聽告訴記者:“他跟我講了他連一場正正經經的戀愛都沒有談過。”
“艾強走了以后,我對生命有了一種新的看法,什么叫生命啊,生命只有活著的時候它才叫生命。”
在服刑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里,130名走向刑場的死刑囚犯在歡鏡聽面前留下了他們最后的遺言。
“在記憶中一直震撼我靈魂的,是偷錢資助貧困女大學生的小偷王一。”
王一是永川黃花山至城區路線的“丁冬”(小偷)。1990年,他因為“光顧”了窮得身上只有5毛錢的女大學生珍珍,心生憐憫并觸發俠義“壯舉”。當晚,他在一火鍋店用刀向服務員“借”了50元錢郵寄給珍珍。可是他偶然在車上再次與珍珍相逢,并將當天所得全部悄悄放進她的衣兜時,珍珍的一聲“抓偷兒”卻讓王一惹來乘客的毒打,最終一步步走向不歸路。
“王一臨刑前沒有一絲害怕和悔恨,反而還念叨珍珍‘不知道她現在的生活如何,是不是還像過去那樣窮?’”歡鏡聽說,聽完王一的故事,自己的眼眶禁不住濕潤了。“出獄后,我更大的收獲是學會了最大限度的寬容和理解。”
1998年3月23日,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根據歡鏡聽獄中的良好表現,為他減刑半年。1998年4月5日,歡鏡聽出獄。
出獄后改姓為“歡”
出獄后,歡鏡聽尋到了一條與傳統案例完全不同的寫作方法,那就是“敬畏”。不是敬畏那些已經化成朽骨的死囚,而是對生命的敬畏,也就是說,活著,讓生命鮮活地存在下來,這是世界上最有尊嚴、最幸福無比的事情。
這就是歡鏡聽那本《我為死囚寫遺書》的寫作動機。
2001年9月,江蘇文藝出版社印發單行本,書名改為《死囚檔案》。這是歡鏡聽第一次公開出版的作品專著。2004年,《死囚檔案》榮獲第二屆重慶市文學創作獎。
2003年,他將原本是筆名的歡鏡聽改作姓名。歡鏡聽是中國第一個姓“歡”的人,“百家姓”之外創造出一個新姓氏:歡。
(蔡梗民摘自《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