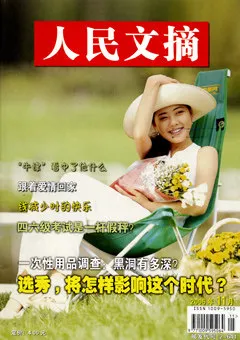人生最后的簡樸
法國總統戴高樂是一代偉人,他在晚年寫下了《我不需要國葬》的遺囑:
“如果我在他鄉去世,請應將我的遺體運回家鄉,不要舉行任何公開儀式。
我的墓地就是己經安葬了我女兒安娜的那塊墓地,我妻子將來有一天也要安葬在那里。
碑文是:夏爾·戴高樂,生卒年。別的什么都不要。
儀式將由我的兒子、女兒、女婿、兒媳,在我辦公室人員的協助下進行安排,務必使之極其簡單。
我不要國葬,不要總統、部長、兩院各單位和行政、司法機構參加。
只有法國軍隊可以以軍隊的身份正式參加,但參加的人數應該很少。不要音樂,不要軍樂隊,不要吹吹打打。
在教堂里和別的地方,都不要發表講話。
在議會里,不念悼詞。
舉行儀式時,除了給我的家屬,給我的那些曾經榮獲解放勛章的戰友,給科隆貝鎮議會留出席位外,不留其他任何席位。
法國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的男女,如果愿意的話,可以把我的遺體護送到我的墓地,以此作為對我的紀念。
但是,我希望在安靜的氣氛中把我的遺體送到我的墓地。
我事先聲明,拒絕接受法國或外國的勛章、晉升、稱號、表彰和聲明。
無論授予我什么,都是違背我的遺愿的。”
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這位被世人譽為拯救了法蘭西的英雄去世了。人們按照他的遺囑,買了價值僅為72美元的橡木棺材將他安葬。他的靈柩由村里兩個乳酪制造工人、一個農民、一個屠宰工人的助手抬著,送到他的出生地——科隆貝鎮雙教堂村的墓地。他的墓碑上寫著:“夏爾·戴高樂,1890至1970。”一點也沒有對他生前的豐功偉績的宣揚,一點也沒有與他的偉大業績相應的豪華陳設。
音樂大師赫伯特·馮·卡拉揚譽滿全球,擁有數十億美元的財產。他生前曾表示,自己的后事一定要簡樸。他要安息在自己的故鄉,因為家鄉的乳汁滋養了他。
他的墓前沒有石碑,只有一個既未雕刻也未油漆的十字架,上邊刻著他的名字。墓地種滿了白色的小花。并非小鎮上的人們不想為這位偉大的同鄉建一座墳墓,而是卡拉揚的后人堅持,只有遵從死者的意愿,才是最好的紀念。
文學大師托爾斯泰的墓地在距離莫斯科不遠的亞斯納亞莊園。墳墓是一個極普通的小土丘,旁邊立著一個極普通的小木牌。小木牌上刻著兩行字:“請你把腳步放輕些,不要驚擾正在長眠的托爾斯泰!”
這個周圍除了茂密的參天大樹,沒有其他任何明顯標志的小土丘,每天都吸引著全世界數以千計的人來到這里。他們靜靜地站在土丘前,獻上一束野花,表達自己由衷的崇敬。所有來這里的人,都輕輕地從小土丘前走過,仿佛擔心會真的驚醒了沉睡中的托爾斯泰。
這些人生最后的簡樸,不僅無損于這些偉人和大師的光輝形象,反而使他們的靈魂更加高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