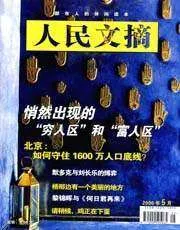北京:如何守住1600萬人口底線?
盡管擁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車,但6年前大學畢業后輾轉來到北京的楊月卻時常萌動逃離這座城市的想法。
33歲的楊月出生在湖南一個山村,現任一家廣告公司的中層經理。雖然工作小有成就,但他愈發覺得這個中國人心中的夢想之城其實并不適合生活。“生存問題解決后,你會強烈感受到大城市的弊病:大氣污染、交通擁堵、房價昂貴……”他說。
北京人口壓力問題成焦點
楊月的苦惱其實也是北京城市管理者的尷尬,他們必須面對一個兩難選擇:是冒被指責“歧視”的風險對外地人實施“準入”制度,還是繼續承受人口膨脹給城市資源帶來的過度壓力?
在2005年召開的北京“兩會”上,接受審議的《北京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中提出,北京“力爭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1600萬”。
根據最新統計,2005年北京常住人口已經超過1530萬人,這意味著北京未來5年人口增長的計劃空間只有70萬。北京該不該控制人口?該如何守住1600萬人口底線?上述問題成為人們最關注的熱點。
公平理想與現實壓力之爭
北京市市長王岐山在“兩會”期間向人大代表坦言,北京市面對沉重的人口壓力。他在向大會作“十一五”規劃綱要報告時,每遇重大問題語速都放慢,聲音都加重,當念至人口問題,他的語調明顯變得緩慢、沉重。
他說,現在北京的問題是人口呈現機械增長,過去五年增長了166萬。中央對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中提出的2020年城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按照目前發展速度,要完成中央提出的目標是成問題的,即便是對照“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的未來5年內人口控制在1600萬左右的目標,也是只會“右”不會“左”的。
2005年1月北京召開“兩會”期間,市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惟英的一份題為“建議實行人口準入制”的提案被置于前臺。提案認為,外來人口的大量盲目調入,使北京的可持續發展難以為繼,資源的承載量受到挑戰,“建議摸清北京實際需要人才類別,用準入制度合理引入,控制人口無序流動,保持人口與城市資源的平衡,保證北京的可持續發展。”
此言甫出,立刻引起強烈反響。報道當日,新浪網相關評論即達到海量,張惟英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輿論也很快分為正反兩方。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張惟英說出了一個誰都無法否認的事實,即北京膨脹的人口正給城市帶來巨大壓力,一個城市各方面的承載量是有限的。如果處理不當造成本地人口生活質量的下降,也會產生新的不公平。”
另一方面,張的“控制人口”觸動了很多外地人的敏感神經。在網絡上,網民們言辭激烈地對張的觀點進行嚴厲批評。網民小魚寫到“提議看來冠冕堂皇,還用了可持續發展等最為時髦的詞匯,卻忽略了憲法基本的平等精神。憲法明確規定凡具有中國國籍的人都是中國公民,難道北京是北京人的首都?難道中國公民進入自己國家的首都還要先申請準入?”
同為北京市政協委員的萬建中教授認為,把北京需要的人放進來,把那些“無序涌入”的人擠出去,這種對外來人口區別對待的方式,現在看來實在“是個霸王規定”,他覺得限制窮人來北京生活,其實就是歧視。
資源無法承受之重
因為會上的提案,在去年的很長時間里,張惟英都承受著巨大的精神折磨。家里時常接到騷擾電話,攪得日常生活也不安定。但事實上,張的觀點卻似乎一直得到官方強有力的回應——就在爭論發生不久,深圳市便出臺一系列文件,打破延續25年的人口開放政策,提出對外來人口將施行控制政策,遏制暫住人口過快增長;此外,北京也終于態度明朗地提出“控制人口”。
有人評價,北京人口問題之爭,體現了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激烈搏弈;而北京新的人口政策,則顯然代表了官方極力在維護社會公平和應對現實壓力之間尋找平衡的苦心。
在關于人口控制的討論中,雖然人們仍存在諸多分歧,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北京的資源已經面臨承受極限。
據悉,目前,對北京的城市承載力影響最大的是水資源。北京現在水資源是人均300立方米,這是全國1/8,是世界1/30。據預測,北京2010年的可用水量僅為37.7億噸。雖然有人提出“南水北調”能大大緩解北京水資源匱乏的情況,但是學者經研究發現,北京市現在人口增長的速度規模過大,“南水北調”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在北京,很多人感到生活質量越來越不如意。由《商務周刊》和零點公司2005年12月21日聯合發布的“2005宜居城市排行榜”中,北京的排名由2004年的第3位跌至第15位。
雖然人們對排行榜的評價體系表示懷疑,但這個結果說明北京在宜居等方面確實存在一些問題。
2004年,市政府投入350億元改善交通狀況,但堵車依舊是這個城市幾乎隨處可見的一個“常景”。楊月每天從郊區的家中開車到單位,18公里的路程通常需要1個多小時,而大量無車居民則要忍受公交車的擁擠。
日益飛漲的房價使普通市民改善居住條件的想法遙不可及。2005年前11個月,北京商品住宅期房平均價格將近6800元/平方米,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僅為12000余元。此外,國家環境分析測試中心的研究表明,北京汽車尾氣污染損害超過了沙塵暴。
北京市副市長張茅坦言,一方面,北京已經不能再采取計劃經濟時代的方式來限制人口,因為確如很多人提到的,北京是全國人民的首都;另一方面,北京正面對嚴峻的人口和環境資源壓力。
北京的困境其實是中國大城市面臨的共同問題。建設部的統計顯示,北京作為首都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成為眾多外地人追求夢想的首選之地,城市規模從三環“攤大餅”式地擴大到了六環。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專家王凱認為,中國在尋求城鎮化過程中,過度渲染了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的勞動力吸納功能和經濟輻射能力,使這些城市陷入了資源日益緊張的困境。
事實上,無論如何,對于北京來說,控制人口都將是政府未來五年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然而令人欣慰的是,王岐山的說法給人們帶來了積極的信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單純是一個經濟指標,也是一個和諧的概念。構建和諧社會,要靠發展、靠改革、靠理想信念。任何矛盾化解都有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崔 含摘自《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