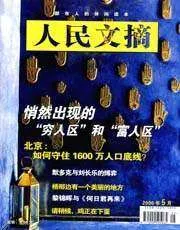李安:成功背后的寂寞
2005年的世界電影可謂“李安年”,然而在耀眼奪目的光環背后,卻是一顆寂寞多年的心靈。
父親送我的惟一跟電影有關的禮物
李安祖籍江西德安,1954年10月23日出生于廣東潮州,父親給他起名“李安”,一來是老家在江西德安,二來是他的父親去臺灣的時候幾乎是死里逃生,所乘坐的輪船為“永安號”。
書香門第的李家家教極為嚴格,甚至在逢年過節時還行跪拜禮。父親對兒子的希望是考上大學,成為詩禮傳家的楷模。可是兩度聯考落榜(第二次數學甚至交了白卷),讓父親對他的人生前景非常憂慮。這種憂慮直到他憑《臥虎藏龍》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之后還偶有流露。最終,懷著電影夢的李安考進了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影劇科。在那里,李安得以施展他演藝方面的才華,甚至還獲得了一個小小的演員獎。可是父親對他這個選擇一直很擔憂,直到讓他保證畢業后出國深造,才同意他繼續留在藝專。
藝專的日子輕松而快樂。李安經常在臺北漢口街的臺映試片室看當時風行的歐洲藝術電影。二年級的時候,父親送給他一臺8毫米攝影機,這是父親一生送給他的惟一一份和電影有關的禮物。他用這臺攝影機拍了一部18分鐘的黑白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懶散》,正是這部短片幫助他申請進入了紐約大學電影系。
失樂園:異國求學的日子
然而,父子的沖突并沒有結束。兒子經常參加臺灣環島公演,又黑又瘦的“鬼樣子”讓父親怒火中燒,他們之間開始發生嚴重的言語沖突。1978年,李安做了一個讓父親十分憤怒的決定:報考了美國的戲劇電影學校。這讓父親很無奈,因為這并不違反當初讓他出國深造的“命令”,只是,他不能接受兒子竟然想去從事沒多大出息的娛樂業。他可能為此耿耿于懷了一生。后來所取得的電影成就,在李安看來,并沒有給父親帶來觀念上的改變:或許他一生都沒有接受過兒子已經成了一個電影導演這個事實。他們的互相沖突和妥協,盡管給李安的青少年帶來了嚴重的心理障礙,卻使他獲得了對中國父權文化、親情紐帶的深刻思考和復雜情感。據李安回憶,他始終不知道父親對他的電影的真實態度。
1985年2月,李安把所有東西打包成8個紙箱,準備回臺灣發展。就在行李運往港口的前一晚,他的畢業作品《分界線》在紐約大學影展中獲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兩個獎項,當晚,美國3大經紀公司之一的威廉·莫瑞斯公司的經紀人當場要與李安簽約,勸他留在美國發展。
沒想到,這一留就是6年無所事事和孤寂難耐。
隱忍在紐約郊區的6年
李安的太太林惠嘉是美國伊利諾大學的生物學博士。他們1978年在一次留學生的聚會上相識、相愛;1983年,李安與林惠嘉在紐約舉行了一場中西合璧的婚禮。婚后兩人分隔兩地。林惠嘉是一個個性很獨立的女人,從來不麻煩別人。大兒子出生時,太太居然沒有通知李安,讓醫院誤以為她是一個棄婦。二兒子出生時,她也把李安趕出了醫院。有關這位“酷”太太的逸聞趣事非常多:李安的《喜宴》獲得金熊獎時在柏林給太太打電話,她為從睡夢中被吵醒感覺很不爽,怪李安小題大作。拿了奧斯卡小金人后,李安和太太到華人區買菜,有位臺灣來的女人對林惠嘉說:“你命真好,先生現在還有空陪你買菜!”不料當即遭到李安太太的搶白:“你有沒有搞錯呀,是我今天特意抽空陪他來買菜的。”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男人過了30應該是已經有了一份穩定恒久的事業養家糊口了,可是,李安卻成為家庭的累贅,一家人只靠林惠嘉微薄的薪金度日。
為了緩解內心的愧疚,李安每天除了在家里大量閱讀、大量看片、埋頭寫劇本以外,還包攬了所有家務,負責買菜做飯帶孩子,將家里收拾得干干凈凈。每到傍晚做完晚飯后,他就和兒子一起興奮地等待“英勇的獵人媽媽帶著獵物回家”,這常常令林惠嘉覺得很溫馨很感動。
林惠嘉也有過絕望的時候,但她仍然堅持不讓李安做無謂的糊口工作。有一次,李安偷偷地開始學電腦,希望能比較容易地找一份工作。沒過多久,被林惠嘉發現了,她很生氣地說:“學電腦的人那么多,又不差你李安一個!”在妻子的堅決反對下,李安只好打消了出去找工作的念頭。林惠嘉知道,李安真的只會拍電影,別的事情不會也不感興趣。她對丈夫的才氣十分肯定,她相信丈夫一定會成功的。
灰心至極的李安偶爾也幫人家拍拍小片子、看看器材、做點剪輯助理、劇務之類的雜事,還有一次去到紐約東村一棟很大的空屋子去幫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會遇上土匪闖進來搶劫。”
回憶起這段難熬的生活,李安至今仍然十分痛苦:“我想我如果有日本丈夫的氣節的話,早該切腹自殺了。”就這樣,在拍攝第一部電影前,李安窩在家中當了6年的“家庭主男”,練就了一手好廚藝,就連丈母娘都夸獎:“你這么會燒菜,我來投資給你開館子好不好?”
從《臥虎藏龍》到《斷背山》
執導了幾部西方電影后,李安反而愈發覺得自己是個東方導演。
他想回到他所熟悉的中國題材。這時,他想起了《臥虎藏龍》。
讓他難以預料的是,《臥虎藏龍》會這么復雜,這么難搞!從開始籌劃,到奧斯卡結束,整整折騰了3年!
2001年,《臥虎藏龍》成為華人導演中第一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電影,該片在全球引發了一股瘋狂的中國武俠熱,以至于比他成名在先的張藝謀等人紛紛步他后塵,拍攝自己心目中的武俠電影,沖擊奧斯卡,但最終無人能達到李安的圓滿結局。
之后,就是《斷背山》。這是一部解脫般的電影,純凈、虛空,仿佛帶著一種朝圣的心態。就在這部電影的準備階段,和他對峙了一輩子的父親去世了。他仿佛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虛空。他忍住悲痛,遠赴加拿大牧場,全心投入《斷背山》的拍攝,希望能撫平自己內心的傷痛和疲憊。支持他繼續獻身電影的,是父親臨終的遺言“你不應該放棄,應該繼續拍下去。”
這是這個孤獨寂寞的電影導演此生惟一一次聽到父親這樣鼓勵他。
(李 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