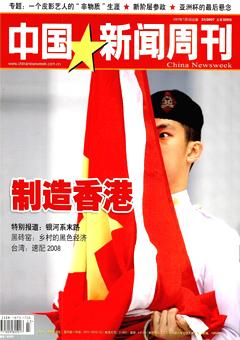董橋:香港文化要反省與回顧
蘇 琦 孫 展
沒有根的感覺,對一個香港的讀書人來說,總有一種失落感。這種懷舊的文化,對一個人的人文修養來講,如果沒有對自身成長是有影響的
家學淵源得正宗國學心傳,受教臺灣成功大學外語系后,又負笈英倫取西學真經,其后返港在報界浸淫多年,兼有報人、文人、學人的身份,一路走來,董橋已然成為香港文化的一個標桿性人物——香港文化中的中西合璧、傳統與現代兼備的特質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表達。
在訪談中,董橋以一個文化守望者的姿態,對包括香港在內的兩岸三地自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流變進行了精辟的解畫,既有對傳統中國文化味道式微的些許失落與無奈,也有對多元文化成長可能性的樂觀期許;既對港人國語水平的提高滿心歡喜,又對其英文水平的下降感到憂心;在豁達看待香港文化尷尬轉型的同時,又對大陸的“大文化”形態和讀經讀史熱提出清醒的認知。
在一個煙花繁華之地守望文化是寂寞的,但董橋自言:貢獻就在于點點滴滴把這么多年來用心追求的知識,傳授出來。有沒有人看,是另外一回事,“這是盡了你自己的一個本分。”
沒有了根,總有一種失落
中國新聞周刊:你怎么看香港回歸以來文化方面的變化?
董橋:我個人感覺,最大的區別,就是回歸以后香港人基本上都會講國語了。每個人都在很努力的學講國語、聽國語。這點我很開心,我的孫子現在很小都會講國語了。
我還在推(動)一個事情,就是國語課應該用國語教,國語讀,這樣以后他寫東西會很方便。香港中文這么多年受到一個很大限制就是文字不行、語言不行。現在這一關克服過去就很好了。
中國新聞周刊:那英語呢?在回歸前后你擔心港人的中文水平,近來好像更擔心他們的英文水平?
董橋:英語嘛,過去可能很好,回歸之前已經不太行了,一蟹不如一蟹。有的學生還是很好,但一般的水平不如殖民地早期我們的前輩,甚至沒有我們這一輩的英文好。
香港呢,我覺得它的價值就在于是一個世界之窗。如果香港人不能好好地保持這種優勢,就比較麻煩。怎么保持呢,你必須語言要強,英文要好,懂得越多國的語言越好。
中國新聞周刊:好像不少人對香港文化能否保持香港性有所擔心?
董橋:香港性,要兩個方面看。香港性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中文不夠好。好的一面就是除了中文之外,必須懂得一門或一門以上的外國語言。
這一點很重要。我最希望內地的人能多懂一兩國語言,因為這對他個人的生活情趣會增加一些。你看的東西不會局限在一個框框里面,會知道別國家的一些東西,這對一個民族的品味、趣味、情趣,甚至于整個社會的安寧、和諧都有幫助。
中國新聞周刊:在80年代你寫的《這一代人的事》,曾提出“文化中國”的概念,感覺你當時有一種很濃重的家國情懷。現在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日益熱絡,是不是就是“文化中國”這個概念所涵蓋的呢?
董橋:我講文化中國的時候,內地“文革”過去了,感覺到中國文化出現了一個斷層。我跟余英時先生經常通信,我們那時就討論中國情懷,我在《明報月刊》的時候就弄了期“中國情懷”“文化中國”,余先生給我寫了比較軟性的,比較感性的文章。
為什么我們會這樣做呢,我們心目中的中國情懷或者文化中國,是希望大家再回味一下老中國的東西。所謂老中國包括那么多年的歷史,也不用太長,清末民初就很夠了,那種味道就在那里。這種東西太多了也不行,太多了人就迂腐了,你完全沒有呢,就等于一個人完全在一個非常現代化的辦公室或住家里面,感覺都是電腦,很冷感的時代,沒有后花園。
中國新聞周刊:沒有根。
董橋:沒有根的感覺。那時我們說文化中國或中國情懷,主要是看到大陸文化斷了一層,看到臺灣在走自己的本土化。這種情形對一個香港的讀書人來說,總是有一種失落的感覺,好像現在兩邊都不到岸。
臺灣那時還有一種老民國的味道在那里。就它那兒最濃。現在你問我關于香港文化,我還是提倡文化的一種反省,一種回顧,不光是中國文化,也包括西方文化在內。所以這些外國書(指著桌上古版英文書籍),我有能力的話都要去搜。這種懷舊的文化,這種古老的文化,對一個人的人文修養來講,如果沒有的話,是有影響的。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兩岸三地的文化發展,是更融合了,還是更分立了?
董橋:越來越散,越來越雜,這是好事情,多元。
中國新聞周刊:但是從曾經共同擁有一個文化母體的意義上來講,還是挺讓人傷感的。
董橋:不要傷感,應該開心才對。要這樣散掉才好,才會冒出一些人物出來,不然總在一個天地里鎖著。
傳授是知識分子的本分
中國新聞周刊:香港文化十年來,有沒有吸納新的元素?
董橋沒有。有一個比較不好的現象,就是英國人那邊的淵源斷掉了,中國這邊的淵源還沒有建立起來。我覺得現在香港人,就像港府整天講的,經濟最要緊,賺錢最好。這就像鴉片,讓你在別的方面不求上進。當然我不能說這個不好,但是不能光這樣看東西。
中國新聞周刊;內地也存在這個問題。
董橋:是啊,看一個社會不能光這樣看。我覺得現在香港的官員中國文化的素養太弱,太不夠,這很可悲。我看香港的領導層要經過二三十年,幾代之后(中國文化素質)才會好一點。
現在一些香港官員對內地沒有認識,也沒有感情,對臺灣也沒有感情,他總是一個香港,自我中心論,自我感覺非常良好,這很糟糕。
中國新聞周刊:香港的文化是該吸收大中華文化以后創造出一個亞文化,還是要回歸到某種傳統?
董橋:凡是這樣的說法,我都不會同意。因為你把文化弄成一個整體去思考,等于是要有一個中心思想在那里去引導它。其實文化像水一樣,不能凝固在一起,不能用一塊東西變成另一塊東西,讓你去塑造。文化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有的時候自然就有了,你開窗看到外面樹木突然都綠了,鳥都回來叫了,你就很開心,那就是文化,可是你不能說這些東西是意識形態。
比如文化我是偏向早年老民國,像林語堂先生,梁實秋先生,那一輩的人,包括現在內地還在世的黃裳先生,楊絳先生。這些是文化,但是你不能把他們歸類,你不能說啟功先生代表整個北京的文化,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不能把文化變成一個整體去考量,而是讓社會有這樣一個氣氛,讓一百個人中有四個人、五個人、六個人關懷這個東西,那就夠了。
中國新聞周刊:那么現在推動香港文化繼續向前走的動力源在哪里?
董橋:早年,錢穆先生來香港辦學,辦新亞書院,他的學生是余英時,這樣一代代傳下來。現在呢,你要想在香港的大學里面找到能夠在學術上真鎮得住場的人
物,不多,大陸這樣的人也不多。這是我們要面對的現實。
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不論做什么工作,你的貢獻就在于點點滴滴把這么多年來用心追求的知識,不管是舊的、新的,傳授出來。有沒有人看,是另外一回事,是盡了你自己的一個本分。
連這一點,現在也不容易了。因為電腦。我們那一代人,真是一頁一頁、一本一本看,學問都是這樣,幾十年累積下來。現在寫文章,不用翻書,電腦一按,什么資料都在里面了,你只要照著抄就行了。跟我們這些人一本本去看哪里一樣,你說這不是非常悲哀嗎?
可是我想必須經過這段時間。現在包括美國、英國,新作家的東西我不一定看的下去,看兩行就覺得不太對,因為感覺沒有了,還是看回我們那一代人的東西。
中國新聞周刊:所以你現在經常寫一些關于筆洗、如意,這些過去文化的符號性的東西。
董橋:對,我有時是故意這樣寫的,因為看年輕一代都是電腦,讓人很擔心。
中國新聞周刊:你對內地目前出現的讀經熱、讀史熱,以及祭奠孔子等怎么看?
董橋:有人做我不反對,但你要我提倡、發揚這個東西,那就不必了。
不要有所求,就讓它自然推過去。最要緊的是要培養一個人的誠信,進行公民教育,以及做人一些很基本的東西,這是很必要的。但不要把它歸為一個組、一堆人或是一個團隊的精神。不要希望要把它弄成一個怎么樣的大趨勢,因為我看很難,除非用高壓手段。
中國新聞周刊:之前我們跟陳果導演聊,他說香港處于一個相對尷尬的時期,也如你所言,舊的已經去了,新的淵源還沒有建立起來,轉型的方向感也不是太明朗,那么你對香港文化的走向有何預判?
董橋:我都是個人的看法,風水輪流轉。所謂十二年一個運,香港人的競爭力以后都會不如內地。內地有一些年輕人,我看到的、認識的,真是很用功,很苦干。
七八十年代長起來的這代人太幸福了,沒有吃過什么苦。50年代、60年代我們剛來香港的時候,日子很難過,那是要拼的。日子難過對一個人、一個社會來說是好事,只要有一個信仰,凡事付出一分力,就會有半分收獲。
《獅子山下》那種精神,當時肯定有,后來就沒有了。因為興旺了。
所以回歸之后,我有一個比較復雜的想法,或者說一個比較矛盾的想法,就是香港的下一代人,除了盡量爭取到外國讀書、去看看外國的情況以外,更要多一點去內地看看,包括臺灣。這是中國人幾代人在那里成長的地方。香港人如果沒有這種感受,可能會是一種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