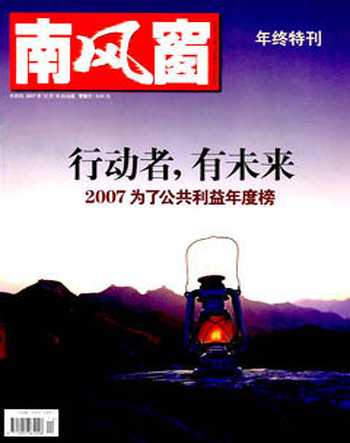環境危機:陰影下的希望
田 磊
對于在中國從事環境保護事務的官員、科學家、NGO們來說,2007年是一個最壞的年份,也是一個最好的年份。
這一年,中國環境事故頻發,太湖藍藻爆發,洞庭湖鼠災驚人,淮河治污10年之功歸于失敗,南水北調最易修建的東線工程因污染而推遲,昆明的滇池、武漢的東湖這些中國地圖上最著名的城市明珠無一例外地因污染而成為城市的心病。
以廈門PX風波和太湖藍藻帶來的無錫飲水危機為標志,生態問題正在成為公共危機,2007年的環境事故為生態危機不能被“置之不理”、而是已經涌入了中國現代政治的核心地帶這一事實提供了充分的證明——假如需要證明的話。
執政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總書記胡錦濤把“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列為今后執政面臨的八大問題之首,環境保護領域的官員們前所未有地走到了中國政壇的前臺,從事生態研究的科學家們再也不用為課題發愁,環保NG0在中國從未像今年這樣活躍。
環境到底有多糟?
對于中國環境問題的描述,從來都不缺乏糟糕的字眼,從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銀行、各種各樣的研究機構到中國的環保總局,總會不斷地有一連串的數據來佐證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毒氣和污水的國度。
歷史上成為主要工業強國的國家,無一不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中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成長為經濟強國,因此,幾乎不需要太多的數據,就可以推斷出,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也一定是史無前例的。
但是,這些統計數據和宏大的概念從來都不曾讓國人清晰地意識到,我們的環境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直到2007年5月30日這天,中國環境保護史上發生了兩件引人關注的事故。一件是:廈門市政府宣布投資海滄的PX(對二甲苯)化工項目緩建。另一件是:太湖藍藻引起無錫市自來水發臭,數百萬市民斷水。數萬市民的上街游行和搶水風潮讓兩起純粹的環境事故迅速地演變為公共危機,從而引起了輿論的關注和政府的恐慌。
PX與藍藻,一個事關清新的空氣,一個事關干凈的水。PX背后是中國重化工業方興未艾的背景,市場上對二甲苯供不應求、價格高居不下的現實,讓廈門這樣美麗的海濱城市也無法拒絕經濟發展的誘惑。太湖藍藻背后則是太湖流域16年治污的毫無效果。中國東南沿海兩個美麗又富庶的城市,那里的市民才過上溫飽富足的體面生活,馬上又要為獲取清新空氣和干凈水的生存權利而抗爭。
污染并不局限于工業發達的東南沿海,明底,安徽巢湖再現藍藻,水質降為重度污染;西部的云南省,滇池治污8年,湖水依然發臭,擋不住藍藻頻發;百湖之市武漢的龍陽湖死魚泛起,漁民們將武漢卷煙廠武漢水務集團和武漢城市排水發展有限公司告上法庭,索賠近240萬。
和往年不同的是,2007年的環境問題很少再有像松花江污染那樣的突發性事故,而大部分都是日積月累的環境危機,這更增加了政府控制的難度。污染正在成為中國公眾需要長期面對的日常負擔,也給執政黨帶來巨大的政治挑戰。
我們生存其間的國土被污染得到底有多嚴重?這不再只是一個生態問題,而更成為政治命題。2007年12月31日,國家將展開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這項普查完成后,政府也許能得到一個相對清晰而理智的判斷,在未來更嚴峻的執政挑戰來臨之前,心里先有個底。
中央政府的決心
政府仍是中國解決環境危機的最大依靠者,現實的選擇方案,將是不懈推動政府更積極地將這種力量發揮出來。
“中央政府的決心是不用懷疑的。”國家環保總局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勇說,2007年可以列為中國環境保護史上最具標志意義的一年,從今年起,環保作為基本國策開始真正進入社會發展的主干線,黨的十七大報告里,一共有五大方面16個地方提到環保,而5年前的十六大報告還僅僅只有6處。
作為環保領域最知名的國際NGO,綠色和平項目總監盧思騁先生也認為,2007年,環境惡化的根源問題得到了中國的中央政府前所未有正視。兩個重要的問題在浮出水面。一個是關乎環境治理與體制中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的博弈,另一個是關乎中國的發展模式——中國需要發展,但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
在傳統的環境倫理學思想中存在著這樣一種看法: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存在一種“以此換彼”的交易關系。正處于蓬勃的工業革命時代的中國,僅僅因為河流湖泊的污染,中央政府真的能下決心用控制經濟增長的方式來減輕污染嗎?經濟增長放緩帶來的很可能是成片的失業、社會的動蕩等執政黨無法面對的后果。
“從短期來講,保護環境和經濟發展肯定是有矛盾的,但是從長遠來說,則沒有矛盾。如果不解決資源環境的利用效率問題,經濟發展本身也很快就會難以為繼。”任勇說,中央政府追求的肯定是長遠利益。
任勇一直承擔著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的一個實證研究項目,主要是對電力行業節能減排的成本分析及經濟影響。“做這些就是為了弄清楚保護環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我們經濟發展的速度。”任勇說,就電力行業而言,節能減排目前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上脫硫設備,二是項目審批上的上大壓小,通過具體的實證研究發現,脫硫項目到2010年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會是負面的,上大壓小則是正面的。
在2007年年初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國務院總理溫家寶48次提到環保問題,到了年尾又出臺了《“十一五”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考核辦法》,將“一票否決制”和“責任追究制”納入其中,中組部參與《考核辦法》的制訂,“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減排目標,納入地方政府政績考核,這些幾乎都是執政黨一貫的政治治理方式中最嚴厲的手段。
內外交困的現實
中央政府治理環境的決心似乎不用懷疑,但下了決心之后又該如何治理?在國際環境交流場合,中國正在遭到越來越多的指責,在《紐約時報》的報道中,不僅東京和漢城的酸雨是由中國的燃煤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造成,就連洛杉磯的微粒污染也是源自中國,環境問題正成為大國領導人時髦的口頭禪,中國的環境危機也不再僅僅是國內問題,而與國際政治連在一起。
“在十七大報告里,對外關系方面居然也提到了環境保護,這還是第一次。”任勇說,十七大報告把環境問題跟政治、經濟、文化和安全并重,這足以說明環保不僅僅是內政了。西方發達的工業國家通常在繁榮之后,就會立即清理環境污染的危害,但是,中國必須在仍處于發展階段,且沒有形成成熟的經濟的時候,就開始清理,這樣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
11月27日,法國總統薩科齊訪華期間,在清華大學的講臺上大談氣候和環境,但誰都聽得出,他更關心的顯然不是深受廢水毒氣之苦的中國國民,而是法國的企業家
們如何從中國的環境治理中謀取更多的商業利益。
他很清楚,沉湎于高速工業化的中國,根本無暇顧及環保產業的研發,跟20多年前,一窮二白的工業基礎一樣,今天中國的環保產業同樣如此,治理污染的技術、設備、模式統統還是要從發達國家來引進,這也是太湖污染的治理,不得不去日本取經;請回日本人的企業和技術之原因。
對外,我們無法分辨有多少人是在夸張中國所遭遇的環境問題,從而謀取商業利益?即使能分辨清楚,也無濟于事。對內,中央政府面臨的更大難題是,如何去管治地方政府真正重視環境問題。
太湖藍藻暴發導致供水危機,無錫市決定兩年內關閉規模以下的化工企業772家,一批“小電鍍”、“小印染”、“小鋼鐵”、“小水泥”等企業也被列入關停名單。預計今年內被關停企業將逾千家。
消息傳出,從全國各地涌來大批招商引資團隊,招引被關停的企業,大部分都是來自中西部地區二等縣市。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深圳,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業在環保標準抬高的深圳無法生存時,紛紛成了中西部地方政府的座上賓。
污染在迅速地向中西部轉移,環境治理并不能在全國形成統一標準,也無法形成統一標準。我們如何去說服中西部地區,引進那些工廠會將你們毀滅,而不是像東部已經經歷過的那樣富庶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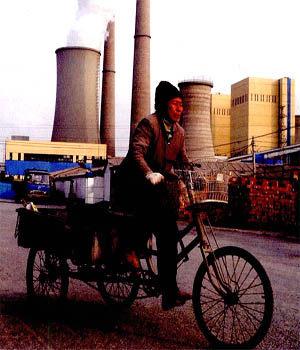
事實上,在科學家們關于環境問題的爭論中,也有著不同的看法,丹麥統計學者隆伯格就曾在《多疑的環境保護論者》中,用詳盡的數據證明過,在已發達國家,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空氣變得越來越干凈,例如倫敦,現在的空氣質量是1585年以來最干凈的。至于發展中國家,污染的確是個問題,不過一旦他們逐漸擺脫貧窮、不必再為饑餓煩惱,就會開始關心環境,污染就會逐漸減輕。
“在中國,這的確有些難,中央強調中西部要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可是地方政府不一定都會這么想。”任勇說,不過,現在生產工藝和產業已經有更先進和清潔的了,如何找到新的發展模式,才是最重要的。
政治治理之外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在中國不是新問題,環境保護不過是一個新的領域。面對挑戰的時候,執政黨習慣于命令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鄧小平當年成功地迫使中國懶散的官僚政治重新重視經濟增長,今天的執政黨又將如何迫使已經沉迷于經濟增長的地方官僚重視環境保護?
廈門PX事件清晰地告訴我們,與地方政府的歡迎相反,那些新建的電鍍廠、化學工廠、核能或者生物技術工廠正越來越多地遭遇到直接受其影響的公民和民間組織的抵制。雖然,該項目經國務院批準立項,通過國土資源部建設用地預審,通過國家環保總局環境影響評估,經國家發改委核準通過項目申請報告,但民眾的抵制還是起到了作用,這是整整一年里,中國的環境事務中,最讓人振奮的成就。
在中國,盡管大部分與公共利益相關的政策并未有相應的公眾參與,但是,作為一種趨勢,民主、法治和公眾參與,成為改變現狀的關鍵,而環境領域,則是最好的實踐場,在環境事務上,決策不能只由那些“專家”和政治家去做,必須使公民和新的社會組織參與進來。
對于促進公眾參與,2007年也有積極的進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將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一直以來,雖然中國的環境法中也有對公民權利的規定,比如健康權、知情權、檢舉權、參與權等,但缺乏程序性保障,這些實體性權利根本無法得到落實。
“幫助污染受害者打官司,最大的問題就是根本無法獲取任何有關環境變化的信息,去政府環保部門索要,往往會被極其惡劣的態度拒絕。”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訴訟部部長張兢兢說,“信息公開是所有環境權益的基礎性保障,但目前中國的現狀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也完全不公開,沒有建立一整套完整的體制讓老百姓知道自己是如何被污染的,被誰污染的,污染程度如何?環境信息公開條例的出臺,將從法理上解決目前公眾參與的最大難題。”
在中國,公民、政府、新的社會組織都正在通過被迫面對生態保護運動而獲得了新的活力,這也許是“塞翁失馬”之福,以2007年為起點,環境保護應當被看成是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一種重要資源,而不是它的對立面。
(責編趙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