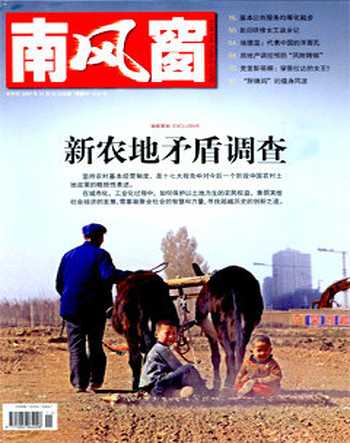學(xué)習(xí)民主執(zhí)政
黃臥云
新的執(zhí)政觀念認(rèn)識到,統(tǒng)攬一切的執(zhí)政方式不但沒有必要、而且與民主格格不入。執(zhí)政權(quán)是對政府行使管理權(quán),但不是唯一的國家權(quán)力。它需要其他權(quán)力的合作。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其基本形式是以政黨為中心、由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的民主政治體制。它是個性與共性的統(tǒng)一。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表明中國特色的個性,但它同時也要體現(xiàn)民主的一般原則。十七大報告提出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把實現(xiàn)黨的民主執(zhí)政作為明確的方向,這必然要對黨的執(zhí)政方式提出新的要求。
朝著民主的方向推進(jìn)政治改革,就是要使中國特色的政治適應(yīng)于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則。一個新的歷史發(fā)展時期開始了。“從農(nóng)村到城市、從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到其他各個領(lǐng)域,全面改革的進(jìn)程勢不可當(dāng)?shù)卣归_了;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從東部到中西部,對外開放的大門毅然決然地打開了。”十七大報告中這段話,既是對以往中國改革開放進(jìn)程的描述也是對就要來臨的改革開放勢頭的展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基礎(chǔ)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這一概念不但對民主做出了限定,也對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做出了限定,即,民主是有中國特色的,同時中國特色也是民主的;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同時社會主義也是民主的。
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都有自己的歷史。中國革命的歷史形成了以政黨為中心的國家治理模式,由政黨發(fā)動革命、組織革命和完成革命,最后走上執(zhí)掌政權(quán)的道路。中國同盟會、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chǎn)黨,先后成為中國近代革命史上領(lǐng)導(dǎo)革命的政黨。在政黨中心型體制中,執(zhí)政黨組織和管理政府,它的領(lǐng)袖作為國家元首行使國家最高權(quán)力。中國革命的歷史還形成了高度集權(quán)的執(zhí)政方式。根據(jù)我國的執(zhí)政實踐和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的執(zhí)政觀念,過去我們一直認(rèn)為執(zhí)政就是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進(jìn)行全面管理。
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一方面形成了強(qiáng)有力的執(zhí)政黨,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yè)發(fā)展提供了現(xiàn)實的領(lǐng)導(dǎo)力量和執(zhí)行力量,但同時,正是全面的國家管理壓縮了社會的民主空間,壓縮了公民的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和文化權(quán)利,也造成了權(quán)力自身的諸多問題。建設(sh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迫切、最艱巨的任務(wù),就是發(fā)展社會主義,對中國社會主義傳統(tǒng)進(jìn)行民主化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chǎn)黨對社會主義的認(rèn)識有了兩次飛躍,一次是由鄧小平一代黨的領(lǐng)導(dǎo)人完成的,認(rèn)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zhì)是共同富裕,為這個替窮人代言、從窮人中崛起的黨指出了新的方向。另一次是由胡錦濤領(lǐng)導(dǎo)的第十六屆黨中央完成的,把促進(jìn)社會公平正義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目標(biāo),明確把民主法治與公平正義聯(lián)系起來,這個從革命中走過來、缺少法治傳統(tǒng)的黨找到了實現(xiàn)公平正義的新途徑。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全面把握了社會主義的實質(zhì)。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想與人類的共同理想是一致的,與人類對公平正義的終極追求是一致的。從根本上說,只有反映人類共同理想的思想體系,才可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zhì)。
民主則與人類上述共同理想不可分割,迄今為止的一切政治探索表明,沒有一種政治手段比民主法治的手段更能促進(jìn)公平和共同富裕的人類理想的實現(xiàn),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能是民主的社會主義,而不可能是沒有民主或民主匱乏的社會主義。
當(dāng)代人要站在時代和歷史的高度,不但為自己這一代人、也為后代人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就不能不以民主政治的共同原則指導(dǎo)制度改造工程,民主共性構(gòu)成民主制度的內(nèi)核,它不會因一時一地的特殊因素而變化,相反,一時一地的特殊因素必須要包含民主內(nèi)核,才能證明自己與民主是兼容的。中國特色的民主是奠基于普遍的民主原則之上的民主。沒有民主共性的“民主”是不存在的,就如不存在沒有人的共性的“人”一樣。一切個性都有其共性基礎(chǔ)。
民主最一般的意義,是指執(zhí)政的狀況和方式,中國人民長期探索民主道路得到的經(jīng)驗是,民主要發(fā)展,關(guān)鍵是執(zhí)政方式要改革。
民主執(zhí)政的共性
民主執(zhí)政不能因為強(qiáng)調(diào)民主的個性而忽視民主的共性。政治決定利益如何分配,民主政治是用民主的方式?jīng)Q定利益分配,公民不但最終控制決定利益分配的公共權(quán)力,而且他們通過直接或間接廣泛的政治參與影響國家政策。由于民主制度從始到終為每一個公民維護(hù)自己的切身利益提供了各種通道,并把一切個體和社會團(tuán)體都置于法律控制之下,它才是最有利于實現(xiàn)社會公平的制度。
政黨是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組織形式,它不但為組織政府和公共決策提供了穩(wěn)定的人員支持和依據(jù),而且在公眾與政府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一方面,政黨把執(zhí)政作為自己矢志追求的目標(biāo),為此要努力獲得民眾支持,要廣泛聽取和收集民眾意見,要盡可能地表達(dá)他們的利益,反映他們的政治意愿,另一方面,民眾通過政黨把自己的意志帶到政府中去。比起他們直接去影響國家政策,利用政黨中介影響公共決策,成本更低,也更富有成效。
從政黨政治的起源上看,執(zhí)政的行為本身就包含了公民參與的民主過程,意味著權(quán)力在陽光下運(yùn)行。中共十六大為中國共產(chǎn)黨做出的如下定位:“從一個領(lǐng)導(dǎo)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quán)而奮斗的黨轉(zhuǎn)變成為一個領(lǐng)導(dǎo)人民掌握著全國政權(quán)并長期執(zhí)政的黨”,表明了執(zhí)政黨的執(zhí)政意識。執(zhí)政有它自身的要求和規(guī)律,每個國家可以根據(jù)自己的具體歷史、文化條件設(shè)定執(zhí)政體制,但它不是沒有任何約束條件地任意設(shè)計。政黨政治在其長期發(fā)展的歷史中,形成了執(zhí)政的一些基本特征,它們是不同國家的民主政府共同擁有的。
其一,執(zhí)政權(quán)力有明確而適當(dāng)?shù)姆秶?fù)責(zé)組織和管理政府;負(fù)責(zé)大政方針、國防、外交;負(fù)責(zé)維護(hù)社會公正。而在更大的社會領(lǐng)域內(nèi),則存在著廣泛的公民自治,他們進(jìn)行自我管理,行使著政治的、社會的、經(jīng)濟(jì)的和文化的權(quán)力。
其二,執(zhí)政黨與人民必須有保持緊密聯(lián)系的方式,為公民表達(dá)觀點(diǎn)和對政治決策施加影響提供大量的機(jī)會。與人民成功地建立密切的聯(lián)系,是執(zhí)政黨的生命所在,也是一切追求執(zhí)政目標(biāo)的政黨的生命所在。
其三,執(zhí)政權(quán)力即使在自己的范圍內(nèi)活動,也要受到不容置疑的約束。在法治理念中,任何一種合法權(quán)力都有其限度,都要受制于其他權(quán)力。一定程度的權(quán)力制衡是民主制度和民主政府一個永恒的要素。
其四,政黨和國家權(quán)力以及其他力量之間進(jìn)行廣泛的政治合作。合作方能更好地推動社會發(fā)展。
建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需要執(zhí)政黨以新的態(tài)度對待執(zhí)政權(quán)力。
新的執(zhí)政觀念認(rèn)識到,統(tǒng)攬一切的執(zhí)政方式不但沒有必要、而且與民主格格不入。執(zhí)政權(quán)是對政府行使管理權(quán),但不是唯一的國家權(quán)力。它需要其他權(quán)力的合作。當(dāng)權(quán)力切切實實成為一種責(zé)任時,切切實實被理解為一種責(zé)任時,切切實實需要擔(dān)當(dāng)責(zé)任時,執(zhí)政者就會感到擔(dān)負(fù)過大過多的權(quán)力是不能勝任的。
新的執(zhí)政觀念認(rèn)識到,限定權(quán)力就是限定責(zé)
任。如果權(quán)力意味著責(zé)任,那么無限的權(quán)力就意味著無限的責(zé)任,顯然它是任何權(quán)力都無力擔(dān)當(dāng)?shù)摹?zhí)政黨將某些權(quán)力移交社會和公民,實際上為執(zhí)政黨減輕了權(quán)力過大造成的許多負(fù)擔(dān),減少了滋生腐敗的機(jī)會,這不會損害執(zhí)政黨的地位,只會加強(qiáng)執(zhí)政地位。它在轉(zhuǎn)移一部分權(quán)力的時候,也就同時轉(zhuǎn)移了一部分責(zé)任。把所有權(quán)力集中在執(zhí)政黨手中,看起來能確保執(zhí)政地位,其實充滿風(fēng)險,因為一旦責(zé)任超過它的實際承受力,它就無法真正對人民負(fù)責(zé)。
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基層民主實踐和在農(nóng)村開展的村民自治活動,就是把原有的一部分政治權(quán)和行政權(quán)讓渡給公民,是朝放棄部分權(quán)力的方向所進(jìn)行的積極嘗試。以人為本的社會,是一個有更多公民自治的社會,它要逐步從權(quán)力本位的沉重歷史負(fù)擔(dān)中解脫出來。用以人為本最終取代以官為本,是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的歸宿。
民主執(zhí)政的制度要求
轉(zhuǎn)變執(zhí)政觀念對轉(zhuǎn)變執(zhí)政方式是重要的,卻不是唯一重要的;觀念影響人們的行為,而制度不但能影響人們的行為,還能約束人們的行為。執(zhí)政黨最終要完成自己的執(zhí)政方式的轉(zhuǎn)變,有賴于建成與民主執(zhí)政相適應(yīng)的必要制度。
在一黨執(zhí)政的政治制度中,執(zhí)政黨務(wù)必解決兩大問題,它如何通過適當(dāng)?shù)慕M織方式與人民保持緊密聯(lián)系,使自己的決策符合人民的意愿?它如何讓人民監(jiān)督自己,確保自己表現(xiàn)良好、不被權(quán)力所腐蝕?這不僅對于持續(xù)執(zhí)政具有極大的重要性,是執(zhí)政黨建設(shè)的重大問題,其實也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shè)的重大問題。
執(zhí)政黨需要與民選機(jī)構(gòu)聯(lián)合。把監(jiān)督政府的權(quán)力交給由民選產(chǎn)生的民意機(jī)構(gòu),保證了民眾有序地參與政治,也為執(zhí)政黨與民眾溝通開辟了渠道。沒有這個渠道,執(zhí)政黨難以確切地接受民意的約束,也不能全面、及時、準(zhǔn)確獲取作為決策基礎(chǔ)的民意。這是一種管理性權(quán)力與一種約束性權(quán)力的聯(lián)合。前一種權(quán)力體現(xiàn)黨的領(lǐng)導(dǎo),后一種權(quán)力體現(xiàn)人民當(dāng)家作主。
十七大報告在論述人民當(dāng)家作主時說到:“人民當(dāng)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zhì)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jiān)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quán)、參與權(quán)、表達(dá)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支持人民代表大會依法履行職能,善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職權(quán),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聯(lián)系,建議逐步實行城鄉(xiāng)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
雖然執(zhí)政黨可以利用各種形式了解民意,如進(jìn)行民意調(diào)查,通過大眾傳媒收集民眾意見、傾聽民眾呼聲,但它們都不能代替專門的民意機(jī)構(gòu)的作用。沒有專門的民意機(jī)構(gòu),民意的表達(dá)和約束往往是分散而抽象的。要求一個政黨一貫自覺地以民意作為決策的出發(fā)點(diǎn),是不符合人類理性的;另一方面,無論權(quán)力還是個人,要求擺脫一切約束以獲得自身最大行動自由,同樣是不符合人類理性的。人們通過接受道德約束和法律約束提升自身文明程度。我們國家當(dāng)前存在的嚴(yán)重腐敗現(xiàn)象證明,黨員干部由于缺少民意的有效約束,往往會從自身利益出發(fā)制定政策,而完全背離公眾利益,對文明是一種倒退,對執(zhí)政黨是一種玷污。
中國共產(chǎn)黨的執(zhí)政地位確立了黨政一致的關(guān)系,政府與民意機(jī)構(gòu)的關(guān)系,實質(zhì)上就是執(zhí)政黨與民意機(jī)構(gòu)的關(guān)系。根據(jù)民主的一般經(jīng)驗,執(zhí)政黨與民意機(jī)構(gòu)是完全能夠和諧共處的,這不但因為它們職責(zé)分明,各司其職,而且因為它們都以民意作為自己存在的基石和權(quán)力源泉。順從民意,體現(xiàn)民意,是執(zhí)政黨持久穩(wěn)定執(zhí)政的條件,而民意機(jī)關(guān)本身就是人民意志的產(chǎn)物,定期選舉約束它的代表成為人民的忠實代理人。共同的基石和源泉使執(zhí)政黨與民意機(jī)關(guān)在法律、政策問題上不會出現(xiàn)不可調(diào)和的分歧。正因為這樣,民主國家執(zhí)政黨的主要政策主張都能通過立法途徑變?yōu)榉伞M瑫r,它們由于都必須受制于法律,它們之間的矛盾能夠通過法律協(xié)調(diào)解決。用法律解決權(quán)力間的分歧,既是實現(xiàn)民主的途徑,也是民主現(xiàn)實的標(biāo)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