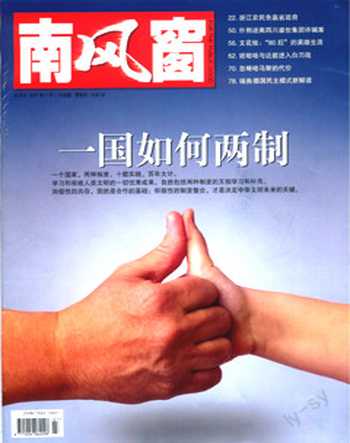培訓中心還要整頓到幾時?
鐘岷源
隨著山西省糧食局在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以建本系統“培訓中心”為名,挪用國家資金修建賓館及“糧神殿”事件被披露,黨政機關興辦培訓中心的問題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在中央紀委等七部委通報的四起違規修建樓堂館所的典型案件中,兩起與培訓中心有關。
據悉,目前中國尚未進入商業酒店序列的各級黨政機關及大型國企的培訓中心,至少超過一萬家。這些利用財政資金所辦的各式各樣的培訓中心,90%以上處于虧損狀態。
第三波整治
在今年掀起“清理風暴”之前,過去的十幾年,就有兩波聲勢浩大的治理浪潮。
早在1988年,國家就頒布實施《樓堂館所建設管理暫行條例》,嚴格“樓堂館所”的建設制度,并且多次發文禁止黨政機關參與修建。各省、各行業,也都相應發文作出呼應。這是第一波的整治潮。
第二波的整治是在2003年。中辦和國辦再次發出《關于繼續從嚴控制黨政機關辦公樓和培訓中心項目建設的通知》,重申并提出從嚴控制黨政機關辦公樓和培訓中心項目建設的要求。整治有成效,但就全國而言,問題依然嚴重,各地興建培訓中心的風氣依舊蔓延。
到今年年初,第三波的整治浪潮席卷全國。“國家不再審批培訓中心的項目。”七部委聯合發文,要求全國范圍內全面清理樓堂館所及培訓中心,并明確要求各省要有一名副省長主抓,重點清查“項目立項、土地使用、資金支出”等關鍵環節,清查報告由七部委共同匯總之后,直報黨中央和國務院。6月20日是清理的最后期限。
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透露說:“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極為關注盲目攀比爭建豪華辦公樓的現象,今年通報的四起典型案件,均由胡錦濤親自點名批評。”
據稱,這種清查力度有其“重要背景”,即與明年我國將加大公務員培訓計劃有關。在培訓公務員隊伍之前,國家相關部門正像清理非法小煤窯一樣清理“培訓中心”,正本清源,這是明年的培訓能否真正取得實效的基本前提。
屢禁屢犯,自禁自犯,三波整治,效果尚無定論,各種深層次問題,反而“浮出了水面”。培訓中心的功能已被嚴重異化,名副其實地成為權力尋租的黑洞、滋生經濟犯罪的溫床,腐敗暗流此地涌動。“培訓中心”作為一種黨政權力的微觀形態,正以其小集團的利益損害整個社會肌體。
權力尋租的隱蔽場所
十幾年來,培訓中心的問題未能有效遏制,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它具有較強的隱蔽性。
在人們的目擊之處,多數培訓中心地處遠郊,甚至遠在異地,遠離公眾的視線,監管部門往往鞭長莫及。這種隱蔽性,使得很多培訓中心漸漸違背建設初衷,成為利用便利條件大肆拉關系、搞錢權交易,請客應酬、公款吃喝玩樂的“安全之地”。
近年的事實證明,大量的腐敗案件,都在這些“既安全又隱蔽”的場所里悄悄進行,下級搞定上級,商人搞定官員。一些單位的領導更是把培訓中心變為權力尋租場,比如,河北省巨貪李真,先后把省國稅局承德培訓中心工程、衡水培訓中心工程、石家莊培訓中心工程等6個工程強行“發包”給朋友,心安理得地從中收受賄賂305萬元;原山西省旅游局培訓中心主任李貴發,在任職期間數次利用職務便利進行貪污和受賄,非法所得財物近50萬元;原湖北省鄉鎮企業培訓中心主任王毛弟,上任一年多就向某建筑商索取回扣77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
另外,由于培訓中心大多為事業單位,可以獲得所屬機關一定程度上的保護,因此培訓中心難以和一般的賓館酒店一樣受到有關部門的監管,從而成為部分領導干部墮落的溫床。比如張二江、胡長清、王寶森“搞腐敗”的地方,就掛著“培訓中心”的牌子。
功能異化的“培訓中心”繁殖腐敗,而腐敗又衍生出更多的“培訓中心”,兩者糾纏共生。
“我的地盤我做主”
“一年到頭,單位組織員工過來開一次年終總結會,平時主要還是內部接待上下級人員,或本單位大大小小的領導。”北京某“培訓中心”負責人向記者透露,“一些黨政機關領導挖空心思要建‘培訓中心,除為培訓干部提供點方便之外,主要是單位的名字往上一掛,那是實力的一種象征,不但讓單位形象‘上檔次,而且給領導面子添光彩。”
培訓中心“孕育”出來的地盤政治,折射出當今的官場心態。
事實確是如此。在一些地方,單位接待條件好壞,已經成為領導者能力高低的一種體現。因此,一些機關的官員往往不遺余力地在各風景名勝區建設培訓中心,同時在內部設施的檔次上不斷升級,以在來訪的各級領導面前留下工作能力強的好印象。更有甚者,少數地方甚至把培訓中心建設作為單位考核的一部分,更加助長了培訓中心的攀比之風。
不過,亦有專家提出,黨政部門熱衷于建設“培訓中心”,其真實動機與古時“臥榻情結”很相似。由這種“臥榻情結”發展而來的現代版是:一旦權力在手,就要自我創設能夠進一步盡顯官威的空間,徹底實現“我的地盤我做主”。
換個說法,其實這種情結就是“地盤政治”。冠有“××培訓中心”、“××大廈”或“××賓館”標牌的大大小小“培訓中心”,實際上是各個權力部門的私家后花園。這些形形色色的“培訓中心”的存在,滿足了各部門機關領導干部的自尊心。在這些場所進行的本部門、本系統培訓,也使某些系統、部門頗有些“權力山頭”的意味。
古時“臥榻情結”的致命之處,在于其將天下人的江山視作了自家的江山;眼下“地盤政治”的致命之處,則在于其將公共的權力視作了部門的權力,給部門執掌的公共權力賦予了濃厚的私密色彩。
如同當年安徽亳州的“閱兵書記”李興民,“為慶升官全城大閱兵”一樣,今年曝光的“糧神殿”事件,也終將成為人們的記憶。但兩起奇聞般的事件,卻暴露出公權力失范以及追逐“地盤政治”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望去,每一座功能異化的“培訓中心”,皆為權力觀扭曲的真實標本。
“賬外賬”、“小金庫”
由于制度的縫隙,培訓中心的“賬外賬”、“小金庫”因此而生。
先說監管制度。按相關的規定,經營性國有資產由國資委管;而培訓中心這樣的非經營性國有資產,卻處于監管空白。培訓中心屬單位所有,雖然不以營利為主要目的,但它們占用大量的財政資金,收支就像“無底洞”,誰也不知道它賺了多少或是虧了多少。賺了,即為單位的“小金庫”;虧了,那是國家的錢。
其次,培訓中心的“小金庫”也在叩問現行的財政制度。
前兩年,審計署曾披露案例,國家電力公司召開內部人事干部會議,短短3天時間揮霍304萬元,人均耗費2.4萬元。事后,會議主辦者為掩蓋真相,通過旗下的“培訓中心”對會議費用進行“技術處理”。
顯然,因為制度的疲軟,培訓中心成
了部門和企業轉移資金、利潤的渠道,而由此生成的“小金庫”,被用來違規發放干部職工的獎金、福利,甚至還用作支付領導的個人開支,使培訓中心成為一些單位負責人吃喝玩樂的逍遙地。
不僅如此,一些培訓中心之所以建得“富麗豪華”,也是為了轉移資金的需要。在很多地方,最豪華的培訓中心往往歸屬那些掌握較多行政權力和經費的部門。而這些部門如果不興辦培訓中心,不將培訓中心豪華化,他們的行政權力和掌握的經費就難以變為本部門的實際利益和資源。建設豪華的培訓中心,不僅可以爭取更多的財政經費,而且可以利用行政權力為培訓中心獲取經營收益,從而將公共資源轉變成為本機關掌控的資源,進而形成龐大的預算外、體制外資金。
就在培訓中心巧鉆一些制度縫隙的同時,在嚴控樓堂館所和培訓中心項目、嚴禁公款吃喝的制度環境下,培訓中心本身又成為制度的縫隙,并被充分利用——將吃喝玩樂的花銷換成干部培訓費用,不僅可以掩人耳目,躲過財政與審計的監督視線,而且,在本單位的培訓中心里搞腐敗,不僅隱秘,手頭還掌控“小金庫”,花錢更加方便。政令弱化
培訓中心的泛濫和禁而不止,彰顯出政令的弱化。
且不說對培訓中心采取一波接一波的整治,最終的結果似乎仍然收效甚微。單從國家對于黨政干部培訓工作的重視卻被移花接木偷梁換柱,改造為荒唐的“星級培訓”,從中已經充分表現出某些地方政令不暢、行政不力的現象。“政策學”遭棄擲,而“對策學”大行其道,國家機關的執政形象在無形中受損。
目前多數“培訓中心”的人事格局是,負責人基本上由單位的某處級或副處級領導兼任。由于創收涉及單位切身利益,很多領導不得不放棄本職工作搞創收,分散了精力,也造成政企不分。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周漢華認為,清理規范“培訓中心”,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對清理整頓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尤其是對那些給清理規范工作制造阻力的“背景”查查都是誰,為什么這么“牛”?對違反國家規定的黨政機關,要依法依紀從嚴追究直接責任人和主要領導的責任。動了這個根子,恐怕清理規范工作就能事半功倍了。
然而,也有人擔心:這種屬于黨政系統內部監督的治理方式,能否形成長效?
擔心不無理由。因為,系統的內部監督和自我約束固然重要,外部監督也必不可少。監督有異體性和強制性的要求,外部監督的缺失往往導致內部約束的乏力。比如,剛剛被通報的河南濮陽縣的案例,本身負有監察黨政機關行為之責的縣紀委,同樣借培訓中心之名,違規修建辦公大樓。
基于現實情況,研究人員指出,從長遠看,要促進干部培訓逐步市場化、專業化,把機關培訓工作交給專門的教育機構承擔,因為這些機構本身就具備圖書館、教室、宿舍、食堂等,相應減少了成本;從培訓功能上看,它們也更有資格。政府部門可以向類似機構公開招標,根據能力和成本擇優選用。這是社會分工專業化的必然趨勢,也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