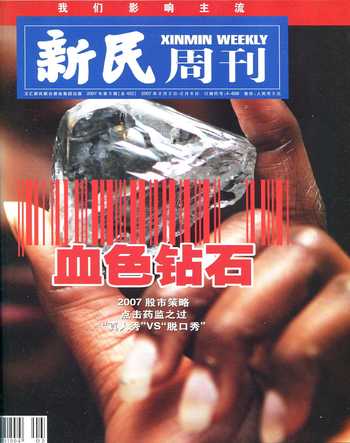合作建房、團體購房的標本意義
陳 憲
關于合作建房的討論,已經有一段時日了。最近,這個話題上了央視“對話”節目,又引起不少人的熱議。合作建房,亦稱合伙建房,個人集資建房。合作與合伙,意思相近。合作建房,是個人合作消費,不是個人合作投資或經營,不存在“集資”營利的動機,因此,“集資”二字是不必要的。歸納起來,對于合作建房,有以下幾種代表性的看法:一種觀點是,合作蓋樓是老百姓當家作主的一次嘗試,是市場經濟發展中一個重要的標志;另一種意見認為,在社會分工趨于成熟的今天,出現合作建房是一種反歷史潮流的行為;最多的看法是,合作建房是對高房價的用“腳”投票。
第一種看法有點說大了,合作建房和老百姓是否當家作主好像沒有特別關系,也談不上是什么“標志”。第二種看法不盡準確,恰恰是社會分工成熟為合作建房提供了可能,建房的各環節理論上都是可以外包的。第三種看法是民意,但稍有片面,如果合作建房可行,那么,中低房價時也會有人出于其他考慮作此選擇。我的看法是,合作建房是市場替代企業的一種選擇,是對企業替代市場的反動。這似乎是一種“回歸”,但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說過:“可以假定企業的顯著特征就是作為價格機制(市場)的替代物。”為什么要替代?企業的存在是為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即用費用較低的企業內交易替代費用較高的市場交易。企業的規模被決定在企業內交易的邊際費用等于市場交易的邊際費用的那一點上。企業往往根據這一點上的情形,決定是在相繼生產階段或相關產業之間訂立長期合同(外購或外包),還是實行縱向一體化(并購),這取決于兩種形式的交易費用孰高孰低。
同理,同樣存在市場替代企業的情形。當市場主體(指居民和家庭)可以不通過企業的形式,而以合作或家庭內的形式,獲得更低成本或更大滿足程度的消費品或服務,那么,他們就會采取合作或家庭內的形式。以合作建房為例。面對不少城市的高房價,居民難以承受,選擇個人合作建房,以非營利的方式運作,省去廣告銷售費用、項目貸款利息、大部分管理費用和開發商利潤,就可以較大幅度地降低成本,獲得他們在價格、房型上更加滿意的住房。再如,家庭可以委托醫院煎中藥,也可以自己煎;可以到面包房買面包和點心,也可以自己做;可以到飯店請客,也可以在家里請。前者的方式,是家庭購買企業的商品或服務,易言之,是企業替代了一部分家庭的功能;后者的方式,是以家庭內提供的方式替代了企業,用自己同樣有機會成本的時間為自己服務,這里,可能有價格或性價比的考慮,還可能有個性化、服務質量等方面的考慮。
因此,一般地說,市場替代企業和企業替代市場一樣,是市場主體(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理性選擇。當然,在現實生活中,建房是一件比較復雜的活動,盡管可以通過專業化分工體系,購買包括設計、融資、保險、施工和裝修等服務,但由自然人主體合作運作,仍然可能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或難以駕馭的風險。近來,又出現了與合作建房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團體購房——“團購”,即買房人自發形成集體購買行為,并聘請律師、驗房師等專業人士參與,以提高談判能力,盡最大可能“砍”房價。如果說合作建房是“模擬”一個房地產開發公司的行為,那么,團購就是“模擬”一個房地產營銷公司的行為。之所以說是“模擬”,是因為,合作建房和團體購房的組織者都是非營利的。
在發達國家,以及香港地區,居民的絕大部分買房行為,都是通過中介公司完成的。在這樣的買房交易中,賣房人和買房人都自愿與中介人發生關系,得到來自中介人業務和專業方面的幫助,而且,他們都分別得到各自的“剩余”。這是一個成熟的、規范的市場的表征。毋庸諱言,合作建房、團體購房,直接的起因是高房價,背后則深刻地體現了我國現階段房地產市場的不成熟、不規范。譬如,國家調控房地產市場的政策有利于房價下跌,但由于市場不規范,不能直接傳導到高房價,使得廣大購房者仍然感到樓市“高處不勝寒”,因此,頻頻傳來合作建房和團體購房的事情。
在關于合作建房的討論中,有一種觀點認為,從邏輯上說,一個無信的市場走到極端,就會出現以貨易貨的交易方式。當然,如上所述,個人在家庭內自己購買自己的服務,不僅是以貨易貨意義上的,而且是自然經濟(不以交換為目的)的,這和市場信用水平無直接關系。筆者還曾聽到一位經濟學家在一次演講中說,如果一個市場徹底無信用可言,那么,這個市場上就都是個體戶。這兩個觀點都給人以很重要的啟示意義,那就是,如果信用在較大范圍缺失,那么,市場發育和完善的進程就會出現倒退,市場主體都會加大交易費用,市場的整體效率就將下降。這種情形在中國目前的一些市場上出現了,值得引起有關各方的高度關注。(作者為上海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