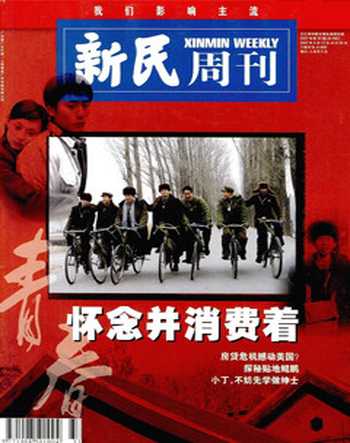從布萊爾到奧威爾
思 郁

《我為什么要寫作》
【英】喬治?奧威爾 著 董樂山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7年6月出版
奧威爾曾在遺囑中表示不希望有人為他寫作傳記。據他自己說是因為一個人的一生從內部看總是一連串失敗經歷的組合體,不但讓別人學習的地方不多,而且想起來都覺得丟人現眼。一個作家去世之前發表聲明不希望后人作傳,這樣的作家還真不少,但那都是因為他們滲透到骨子里的傲慢,覺得那些后人根本無法完美地詮釋自己高貴的思想和圓滿的一生,除非自己作傳,否則都將是一種遺憾。像奧威爾如此沒有自信甚至有些自卑想法的作家委實并不多見。
事實上,我們總是在違背前人,至少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奧威爾的傳記。我想應該對此有個合理而善意的解釋:也許我們不能完美地詮釋出那個“近乎天才的一個人”的一生,但是會不斷地努力向他靠近。
我是在讀奧威爾《我為什么要寫作》一書的時候才閃現這樣一些零星想法的。他的《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已經讀過多遍了,現在還擺放在我書架的顯眼位置。有時候重讀并不是因為覺得好看,但是好像有一種壓力會逼迫你一次次地拿起然后重新閱讀它。一般而言,無論什么樣的經典,只要你經過無數次被迫性閱讀之后也會感覺到乏味。但是冥冥中就是有一種力量,仿佛是那雙老大哥的眼睛在背后的注視讓你不寒而栗,你不得不再次拿起它重讀那些熟悉的字句,重溫那些窒息的場景。最后我幾乎已經絕望了,甚至覺得老大哥的眼睛就在自己的身后,是一個永遠無法蘇醒的夢魘。我開始讀《我為什么要寫作》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想擺脫那雙老大哥的眼睛,然而事實證明,我的想法并不正確。
在《我為什么要寫作》的同名篇章中,奧威爾分析了作家寫作的四大動機:純粹的自我中心、審美方面的熱情、歷史方面的沖動以及政治方面的目的。他說他是一個頭三種動機壓倒第四種動機的人。但是從他的后來的作品看,恰恰是政治方面的書寫幫他贏得了傳世的聲譽,甚至現在,我們已經忘記了他在政治書寫之外還有大量的作品湮沒無聞。正像西蒙?黎斯在《奧威爾論》中所言,如果我們仍在讀那些“非政治性”的作品,“一部分原因是為了他們可以對奧威爾的思想和個性作補充的說明,要是用的是另外一個作者的名字,今天是否會重印則是值得懷疑的”。西蒙?黎斯的意思無非是說如果奧威爾用他的本名“埃里克?布萊爾”出版《緬甸歲月》一類的作品,估計早無人問津了。那么,從布萊爾到奧威爾的轉變到底意味著什么呢?
“奧威爾”這個名字,意味著一種理想型的道德完美的化身,體現出的是一種倫理學和美學上能夠達到的境界;而“埃里克?布萊爾”則是那個從小遭受侮辱和鄙視的學生、作為緬甸殖民地的警察以及在巴黎倫敦的貧民窟和收容所的流浪漢的綜合體。毫無疑問,那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的形象,在他內心最黑暗的角落里揮之不去。也許正是這個令人感到挫敗的“埃里克?布萊爾”,主張后人不要為他作傳,而另外一個“奧威爾”的沉默正好說明了那些慘痛的經歷如何根深蒂固地霸據了他的內心世界。從布萊爾到奧威爾的轉變,是逐步驅逐內心黑暗的轉變,是書寫上的“非政治性”到“政治性”的轉變,是《緬甸歲月》和《巴黎倫敦落魄記》到《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的轉變。西蒙?黎斯對此的評價很到位:“他以一個有見識和正直的匠人開始他的文學生涯,最后成了我們這一世紀的大預言家。但是,歸根結底來說,他所以能有這異常的成就,與其說是由于他的文學才能,不如說是由于他的勇氣、專一和清晰的眼光,能夠看到極權主義對人類的沒有先例的威脅,并加以分析和譴責。”
他最后的結論也很干脆:“奧威爾并沒有達到普遍性的水平,這是所有大藝術家所特有的標志。而且他的作品大概也不會具有經典的永久性。”能讀出這句話背后隱微的含義么?我們不渴望奧威爾的作品成為經典,除非我們想永遠生活在極權主義環境中或者生活在老大哥眼睛的注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