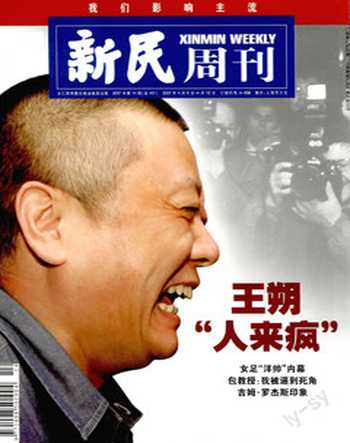“御林軍”要走出象牙塔
沈嘉祿
融入社會,切入當代,對長期來在體制內運行的上海油雕院來說,是走出困境的兩條必由之路。
上周,上海油畫雕塑院在松江新城召開了一個年度創作工作會議,亮點之一是特聘來自北京的4位聲名顯赫的美術評論家范迪安、邵大箴、殷雙喜、水中天和上海博物館館長陳燮君為學術主持。但是記者注意到另一個信息或許更有現實意義---上海油雕院負責學術的副院長兼藝委會主任俞曉夫再三強調:數十年來以"御林軍"定位出列的這個學術機構已經清醒地看到來自體制變革以及國際文化環境、市場的多方面壓力,決意要走出曾令畫家們自我陶醉不已的象牙塔。
在上海,屬于體制內的美術單位只有4家:上海美術館、劉海粟美術館、中國畫院和油雕院,兩家美術館的功能主要在展覽,真正搞創作的是后兩家。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仿效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一套體制。拿油雕院來說,工作重點就是執行上級布置的創作任務,體現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但在市場經濟啟動后,當藝術市場不停地掀起波濤時,畫家們再也不滿足這個身份了。
俞曉夫對記者坦言:"整個上海有數百個美術機構,包括創意園區、畫廊、藝術中心、美術院系等,與它們發生關系的畫家顯然能獲得更大的自由與空間,油雕院處于包圍之中,曾經的優越感失去了,被邊緣化了,隊伍不整,人心渙散,創作力量下滑,是油雕院的現狀。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推進,油雕院只剩下華山一條路,必須走出去。"
油雕院想出的招數有兩個:一是融入社會,一是切入當代。
所謂融入社會,就是通過辦畫展來實現關注民生、反映社會的價值追求。去年他們通過舉辦"精神與品格---中國寫實主義油畫研究展",取得了與北京聯合辦展的經驗。另外,在由國務院發起的國家重大歷史題材歷史畫的競標中,油雕院承擔了除國畫以外的幾乎所有的油畫與雕塑的創作,顯示了不俗的實力。今年在劉海粟美術館有個"藍本與創造"年度展,還有兩個配合重大工程的畫展,但最重要的亮相是在2008年奧運會后,去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院展。俞曉夫給出的理由也很實際:"一是上海目前缺少大腕級的畫家,沒有北京方面的肯定,你在上海再厲害也不算什么。二是給你一個最高的平臺,讓你來表現。天下事,實際上就是以成敗來論英雄的。我們藝委會想通過這個展覽將油雕院全體創作人員擰成一股繩。"
上海油雕院的創作力量主要有兩撥,一撥是50歲上下的具有很強寫實能力的具象畫家,幾乎集中了上海的精銳。還有一撥是30歲上下的青年藝術家,他們是在對傳統的顛覆中成長壯大的,是吃"狼奶"的一代,對當代藝術很敏感,也很有想法。俞曉夫說:"我們如果把這兩撥力量整合起來,到北京去就膽子大了。"
另一個問題是"切入當代",如何切入?作為具有古典主義氣質的寫實油畫家,俞曉夫明智地搞起了"統戰",他在不久前提出了一個"新具象"的概念。他是這么解釋的:"我想把傳統的架上繪畫讓位給新具象繪畫,因為傳統的寫實繪畫在西方已經被消解、被貶低,使之邊緣化了,再妄自尊大就不利于對外交流。另外,新具象的概念具有很強的包容性,除了經典,還可以玩一把表現制作、巴塞里茨的制作、畢加索的制作等,甚至可以延伸到空間裝置、綜合材料等。"事實上,縱觀近年來上海寫實油畫的創作態勢,從題材到觀念、技巧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所以這位寫實高手再三強調:具象繪畫在切入當代社會時生命力是相當旺盛的,既能完成重大題材創作,又能以靈活的姿態切入當代,與當代藝術結盟,這是其他藝術樣式做不到的。
形勢迫人,"御林軍"再也無法安坐象牙塔了,與其"被養著",不如"自找出路",一向優越感極強的畫家們這一次算是清醒了,他們要攜手走出"彼得堡",走向更加廣闊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