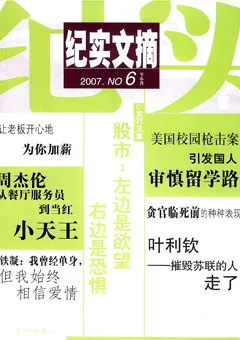父愛的深度
纖手破新橙
我跟楊炎結婚8年,沒見過公公。開始我以為楊炎是怕我嫌棄那個家,不肯帶我回去。于是我積極表態:選了你,就作好了接受你父母的準備,無論他們是窮是富,是老是病。楊炎握了我的手,含情脈脈,卻不說話。
有一次,我甚至買好了3張去他家的車票,興沖沖地擺到他面前,說:沖兒都5歲了,也該見見爺爺奶奶了。卻不想楊炎的臉一下子拉得老長,把車票撕得粉碎,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地說:沖兒沒有爺爺,我也沒有爹!
楊炎從農村出來,我知道他不是個忘恩負義的人。每年過年過節,他都要買很多東西寄回家里。每次打電話,他都說:娘,來城里住些日子吧!看得出他想家,卻從不提回家的事,也從來不提爹。
第二天,楊炎把沖兒送到姥姥家,第一次跟我說起爹。
楊炎是家里的老三,上面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楊炎上初三那年,姐姐繼哥哥之后,也考上大學。家里賤賣了地,才湊夠姐姐的學費。娘說:就這點地都賣了,往后咱吃啥喝啥?爹說:實在不行,就讓老疙瘩下來。或者爹只是那樣一說,但楊炎的心里卻很不是滋味。
姐姐上學走了。楊炎卻因為爹的那句話,學習上松懈下來,并跟一幫社會上的孩子混到了一起。
一天,他跟那些所謂的“朋友”玩了一天回來,看到爹鐵青著臉站在門口等他。爹上來就給了他一巴掌,說:既然你不愿意上學,那就別上了,去工地上做小工!
他瞪著爹,心里的委屈一下子涌上來,他喊:憑什么讓他倆上學,不讓我上?
爹說:想上學可以,打欠條吧,你花我的每一分錢,你都給我寫上字據,將來你掙錢了,都還給我。
他坐起來,抖著手寫了字據給爹。那晚,他跑到村東頭的小河邊哭了一夜。爹一定不是親的,否則,他怎么會如此對他?
他想:考上大學就好了,離開這個家,也就算逃出苦海了。
爹每年都要在院子里種半壟蘿卜,也許是土質不好,蘿卜全都很小很小,幾乎不能吃,全家人只能喝味道很難聞的蘿卜纓子湯。娘還像留好東西一樣,把蘿卜纓子曬干,給他泡水喝。
那年臨近高考,家里的麥子又黃了。爹捎信給他,讓他回來割麥子。他終于沒忍住,回家跟爹大吵一架,麥子割完,他頭也不回地回了學校。
楊炎說:小云,第一次去你家,咱爸給我剝橘子,跟我下象棋,和顏悅色地說話,我回來就哭了一場。這樣的父親才是父親啊。說完,他的眼睛又濕了。
我走過去,把他摟在懷里。我不知道那位未曾謀面的公公會以這樣無情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兒子。難道貧窮把親情都磨光了嗎?
楊炎從一本舊書里找出一張皺皺的紙,我看著上面密密麻麻記著好些賬。下面寫著楊炎的名字。楊炎說:還清了這張紙,我不欠他什么了。
跟單位打好招呼,我對楊炎說要出差幾天,然后去了他的老家。盡管有了心理準備,還是吃了一驚。家里三個在城里工作的兒女,都寄錢回來,他們卻還住著村里最破的土坯房,看來楊炎說的公公愛錢如命果然不假。
院子里還有半壟楊炎說的蘿卜地。每年婆婆還是會寄些曬干的蘿卜纓給我,囑咐我泡水給楊炎喝。我嫌那味道太難聞,總是偷偷扔掉了。
婆婆把我讓進屋,昏暗的光線里,我看到佝僂到炕上的老人,沒有想象里的兇神惡煞,感覺他只是個慈祥的鄉下老頭。
婆婆問起楊炎和沖兒。我用余光看公公,他裝作若無其事,可我知道他聽得很仔細。
我跟婆婆說:楊炎還在記恨我爹呢!婆婆的淚洶涌而出。她說:其實,最疼小炎的還是你爹。你看這半根壟,你爹年年種,就是家里再難的時候,也沒把它種成別的。就是因為楊炎內虛,有個老中醫出了個偏方說蘿卜纓泡水能補氣,你爹就記下了。年年,都是他把蘿卜纓曬好了,寄給你們,然后讓我打電話,還不讓我說是他弄的……
那為什么爹那時那樣對楊炎呢?婆婆嘆了口氣。那時候楊炎在外面交了不三不四的朋友,你爹若不用些激將法,怕是那學他就真的不念了。誰知那孩子犟,兩個人就一直頂著牛……
你爹的身體不行了,動哪哪疼,可是他不讓我跟孩子說,他說,他們好比啥都強,想到他們仨,我就哪都不疼了。他說什么也不肯看病,小炎給的那些錢,他都攢著,說留給沖兒上大學……
我的眼睛模糊了。父愛是口深井,兒子那淺淺的桶,怎么能量出井的深度呢?我站在村口給楊炎打手機,告訴他父親的愛像右手,它只知道默默地給予,卻從不需要左手說謝謝……
摘自紅袖添香2007年1月16日
推薦宋春華編輯李小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