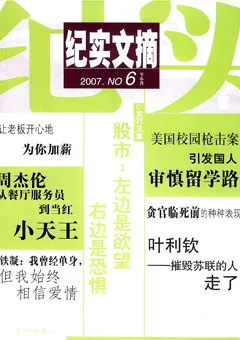還有什么可以束縛你
于 丹
人的一生只能被真正在乎的事情拘束住。如果你不在乎,那么——
真正的仁人志士不怕生活上的貧困,怕的是精神上的潦倒
莊子是戰國時代宋這個國家的蒙地(今河南商丘東北)人。他隱居不仕,終老天年,沒有什么社會名分。
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生在世,很難看破的就是名與利這兩個字。莊子怎么看待自己的貧困呢?在《山木》篇他講了一個故事:
一天莊子去見魏王。他穿著補丁摞補丁的破衣裳,鞋子沒有鞋帶,拿根草繩綁著,一副邋遢相。
魏王說:先生,你怎么這般困頓啊?
莊子答:這是貧窮而不是困頓啊。讀書人有道德理想而不能實現,這才是困頓。大王你沒看見過跳躍的猿猴嗎?它們在大樹上攀援跳躍,唯我獨尊,自得其樂;但讓它們身處荊棘叢中,就只能小心翼翼,不敢亂跑亂跳了。這不是它們身體不靈便,而是處在不利的情勢下,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啊。我現在就是生不逢時,要想不困頓,怎么可能呢?
真正的仁人志士不怕生活上的貧困,怕的是精神上的潦倒。對一個“利”字看得有多重,會決定他面對貧困的態度。
說到今天,一個只有10塊錢的人,他的快樂未必不如一個擁有億萬身價的人。手中有多少金錢,并不能決定它在你心里的分量。俗話說:“雁過留聲,人過留名”。有多少人可能不為利所惑,卻為名所累。即使一個高潔之士,也希望名垂青史。那么,在高官美譽面前,莊子會采取一種什么樣的態度呢?
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所以他不愛說什么。
《秋水》篇里講了一個故事:
大家知道,戰國時期,楚國是個大國。那天,莊子正逍逍遙遙在濮水上釣魚呢。楚王派了兩個大夫去到莊子那里,畢恭畢敬地說:“想要用我們國家的事勞煩先生您啊!”話說得很客氣,就是想要請他出山為相,希望把楚國的相位授給他。莊子手拿魚竿,頭也不回,說:“我聽說楚國有一只神龜,死了都三千年了,楚王還把它包上,藏在盒子里,放在廟堂之上。你們說,這只龜是愿意死了留下骨頭被人尊貴呢,還是愿意活著拖著尾巴在泥地里爬呢?”兩個大夫回答:“當然是愿意活著在泥地里爬啊!”莊子說:“那你們請便吧,讓我拖著尾巴在泥地里活著吧!”
我們以一種常規的思維,束縛了自己的心智
《莊子》中寫到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天,惠子找到莊子,說:魏王給了我一顆大葫蘆籽兒,我在家種了,結果長出一個大葫蘆來,看起來豐碩飽滿,有五石之大。因為這葫蘆太大了,所以它什么用都沒有。我要是把它一劈兩半,用它當個瓢去盛水的話,那個葫蘆皮太薄,要是盛上水,一拿它就碎了。想來想去,葫蘆這個東西種了干什么呢?不就是最后為了劈開當瓢來裝點東西嗎?這葫蘆雖大,卻大而無用,我把它打破算了。
莊子說:你真是不善于用大的東西啊!于是給他講了一個故事:
宋國有這么一戶人家,他們家有一樣稀世的秘方,就是不皴手的藥,在寒冷的冬天,讓人手腳沾了水以后不皴。所以他們家就世世代代以漂洗為生。一天,一個路人偶爾聽說這個秘方,欲以百金購買。全家人就聚在一起商量,說咱家這個秘方雖由來已久,但全家人以漂洗為生,才賺很少的錢。現在有人花百金買方子,干嗎不給他?路人買了這個秘方走了。
當時各地諸侯都在為爭地而戰,吳越相爭之地,正處水鄉。這個人從宋國拿了秘方直奔吳國,去游說吳王。此時正好越國軍隊進攻吳國。吳王就派這人帶兵,選在寒冬臘月,向越國發起水戰。因為有此秘方,軍士可以手腳不凍,戰斗力十足,而越人沒有這個秘方。這一戰吳國大勝。所以這個提供秘方的人,裂地封侯,立致富貴,身價非同一般。
這個方子給不同的人用,它可以帶來不同的人生效率。如果你擁有大眼界,你會看到同樣一個秘方,它可能會決定一國的命運,改變一個人的身份。
莊子告訴惠子說:大葫蘆也是一樣。你怎么就認定它非要剖開當瓢使呢?如果它是一個完整的大葫蘆,你為什么不把它系在身上,去浮游于大江大湖上呢?難道一個東西,必須要被加工成某種規定的產品,它才有用嗎?
一個人境界的大小,決定了他的思維方式。人們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規地去判斷事物的價值。而只有大境界的人,才能看到事物的真正價值。
莊子在《逍遙游》里給我們提出一個永恒的問題:什么叫作有用?
我們今天的教育,父母用自己全部的愛,為孩子規定了太多的戒律。我們讓孩子認為,作為一個葫蘆,它以后只能成為瓢,而不能成為一個巨大的游泳圈,帶著人浮游于江海;作為一塊土壤,上面只可以種菜種糧食,沒有人追問土壤下面可能埋藏的礦藏。我們以一種常規的思維,束縛了自己的心智。這種局限本來是可以打破的。只有打破這種常規思維,我們才有可能去憧憬真正的逍遙游。
重要的不在于我們客觀上有什么樣的寄寓,而在于主觀上有什么樣的胸懷
莊子的人生哲學,就是教我們要以大境界來看人生,所有的榮華富貴,是非紛爭都是毫無意義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有一個快樂的人生。
我們的生命都像電光石火一樣轉瞬即逝。在這么有限的生命里面,不管你是貧窮還是富貴,不論你度過什么樣的人生,最不應該扔掉的是歡樂。
人生的境界有大小。重要的不在于客觀上我們有什么樣的寄寓,而在于主觀上我們有什么樣的胸懷;不在于客觀提供給我們哪些機會,而在于我們的心智在有用與無用的判讀上,主觀確立了什么樣的價值觀。
當我們過分急功近利的時候,我們失去了春花秋月,難道不惋惜嗎?失去了與孩子、老人的天倫之樂,難道不遺憾嗎?失去了很多逍遙游的機會,讓自己的年華迅速老去,卻積累了一大堆無用的事功,難道內心不愧疚嗎?
摘自《于丹(莊子)心得》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編輯李小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