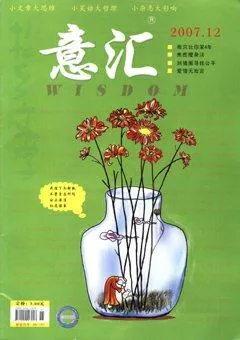謝安的審人術
對人不能一概而論,但從言多言少這一點上看,還是有道理的,一般寡言的人顯得厚重,而多嘴的人常常讓人感到機巧。
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中記載,一次,王羲之的兒子獻之與徽之、操之兩位兄長一起去拜訪謝安,徽之、操之說了很多俗事,而獻之只略作寒暄,就離去了。座中客人問謝安,這三賢中誰最優秀,謝安說,小者最勝。座客問何以見得,謝安答:“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謝安為什么看好王獻之,僅從他的寡言就看出問題。
《續晉陽秋》就稱獻之“雖不修常貫,但容止不妄”,他雖然不善修飾,生活中可能還有點不修邊幅,名士風流,但舉止莊重,比較沉靜。以謝公閱人之多,他一眼就看出王獻之內在氣質,實踐證明他并沒有看錯。王羲之是一代書法大師,他的幾個兒子也都是出色的書法家,而王獻之的成就在兄弟中要數第一,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王羲之,而與其父在書法史上并稱“二王”。
王獻之因受謝安賞識,官也做得很大,數次升遷,在仕途上一派好運。王獻之對他的這位恩人也并非百依百順,只會一味拍馬逢迎。
有一次謝安想讓王獻之為剛建成的太極殿題寫匾額,又難于開口,于是就談起書法家韋誕為魏明帝的凌云臺題匾的事,因為那塊匾額距地面二十五丈,韋誕被放在籠內,用轆轤長繩引上去,韋誕因懼怕,致使鬢發皆白。王獻之明白謝安用意,很有抵觸,認為曹魏的做法很不人道,從而頂撞謝安,讓謝安很是難堪,從這件事上可看出獻之秉性的耿介,這也是他“真”的一面。
盡管如此,王獻之并未有背叛過謝安,更沒有過河拆橋,一闊臉就變,他的恩師謝安病故時,朝廷在葬禮的規格和追贈事宜上有所分歧,獻之極力陳述謝安的功績和人品,最終促使晉孝武帝以殊禮追贈謝安。我們不能不佩服謝安的審人的眼力了。
當然,對人不能一概而論,但從言多言少這一點上看,還是有道理的,一般寡言的人顯得厚重,而多嘴的人常常讓人感到機巧。
據說汪精衛在蔣介石面前從沒說過一句真話,他的每一句話都是隨機而發,并不管它假到什么程度,后來這個人背叛了他的主子,也最終背叛了民族,成為頭號漢奸。在官場這種生態環境中,有的人混了一輩子,就沒有說過多少真話,既欺騙了別人,也欺騙了自己。語言往往是不可靠的,往往帶著某種私念和偏向。
一個智者,在察人時不應聽其說了什么,而更應看其做了什么。同樣,一個有本領的人,也常常是比較低調的人,不在于表露自己,而在于表現自己。
(王霞摘自《潮州日報》文/林楨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