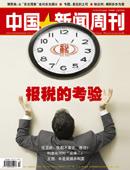“儒學計劃經濟”能靈?(上)
黨國英
“儒學計劃經濟”把改革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歸罪于市場化改革,主張用“完善”舊體制的辦法尋求解決問題的出路。這是計劃經濟思路的一種變異
在社會發展風云際會時期,學者中間總有一些大的治國方略提出。中國當代也正處在社會劇烈轉型時期。二十幾年的改革開放,有幾件事情值得稱道:實現對外開放,我們的經濟在壓力之下提高了效率,民眾的思想也經受了啟蒙,此其一;其二,在國家與民眾的關系方面,社會重心下沉,民間社會的自主性增強。農村開始發育有聲色的民主選舉制度,在經濟領域私營部門迅速擴張;其三,過去遺留下來的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的堅冰也開始被打破。
但是我們過去走的路是漸進改革,這樣就把一些難改的工作和難解決的問題留下來了。在居民收入共同增長的基礎上,不同階層的收入特別是城鄉收入差距還是在拉大;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還是沒有理順,建立一種中央和地方適度分權的體制還沒有破題;發展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大體上有了共識,但走出一條社會風險較小的民主改革路子,似乎還在考驗我們的智慧;經濟在快速發展,但環境壓力也在迅速增加,解決環境問題似乎沒有大手筆。
學者們對時局的批評大體上離不開上述幾個方面。在各種批評者的立論中,有一種被我叫做“儒學計劃經濟”。它把改革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歸罪于市場化改革,主張用“完善”舊體制的辦法尋求解決問題的出路。這是計劃經濟思路的一種變異,只不過裝扮了儒學外衣,所以頗能贏得社會共鳴。
很難說“儒學計劃經濟”是一種有統一的內在邏輯的思想體系,但總還可以說它有大體的外觀,它有這樣兩個特點:
第一是強調所謂東西方“文化”的對立,并把我們發展中出現的負面的東西說成是西方的東西。最近的新說法干脆把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哲學思想統稱為“亞洲價值觀”,把它與“西方中心主義的發展模式”相對立,認為西方模式“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時,它所秉持的理念是競爭、增長和發展,而不是和諧”。顯然,他們在這里把“和諧社會”與“競爭、增長和發展”對立起來了。
第二是將儒家提倡的“中庸”解釋為“均等規則”和非競爭性。一個典型的說法是,“要從道家文化中的‘無為、儒家文化的中庸、佛家文化中靜修以及其他很多亞洲傳統價值理念中去尋求智慧。”
為什么我在這里把有上述特點的學術思想成為“儒學計劃經濟”?早在上世紀40年代,就曾出現系統性的計劃經濟思想:反對市場競爭,相信政府有操控經濟的超人智慧和能力,后來被人譏諷為“計算機計劃經濟”或“計算機烏托邦主義”。比這還早的計劃經濟思想,可以叫做“哲學計劃經濟”,因為它的基礎是一種哲學理念。這些計劃經濟思想事實上從來沒有實現過,真正付諸實施的是“命令經濟”或“官僚經濟”。當今我國反對競爭、增長和發展的計劃經濟思想以儒家學說為裝飾,所以把它稱為“儒學計劃經濟”是比較恰當的。
“儒學計劃經濟”的“理論支撐”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東西方文化比較的“理論”。這種比較研究常常淪為學究式的自言自語,經不住歷史文獻和現實的考驗。例如,我們就聽到過這樣的武斷說法:“亞洲人求穩避險,求正避邪,求和避戰。”言下之意是歐美人總是倒著來的。其實,股份公司制度、專利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都是在歐洲興盛起來的降低風險的制度安排。至于戰爭,歷史資料表明,古代中國以國內戰爭為主,而古代乃至近代歐洲則以民族戰爭為多;歐洲戰爭有專業化的特點,平民卷入戰爭的程度低,死亡率也低。關于文化比較研究,有學者譚其鑲、朱學勤和秦暉等向我們提供了極為深刻的評論,使我們無法相信東西方的文化差異能大到足以讓我們選擇不同經濟發展模式的程度。
二是“資源枯竭”理論。相比幾十年前的“羅馬俱樂部”的理論,“儒學計劃經濟”并沒有給我們提供更新的思想,多的是聳人聽聞的恐嚇與苦口婆心的關于生活方式選擇的勸告。例如,有學者絮絮叨叨地告訴我們:由于人均資源所限,即便有少數亞洲的中產階層可能模仿美國富人,但大多數亞洲人注定不能簡單地照搬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依我看,如果亞洲國家拿這種學說來治理國家,恐怕高興的不是亞洲人,而是歐美的極端種族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