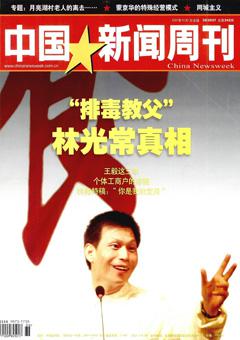慈善本質上是民間事業
徐友漁
人們經常以數據說明中國與美國在慈善捐助方面的巨大差距。這種差距并不一定代表善心和慷慨程度的差距,而是民間社會發育程度、公民在結社、集會、公共參與程度上的差距。
最近,不斷發生的“慈善風波”使得一些學者和評論者主張,解決問題之道是規范化和依靠機構,克服個人捐助不可避免會產生的弊端。
但是,9月媒體報道的發生在山東壽光的事件,使我們更進一步思考所謂規范化和依靠機構實際上應該如何進行,慈善本質上是政府有關機構統管的事業,還是民間事業。
據報道,近日,壽光義工為殘疾兒童和孤兒舉辦義演,為這些失學兒童募捐,但壽光的民政部門和城管人員禁止和中斷了義演;接著,“壽光愛心義工”以未經批準注冊,屬于非法為由被解散。
上述報道使人不得不思考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所謂“非法組織”“非法活動”取締和終止起來是很容易的,而資助孤殘的失學兒童、預防學生溺水的善事,要發起和進行卻不是那么容易,執法者在取締之余,是否有所作為使原來的善舉繼續進行?第二,現存的法或即將出臺的法是否完善,是促使慈善事業規范、有保障、順利地進行,還是設置了過高的門檻和過多的障礙,使欲行善蘋的人士勸輒得咎?
也許有人會說,這樣的組織和活動,如果事先申請、注冊,得到批準,豈不就不存在非法的問題,可見過錯還是在那些活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
我不否認,壽光欲行義舉和善事的人辦事確有瑕疵,他們應該事先去登記,爭取得到批準。但我仍然要問,根據現行的條例,尤其是根據實際上實行的政策和辦法,他們的申請會得到批準嗎?據我所知,在通常情況下,得到批準的可能性不合很大。
根據我國現行條例,社會團體要想注冊成功,必須過兩關,一是找到業務主管單位,二是得到民政部門批準,而對于許多民間性團體來說,很難有明確的對口單位算得上是業務主管單位,就算找到了,這樣的單位也很可能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不愿當主管單位,而更困難的是,就算有7業務主管單位,材料、手續一應俱全,還往往難于得到批準,雖然不是明確駁回,但常常要面對長期甚至遙遙無期的等待。
壽光事件發生后,輿論反應分為對立的兩種,一種為義工活動被解散遺憾,認為雖然有法規依據,卻不合情理。而完全支持解散的意見很有意思,一位網站銷售主管說:“那么多的人組成的團體萬一被人利用后果不可想象。”一位商場人員說:“今天你打著義工的名義成立一個團體,后天他也成立一個,那社會豈不亂套”這典型地反映了一種過時了的思維方式:成立組織很可能危害社會,對于民間組織,主要不應支持和鼓勵,而應該警惕和防范。按照這兩位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第二章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集會、集杜的自由是包含著潛在危險的,應該刪除。
我認為,從本質上說,慈善是民間的事業,人們經常以數據說明中國與美國在慈善捐助方面的巨大差距(比如:中國大陸人均捐款0.92元人民幣,美國人均為828.7美元;中國90%的公民沒有參加過捐助,而美國85%的捐款來自民眾),這種差距并不一定代表善心和慷慨程度的差距,而是民間社會發育程度,公民在結社、集會、公共參與程度上的差距。
說到這里,需要談一談擬議中的《慈善法》。這項應該是最沒有政治敏感性和最不涉及國家機密而與杜會民眾密切相關的法律,不向大眾公布草稿,未讓大眾參與討論,是令人遺憾的。一位了解情況的專家在媒體訪談中說:“我是不贊同個人或者組織可以自由放任地開展募捐活動的,因為自發的活動絕對無法避免失范與失控的局面”,“未經過法定程序批準的機構與個人是不可以隨便募捐的,包括自發性的網上募捐。無序募捐者需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我覺得這種意見有失偏頗。
讓我舉一個實際發生的例子:我在車站看見一個人呼天搶地地哭號,原來是一個民工被盜走全部錢財,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了。我把自己身上的錢全給了他,但還遠遠不夠,于是我大聲向周圍的人求助,向大家募捐。請問,我這種“未經過法定程序批準的”募捐果真是非法的、活該遭到禁止的行為嗎?
但愿《慈善法》是一部規范、支持、鼓勵慈善行為的法律,而不是著眼于防止結社、集會而限制慈善行為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