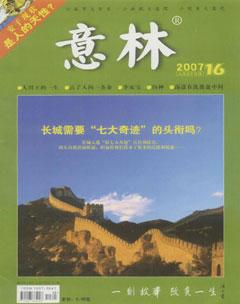花布和蘋果
肖復興
開會時隨手翻鄰座帶的一本書,看見有一首題名為《一塊花布》的短詩,作者叫代薇,詩寫得很有意思。她說如果你愛上一塊花布,“還必須愛上日后:它褪掉的顏色,撕碎的聲音。花布的一生,除了洗凈和晾干,還有左邊的灰塵,右邊的抹布。”
我明白,花布就是人,而且應該是女人。花布顏色鮮艷的時候,正是女人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的最佳狀態,一般容易討得男人的愛。但當花布的顏色褪盡,在日復一日一次次的洗凈晾干之后,最后落滿灰塵,變成抹布的時候,男人還能不能堅持最初的愛,就難說了。隨手把抹布扔進垃圾箱,然后另尋一塊新的花布,是如今一些男人司空見慣的選擇。
我想起童年住過的大院里,曾經有一對夫婦,男的是一位工程師,女的是一位中學老師。他們剛剛搬進大院來的時候,也就三十來歲,我還沒有上小學,雖然懵懵懂懂不大懂事,但從全院街坊們齊刷刷驚艷的眼神中,看得出女教師非常漂亮,男工程師英俊瀟灑,屬于那種天設一對地造一雙的絕配。他們每天蝶雙飛一樣出入我們的大院,成為全院家長教育自己子女選擇對象的課本。
那時候,最讓全院街坊們羨慕而且嘆為觀止的是,女教師非常愛吃蘋果。愛吃蘋果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蘋果誰不愛吃呀?關鍵是每次女的吃蘋果的時候,男工程師都要坐在她的旁邊親自為她削蘋果皮。削蘋果皮,也不是什么新鮮的事,關鍵是每次削下的蘋果皮,都是完完全全地連在一起,彎彎曲曲地從蘋果上一圈圈地垂落下來,像是飄曳著一條長長的紅絲帶。這確實讓街坊們驚訝。不僅驚訝男工程師削蘋果皮的水平,也驚訝他有這樣恒久的堅持,只要是削蘋果,一定會出現這樣紅紅的蘋果皮長長不斷的奇跡。每一次,街坊們從寬敞明亮的玻璃窗前看到這溫馨的一幕時,總能夠看到女的眼睛不是望著蘋果,而是望著丈夫,靜靜地等待著,仿佛那是一場精彩的演出,最好總不落幕才好。街坊們總會說,這樣漂亮的女人,就應該享受這樣的待遇。
我中學畢業的時候,這一對兒夫婦五十多歲了。那一年開春的時候,倒春寒,突然下了一場雪,雪后的街道上結了冰。女教師騎車到學校上課,躲一輛公共汽車,摔倒在冰面上,左腿摔斷了骨頭。一個來月以后,從醫院里出來,腿上還打著石膏,是男工程師抱著她走進大院的。我們的大院很深,一路上,他們的身上便落有一院人的目光,和男工程師臉上淌滿的汗珠一起閃閃發光。
那一年的夏天,她的腿還沒有完全好,傷筋動骨一百天嘛。“文化大革命”來了,她教的那些中學生闖進我們的大院,硬是把她揪到學校去批斗。等她狼狽不堪地從學校回來,她那條還沒有傷愈的左腿壞得更厲害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她的腿徹底殘廢了。每天再看到她的時候,都是丈夫攙扶著她出出進進。她一下子蒼老得厲害,當年漂亮的模樣,仿佛被風吹盡,再也看不出來了。
他們夫婦有兩個孩子,都和我一樣前后腳到農村插隊,等他們和我一樣從農村插隊回到北京的時候,他們夫婦已經是快七十的人了。那時,她已經患上了肝癌,她和她的兩個孩子都還不知道,知道的只有她的丈夫。
那時候,北京城里的蘋果只有到秋天蘋果上市時才能夠買到。而且,那時也沒有現在紅星、富士或美國蛇果那么多的品種,只有國光和紅蕉。每年秋天蘋果上市的時候,我們常常看到她家玻璃窗前那熟悉的一幕,男工程師為她削蘋果。她瘦削得有些脫形,還是如以前那樣靜靜地坐在旁邊,望著自己的丈夫。只有這一幕重復的場景,仿佛時光倒流,讓街坊們又能夠想起當年她那年輕漂亮的模樣。可誰知道她已經是病入膏肓的人了呢?
女教師走得很安詳,按照我國傳統講究的五福,即壽、富、康、德和善終,她的一生雖然算不上富貴、健康,也說不上長壽,卻是占了德和善終兩樣,應該算是福氣之人。送葬的那天,她以前在中學里曾經教過的很多學生來到她家里,向她的遺照鞠躬致哀,有的學生甚至掉了眼淚。那天,我也去了她家,看見她的遺照前擺著兩盤蘋果,每盤四個,每個都削了皮,那皮還都是完完全全地連在一起,擺放在蘋果的旁邊,垂落下來,像是飄曳著的一道道挽聯。
因為讀到了《一塊花布》這首詩,讓我想起了這段往事。
想起這樣的蘋果,對照著《一塊花布》這首詩,讓我感到,對于愛情和人生,花布從鮮艷的布料到抹布的一生,如果像是散文,象征著現實主義的話;那么,蘋果始終如一能夠將皮削成一條長長不斷線的紅絲帶,則像是詩,象征著浪漫主義了。我們需要向花布示愛,更需要向蘋果致敬。
(張愛杰摘自《文匯報》2007年7月9日圖/陳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