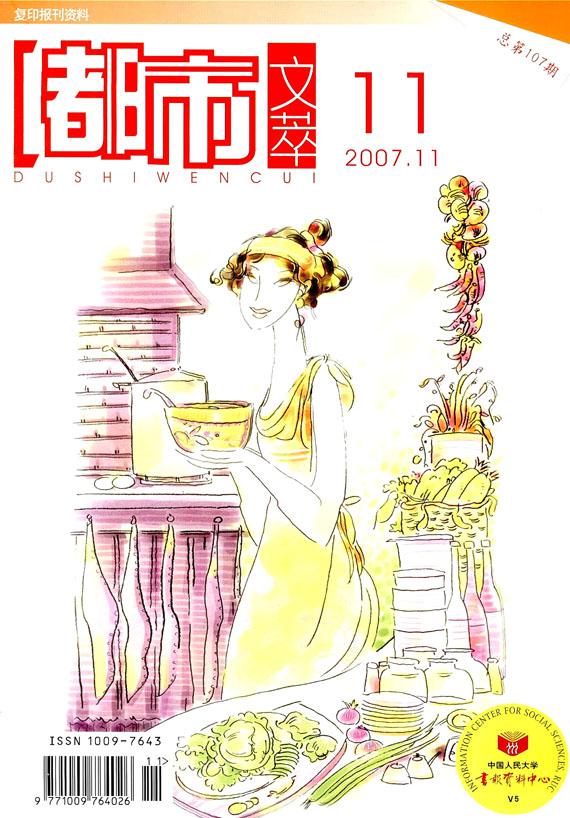等愛的孩子
丑丑丫頭
一
從來沒有見過啟明這樣的男孩子,對所有人,有著近乎卑微的好。
其實怎樣算起來,他都不該是如此的生活態度。23歲多一點兒,高大,英俊,上海交通大學成績優良的本科生,而且工作并非辛苦討來的,是公司誠懇邀約。這樣一個優秀小生,就算驕傲一些也無可非議,到底人家也是年輕有為。
但全然不是如此。報到那天,我便領教了他對人的好。那天和老總會了面后,我帶他去辦公室,他跟在我后面,先說第一句話:“麻煩小易姐。”
笑了笑,心里是有些喜歡的,現在禮貌周全的孩子不多了。
隨后他搶先一步給我開了門,好像是他引領我,然后關門。進了屋子我將他安置在新的辦公桌前,他一直等我離開才肯坐下。過了很小一會兒,他悄聲過去拿我的杯子去接水,我抬起頭來看著他伸手制止。“不用”,我說,“我自己來”。“沒關系的,你忙你的”。他笑著,是那種有點兒羞澀卻誠懇的笑容。便隨了他。
午間,吃完飯回來發現辦公室被打掃過了,他清理了我的桌子和電腦。向他道謝時,他拼命擺手,不停重復著沒有關系……臉都紅了。沒有假裝的成分。
第一天的工作,他有不懂的事情便很誠懇地過來問。他的英語極好,專業知識也扎實,在這樣的貿易公司,做好是很容易的。我只是比他多些工作經驗,真正的,倒教不了他什么。可是他虛心,并且有親和力,很合時宜地叫我小易姐,而不是易小姐或者其他。
一天為我接了5次水,清理了一次垃圾,下班時執意讓我先走,自己處理最后的單據。
我多少是意外的,每一年公司幾乎都有新人進來,沒有誰像他這樣。而且現在的工作環境不要求新人多做什么,大家是平等的。所以想,也許他從小有好的家教,父母教他為人處世的道理,卻難得他會聽從和運用。只是不知這樣的好,他能夠堅持多久。
啟明卻一直堅持了下來,在不大的小空間里很照顧我,類似打掃衛生、接水、開門鎖門之類的事情,再沒讓我做過,爭都爭不過。他不僅對我如此,對其他部門關系平等的同事也是關愛有加。誰的單據過多,誰有資料急需翻譯,找到他,從來不會推脫,盡心盡力做完,下次會主動把一些誰做都可以的工作主動承攬下來。他可以為別人排—整夜的隊買高峰時期的車票;可以充當搬運工用一整天時間,獨自幫一個女孩搬完家,為此還扭傷了腳,好幾天走路一瘸一拐……
二
和他相處的時間,幾乎每個人都能夠感受他的好,沒有絲毫敷衍的好。而且他的稱呼、他的笑容、他的神情,也似乎都對人有著一種深刻的依戀,不知道為了什么。
可是也會覺得他這樣不好,一個人對同事和朋友好是必要的,但不需要過分和盲目。過分了,就會顯得卑微。有一次,他極好脾氣地任由其他部門的同事小陳招來喚去,為一點兒小事情,喚得他一趟趟樓上樓下地跑,跑完了還要他用下班時間把單據送到另一家業務單位。以身體不太舒服為由,小陳竟心安理得地放下單據走人。啟明響亮地答應著,把那些單據收拾整齊裝進紙袋。想著6月份大中午的天,他要騎著自行車汗流浹背地走那么遠的路,忽然覺得有些心疼,忍不住抱怨他:“你就不能不答應,他打個車就過去了,還可以報銷,你跑這么遠的路,中午連休息時間都沒有。”
“沒有關系的。”他笑,“反正我也沒有睡午覺的習慣,再說我這么年輕,真的沒有關系。”
我嘆氣,拿他一點兒辦法沒有。“沒有關系”是他的口頭禪。
漸漸的,每個人都開始習慣他的好,習慣地接受,不再道謝,也不再有感動。好像他的存在就是為了對大家好。常常冷不丁會聽到誰在樓道喊,“啟明,快過來一下,電腦出問題了。”“啟明,昨天翻譯的資料翻譯完了嗎?”“啟明,該換純凈水了……”內線電話也會不停打過來,接完了,他必然會樓上樓下地跑幾趟。
但啟明卻從沒有因為做這些繁瑣的事情妨礙到工作,業務考評成績總是最佳的。他很努力也用心。現在沒有一個年輕人會用他這種方式生活,他們更多的是愛自己。可是他把大多的時間都用來愛了別人,他能碰到的所有人。
啟明的身上終日裝著零錢,他不會拒絕任何一雙伸向他的手,不管對方看過去是不是值得同情。有時候在飯店,因為飯菜的質量問題我們質問服務生,他無一例外地站出來擋駕,最愛說的話是,算了算了,他們多不容易啊……
私下里,我們說他愛心泛濫。所以,泛濫的愛心更加不被珍惜。一年后,他成了公司所有人的勤務員,公事私事,招之來揮之去。起初有些心疼和生氣,漸漸就覺得無所謂了。他可以不這樣,可是他非這樣不可,不是別人的錯,并且自己也習慣下來。承受他的好,不去想是否要珍惜。太輕易得到的,我們都已經習慣了不再珍惜。
三
那天早上過去上班,習慣地推門,卻沒有推開,門是鎖著的。有些奇怪,啟明來后,我就再也沒有用過自己的鑰匙。疑惑地開門,不知道為什么這一次他來遲了,并且直到過了打卡時間也沒有看到他的影子。沒有多想什么,打開電腦做事。
啟明一整天沒有來,那一整天樓道里喊了他幾次,內線電話找了幾次。知道他不在,他們應了一聲消失,沒有誰多問什么。我卻有諸多的不適應,有3次拿起杯子喝水的時候發現杯子是空的,看著新資料中陌生的單詞也會本能地轉頭喊啟明,好不容易到了下班,一時間竟然不知道要不要整理一下亂糟糟的桌面……
原來他慣壞了我的一些行為,他在,不覺得什么,不在,我有不適應感。
第二天,啟明依舊沒有來。
第三天,坐在電腦前,我再也不能夠安心,心不在焉地接了幾個電話,思維斷斷續續地出現空白,總是冷不丁想起他,想他不會那樣不周全,即使請假,也應該提前跟我打個招呼的,那么是他出什么事了?胡思亂想的時候,隔壁的小陳敲門進來,問,“啟明是不是有什么事啊,電話也沒開機。”
“不會吧?”我喃喃地說,“他能有什么事。”
說著手指卻下意識拿起話機撥了他的號碼,真的沒有開機。然后我撥分機號詢問經理,才知道他并沒有請假。
好像猛然地,大家這才發現了啟明的消失,開始不斷有人過來問我,我也想問別的人。但是問來問去,沒有人知道他為什么沒有來上班,去了哪里,甚至沒有誰知道他住在哪里,家在什么地方,這里有沒有其他的親人。平時,我們只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著他的好,沒有人想過要去對他好要去關愛他。
他似乎不再是真實的一個人,像個影子一樣沒有任何質感地存在著。而現在,這個影子消失了,莫名其妙的,讓許多人覺得不適應,因為即使他是影子,也是被許多人需要的影子,并非真的可有可無。
我們開始找他,卻無從找起,11位數的電話號碼是他和我們唯一的關聯。
第四天,第五天……第五天下午,我在心煩意亂中接起了一個電話,我開始因為擔心啟明而心煩意亂。
電話是醫院打來的,對方說,你認識周啟明嗎?
四
我丟下工作匆忙地打車趕去醫院。啟明在5天前出了車禍,昏迷了5天,終于清醒了過來。
病床上,啟明的腦袋被嚴密包裹著,露出的兩只眼睛透著那樣讓人心酸的眼神,那種依戀,那種深深的依戀,看著我,像一個受傷的孩子看到自己的親人。
我的眼淚忽然掉了下來,啟明,他讓我的心感覺到一種酸楚的疼。這么長時間他一直都在依戀,那樣的眼神,從來都沒有改變過,可是我們沒有一個人能撐起這份依戀,沒有一個人。包括每天和他一起相處8個小時被他叫做小易姐,被他照顧得無微不至的我。
那天晚上,我留在醫院陪他。他不肯那樣,想要我走,手抬了幾下又無力地放下去,眼睛是承受不起的慌亂。
可是我必須那么做,在他躺在醫院的這幾天,竟然沒有一個人陪伴他,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他獨自在死亡線上掙扎了4天。我不知道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他沒有通知家人,他還不能說話。他讓我的心在酸楚中不停地動蕩。
那晚,他終于在我的安慰聲中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公司里幾乎所有人都來了,病房里在一個早上開滿了新鮮的花,幾乎成了一個花房。而啟明卻是那樣的不安,他掙扎著要起來,一次又一次,終于忍不住吃力地擺手,像最初我同他道謝時擺手的樣子。
是一種承受不起的拒絕。可是他為什么要這樣,為什么?
啟明在醫院躺了一個月,身體的其他部位都是外傷,后腦損傷嚴重。不過到底年輕,他在治療中極快地恢復著健康。那些天里我們輪流來陪他照顧他,始終,沒有看見他的家人。那天晚上,我將他攙扶起來,一口一口喂他吃飯,吃著吃著,啟明的眼淚掉進了碗中。
這些天他從沒有哭過,包括最疼痛的時候。“小易姐”,他喚我。
我把碗放到一邊,用紗布擦他臉上的淚。“男子漢了,還哭。”我逗他。
他不說話,眼淚卻越來越多地落下來,擦也擦不凈,最后,我索性不擦了,將紗布丟到一邊,等他哭完。
好半天,啟明自己將紗布拿過來,把臉上的淚水抹去。他說:“小易姐,你相信嗎?這么多年,從來沒有人這樣對過我,從來沒有人對我這么好過。”
可是……我將疑問淹沒在唇邊。他的話,不會是無端。
那天晚上,我知道了啟明的身世,知道了這么多年他獨自的成長。啟明的父母在他5歲時因車禍去世了,于是他失去了唯一的親人。好心的鄰居將他托給了一戶無子女的人家收養,但他們卻不疼他,很小,他在家里做繁多的事情。被收養一年后,他們有了自己的孩子,更加視他為多余。為了念書,他容忍了一個少年不能容忍的種種生活和自尊的委屈。讀到高中時,他們不再管他,他開始做許多事情賺錢,端盤子,賣報紙,晚上跟著別人去刷墻……后來終于讀了大學,終于長大。在啟明生活的很多年里,從來都沒有得到過誰的愛。
這便是他一定要誠懇卑微地愛著別人的原因,他相信只有這樣,才能換得別人的愛,哪怕一點點。他不過是個需要一點兒愛的孩子,愛是他生命中的缺失,可是這個世界,從不肯主動給予。我們也不曾給予,我們到底有多冷漠呢?
我背過身去,卻看到門邊,站著小陳和其他幾個同事,他們站在那里,我們的目光碰到一起,漸漸地,都模糊成了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