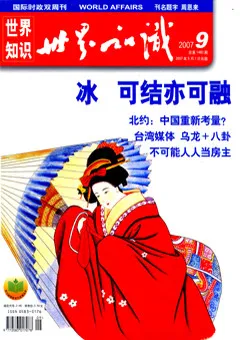另一個日本
當我漫步在伊豆半島那充滿濃郁日本情調的小鎮的時候,午后陽光照射著青石板,散發出古老的味道,竟使人回味故鄉的石板街。石板街兩邊的木板店鋪和挑起的遮陽布簾,完全使我沉醉在《清明上河圖》的情境中。日本,的確是一個單憑嗅覺就能聞出中國傳統文明影響的奇怪的國度。
但是,聽著嘰哩呱啦的日本話,看著迎風招展的太陽旗,一種莫名的警覺告訴我,這是一個經常會使中國人產生錯覺的地方。長期以來,國人認為中日文化同源同種,似乎更應該有相互的親近感。但近代以來150年的歷史昭示我們的,卻是另一種日本,一個和唐時日本完全不同的日本。
日本1萬元的紙幣上,印著一位名叫福澤諭吉的肖像。這位被稱為日本啟蒙思想家的人物,在日本可謂家喻戶曉。正是這位推動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家,在1875年著《文明論概略》時,就已經明確論述了中國和日本文明的差異。而在此書出版后130多年,國人還在不停地暗示中日文化同源同種,說什么必然會和平共處。
福澤諭吉認為,中國自秦始皇統一天下,實行專制政治以來,雖然經過多次改朝換代,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質上并未改變,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與最高的權力集中于一身而支配著社會。而日本并非如此。
他說:“然而,(日本)到了中古武人執政時代,逐漸打破了社會的結構,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強,至強未必至尊的情況,在人的心目中開始認識到至尊和至強的區別,恰如胸中容納兩種東西而任其自由活動一般。既然允許這兩種東西自由活動,其中就不能不夾雜著另外一些道理。這樣,尊崇神政的思想?武力壓制的思想和兩者夾雜著的道理,三種思想雖有強弱之分,但是任何一種思想都不能壟斷,既然不能壟斷,這時自然要產生一種自由的風氣。這與中國人擁戴絕對的專制君主,深信君主為至尊至強的傳統觀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
福澤諭吉認為,“在(日本)人民的心目中,并不像擁戴至尊的天威那樣,而是自然地把他看作凡人。這樣,至尊和至強兩種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這兩種思想當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為真理的活動開辟了道路,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日本的偶然幸運”。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如果不經過一番變革就不可能達到日本這樣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說,日本是比中國容易的。”
值得注意的是,福澤諭吉提出此觀點的前一年即1874年10月,因為和日本人談判而了解了日本狼子野心后,李鴻章在給總理衙門的報告中斷定日本“誠為中國永遠大患”,極力主張創建一支強大的近代海軍,用軍事力量牽制日本。當總理衙門大臣們主張用“大信不約”的理念作指導,不和日本簽訂任何條約的時候,李鴻章極力主張和日本簽訂中日近代第一個條約,以此確定二者的現代化關系,用條約約束日本。但是,洋務派的思想從總體上而言,達不到福澤諭吉的深度,因此,也沒有他那樣的氣魄徹底斷絕和傳統文化的關系,而是最終提出了“中體西用”的綱領。
福澤諭吉在發表上述主張10年后,把他的思想發展成為影響日本100年的國策主張,這就是著名的“脫亞論”。1885年3月16日他在《時事新報》發表了著名的短文《脫亞論》,積極地提倡在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應該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學習西洋文明,明確提出“我國不可狐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退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并且用他們的方式處理對東亞鄰國的關系!
此后數十年,一個完全不同于東亞傳統國家的新日本,在民族毀滅和毀滅其他民族的企圖中,逐漸破殼而出。
中日當代之關系,進入一個需要重新洗牌的階段。日本人清醒地認識到他們和我們的不同,因此推導出民族現代化之新途。中國沉醉于一種想像的邏輯中,不情愿地接受著日本不是東亞國家的殘酷現實。
伊豆半島的石板街上,依然縈繞著川端康成筆下的舞女留下的凄美愛情絕唱。日本人的文明中,的確有東方的情調。但是,除了漢字和吳音對其文字語言的影響,中國的文明已經很難在日本找到繼續扎根的理由。日本人可以為櫻花凋落的情景落淚,但也可以在午夜的電視節目中播送完全不符合儒家傳統的情色片斷。他們對中日文化同源同種的歷史說教,報以冷漠的哼哼。
要對付一個只認力量大小而并不看重民族之間的情感的群體,惟一的辦法,就是抓住當下最為關鍵的發展機遇,把自己做強,除此之外,別無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