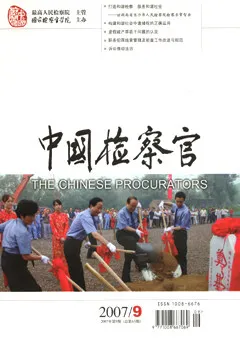虛假破產罪若干問題的認定
內容摘要:針對《刑法修正案(六)》第6條的規定,從犯罪構成的角度就該罪的罪名、犯罪客體、犯罪客觀行為、犯罪主體及法定刑等立法和適用上的若干問題需要進行詳細探討,該罪的直接客體是復雜客體、在客觀上表現為復合行為、其既遂形態是結果犯,由此,對完善法定刑提出建議。
關鍵詞:虛假破產罪 犯罪客體 客觀行為 犯罪主體 法定刑
隨著公司、企業的紛紛建立,妨害對公司、企業管理秩序的犯罪也不斷出現。《刑法修正案(六)》增設了虛假破產罪,則是形成了基本的破產犯罪體系,嚴密了刑事法網,有效地維護了國家對公司、企業的破產管理秩序以及債權人或者其他人的合法權益。但是,由于我國刑事立法的暗含式特點,以及本罪在規定的內容上不盡明確等因素,諸如本罪的罪名和犯罪客體該如何科學的界定,本罪客觀行為的特點,本罪的主體范圍以及法定刑等問題都需要進一步研究。本文擬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以利于正確指導司法實踐。
一、關于本罪犯罪客觀方面若干問題探討
(一)關于本罪的行為構造問題
對于本罪的行為構造,目前不少學者將破產程序開始之前所實施的隱匿財產等行為概括為破產欺詐行為,即主張單一行為說。我們認為這種概括是不妥當的。從本文的立論角度講,行為人在破產程序開始之前所實施的隱匿財產等行為也不能概括為虛假破產行為。因為債權人或者其他人的權益損害,不僅是行為人在破產程序開始之前所實施的隱匿財產等行為造成的,而且也與行為人向法院申請虛假破產的行為有直接關系。因此,虛假破產行為本身并不僅僅等于破產程序開始之前所實施的隱匿財產等行為,這與妨害清算罪的行為構造不同。妨害清算罪的實行行為是妨害清算行為,而妨害清算行為的內容即為現行《刑法》第162條所規定的三種行為方式,即隱匿公司、企業的財產、對資產負債表或者財產清單作虛偽記載以及在未清償債務前分配公司、企業的財產。因此,妨害清算行為屬于單一行為,而不是復合行為。而本罪的實行行為應是虛假破產行為。對此,有的學者認為,行為人實施的隱匿財產等行為與虛假破產行為具有因果關系。[1]我們認為,這種表述的含義并不明確,因為它沒有明確本罪客觀行為的具體形態,即它是單一行為還是復合行為。我們主張,本罪是復合行為,即由隱匿財產等行為和破產申請行為構成,而不僅僅是破產申請之前行為人所實施的隱匿財產等行為。
虛假破產行為的特點是破產的虛假性。由于本罪的客觀行為是復合行為,因此這種虛假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本罪手段行為的虛假性,即虛假的制造破產原因行為;二是本罪的目的行為的虛假性,即虛假的破產申請行為。因為公司、企業雖然可能負債但沒有達到破產臨界點,行為人通過隱匿財產等行為,人為地使公司、企業資產狀況達到破產臨界點,即“資不抵債”,也就是人為地制造破產假象。行為人在破產程序開始之前所實施的隱匿財產等行為本身從法律上并不能消除債權人或者其他人的債權等權益,但行為人在破產程序開始之前實施的隱匿財產等行為確已人為地減少了公司、企業的財產。于是,行為人向人民法院申請破產,利用國家的破產程序中破產財產的清算制度和分配制度,來掩蓋行為人在破產程序開始之前所實施的轉移和處分財產行為所造成的既定“事實”,利用破產程序中破產財產的清算和分配制度來確認公司、企業虛假的財產現狀,使得人民法院對經清算組確認的“破產財產”進行分配,從而行為人理直氣壯地對債權人或者其他人的債權等合法權益不再予以清償,達到嚴重損害債權人或者其他人的權益的目的。因此,我們認為,所謂虛假破產,是指公司、企業本沒有出現“資不抵債”的情形,而是行為人通過隱匿財產等行為有意地、人為地使自己的公司、企業達到“資不抵債”的程度,并利用國家的破產程序,從而實現其嚴重損害債權人或者其他人的債權等合法利益的行為。
就本罪的手段行為而言,《刑法修正案(六)》第6條采取了列舉式與概括式相結合的立法方式,即(1)隱匿財產;(2)承擔虛假的債務;(3)以其他方法轉移處分財產。所謂隱匿財產,是指在破產程序開始前,故意將公司、企業的財產進行轉移、藏匿的行為。因此,本罪的隱匿財產應從廣義上理解,即轉移財產和抽逃資金的行為,也屬于隱匿財產行為。所謂承擔虛假的債務,是指行為人虛假地承擔本不應承擔的債務,包括“無中生有”(即行為人虛假地承擔根本不存在的債務)和“由小變大”(即行為人擴大原有債務的數額)兩種情形。該行為一旦得逞,會大大減少真實的債權人或者其他人的受償機會,對真實的債權人或者其他人合法利益的損害甚為明顯。值得注意的是,從立法技術上,《刑法修正案(六)》關于本罪手段行為的規定,采取了兜底性條款的規定方式,與《刑法》第162條規定的妨害清算罪所采取的列舉式的立法規定相比較,具有很大的進步,以適應破產犯罪的復雜多變性。但是,“以其他方法轉移處分財產”的性質與方式,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其一、我們認為“以其他方法轉移處分財產”的性質,是指行為人實施的財產轉移、處分行為具有“虛假性”,即公司、企業破產原因的“虛假性”。其二、“以其他方法轉移處分財產”的方式。首先,行為人實施的轉移、處分財產行為必須發生在破產申請之前。其次,根據我國有關破產法律的規定,并結合破產案件的實際情況,其手段主要包括:(1)無償轉讓財產(如贈與等);(2)放棄自己的債權(包括無形資產,如知識產權等);(3)非正常壓價出售財產等。
(二)關于本罪犯罪行為實施時間及成立和既遂問題的探討
本罪犯罪行為的實施時間,是破產程序中還是破產程序前,抑或既包括破產程序前也包括破產程序后,確實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因為它直接涉及到行為人的行為罪與非罪的問題。對此,目前我國刑法理論界均主張在破產程序開始前的法定期間或者破產程序進行中。我們認為,本罪的客觀行為只能發生在破產程序開始之前,而不包括“破產程序進行中”,因為破產程序開始后根本談不上虛假破產的問題。如果在破產程序開始之后,行為人實施隱匿財產等行為,僅僅屬于在真破產過程中的損害債權人或者其他人權益的行為,但這種行為不能構成虛假破產罪。也就是說,行為人在破產程序后實施上述隱匿財產等行為,根據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應當以妨害清算罪論處,而不能構成本罪。不過,不少學者在界定“破產程序開始之前”時,均將破產程序開始前的法定期間作為本罪客觀行為發生的時間。[2]我們認為,這是受我國《破產法》第53條規定的影響。《破產法》第53條規定的“無效破產行為”,均要求發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產案件前6個月至破產宣告之日的期間內。但從《刑法修正案(六)》的規定看,行為人的行為發生在破產程序開始前,而未作“法定期間”的限制。我們認為,《刑法修正案(六)》未作“法定期間”的限制,這有利于擴大刑法防治的范圍,有效地預防和遏制虛假破產犯罪,從而維護債權人或者其他人的合法權益。
對于本罪的成立和既遂問題,目前在我國刑法理論上還缺乏深入的研究。如有學者認為,本罪以受破產宣告確定為條件,即破產宣告前一定期限內破產人所為的詐欺行為只有在破產宣告確定時才構成犯罪。[3]根據《刑法修正案(六)》第六條關于“嚴重損害債權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的規定,我們認為本罪的既遂形態屬于理論上的結果犯。根據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構成結果犯,要求行為人的行為必須發生法定的危害結果。就本罪而言,本罪也要求行為人的虛假破產行為必須造成“嚴重損害債權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的結果為構成條件,因為人民法院一旦作出破產宣告,意味著債權人或者其他人的權益受到了嚴重損害,即表明構成本罪的既遂。
至于何謂“嚴重損害債權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由于現行立法沒有提供具體的量化標準,需要有關司法解釋予以明確。對此,我們認為可以參照最高司法機關對于妨害清算罪的司法解釋精神和標準進行認定。具體而言,根據破產法律的有關規定精神,“嚴重損害債權人的利益”,是指由于上述行為使本應得到償還的債權人的巨額債權無法得到償還;而“嚴重損害其他人的利益”,是指嚴重損害實際債權人以外的其他人利益,主要包括由于公司、企業的上述行為致使其長期拖欠的職工工資、勞動保險費用、國家巨額稅款等得不到償還的情形。[4]
二、關于本罪的主體及法定刑問題的探討
(一)關于本罪的犯罪主體問題
目前,學者關于本罪的主體范圍存在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一種觀點是破產人及其法定代理人。[5]二是企業及其有關人員或第三人。該學者認為,參與破產程序的企業是構成該罪最主要的主體,應予以刑事處罰。參與破產程序的企業的有關人員包括該企業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第三人是指破產企業的債權人、債務人和其他關系人。[6]三是自然人,但又不是純粹的個人。[7]有些學者在探討本罪的犯罪主體時,之所以提出將公司、企業以外的組織或者個人作為本罪的主體,主要原因是受《刑法》第162條妨害清算罪的犯罪主體的影響。我們認為,這是不可取的。
我們主張,本罪是單位犯罪,其犯罪主體只能是公司、企業。理由主要有:(1)從我國的破產法律規定上看,我國現行破產制度是排除自然人、非法人組織的破產主體資格。[8]就《刑法修正案(六)》第6條的規定看,立法也是明確規定本罪的犯罪主體是公司、企業。(2)無論是在破產申請之前實施隱匿財產等行為,還是向人民法院申請破產的,都只能是公司、企業。如果在破產程序開始前,公司、企業中的自然人不是以公司、企業的名義實施隱匿財產等行為,就不是公司、企業的行為,而是自然人的行為,這與單位犯罪是有本質區別的。如公司、企業的主管人員在破產程序開始前實施侵占本公司、企業的財產行為,該侵占行為雖然也實際上人為地減少了公司、企業的財產,從而會損害債權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但該行為不屬于公司、企業的行為,對此,不能以本罪論處,而應構成貪污罪或者職務侵占罪,。再如,公司、企業的財會人員故意實施銷毀該公司、企業的會計憑證、賬薄的行為,如果該行為并非為虛假破產作準備,也與其他犯罪之間無連帶關系,則單獨構成故意銷毀會計資料罪,不以本罪論處。(3)從立法關于本罪的法定刑規定看,本罪是對公司、企業中的直接責任人員實行單罰制,其前提只能是立法上已經肯定了本罪是單位犯罪。否則,實行單罰制就失去了法律依據。
(二)關于本罪的法定刑問題
根據《刑法修正案(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