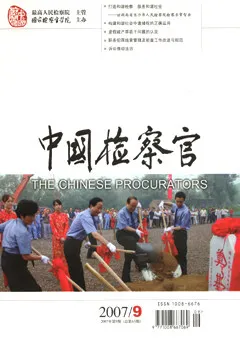將集資款用于高利放貸的行為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2001年犯罪嫌疑人某運管所所長李某請示上級領導同意并開所務會研究后,以給職工搞“福利”為目的,向職工集資,決定集資款只能用于向某一固定線路段客車車主發放貸款、收取利息以更新客車,集資款統一由運管所下屬的交通運輸服務中心管理。此后共收到集資款246.8萬元(其中運管所職工23戶,共集資161.5萬元,占65.4%;職工的親戚9戶,共集資52.8萬元,占21.3%;職工的朋友6戶,共集資32.5萬元,占13.3%),以1分的利息向外出借。這些集資款的使用,經李某批準,既有批給車主用于車輛更新的,也有借給其他個體戶和本單位職工使用的。2001年至2004年間,李某從交通服務中心分四次自批自借集資款31萬元,并將此31萬元投資到某私營企業從事營利性活動。
二、分歧意見
對犯罪嫌疑人李某自批自借集資款的行為,存在著三種截然不同的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李某的行為應認定為挪用公款罪。刑法第91條第2款規定: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集體和人民團體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以公共財產論。據此,本案中運管所集資的246.8萬元雖然所有權歸私人所有,但由于交由運管所這一具有行政執法職能的國有單位統一管理,就屬于公共財產,從而成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對象。李某分四次自批自借本金31萬元,并將此31萬元投資到一私營企業從事營利性活動,應當認定為挪用公款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在本案中,運管所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李某作為所長,屬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應按照刑法第176條處理。本案中的集資行為是經單位會議研究決定,運管所作為行政機關,并非金融機構,當然不具有吸收存款資格,共向本單位和單位外人員38戶集資246.8萬元,并且以高于國家規定的利息向外出借,從數額上達到了司法解釋規定的單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100萬元的立案標準,客觀上擾亂了國家金融管理秩序。
第三種意見認為,李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僅屬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首先,李某的行為不應認定為挪用公款罪。主要理由:本案中的款項來源為非法集資,其本身不具有合法性,在性質上不是公款,也就無從構成挪用公款罪。其次,本案亦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本單位的23戶職工不能成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對象,單位外的15戶是本單位職工的親戚或朋友,不屬于不特定對象,不能認定為公眾。即使認定單位外的15戶為“公眾”,但這15戶所集資的85.3萬元達不到100萬元的追訴標準。
三、評析意見
本案分歧的焦點是,以國有單位名義非法集資的款項能否成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對象?非法吸收某一單位內部成員及其親友的存款能否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根據本案實際情況以及相關法規和學理解釋,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第一,該案不構成挪用公款罪。從客體方面分析,李某的行為并未侵犯公共財物的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以及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刑法第91條第2款規定“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集體企業和人民團體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以公共財產論。”這里的管理、使用或運輸,應該理解為這些機關、單位具有管理權、使用權或運輸權,即所管理、使用、運輸的財產系合法來源。本案中的款項本質上屬違法集資所得,運管所對其并不具有法律保護的管理權,不能以公共財產論。既然不是公共財產,就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客觀方面的要件。從客觀方面分析,李某自批自借的行為并不符合挪用公款“利用職權”的特征。這些集資款的使用,既有批給車主用于車輛更新的,也有借給其他個體戶和本單位職工使用的,使用集資款的范圍較廣,且符合其將集資款放貸收取高額利息的本意。從行為手段看,李某采取打借條的方式,且支付利息,與挪用公款行為的特征不符。
第二,該案在本質上屬于一種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但判定本案的關鍵要素是對“公眾”的認定。在本案中“非法”表現為主體不合法(運管所不具有吸收公眾存款的資格),行為方式不合法(超過國家允許的利率范圍),目的不合法(不同于正常的借款投資,而是為了套取利差)。1998年頒布的《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第4條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是指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出具憑證,承諾在一定期限內還本付息的活動……”很顯然,據此,“不特定對象”是判斷“公眾”的一個標準。但何為“不特定對象”,仍然沒有很明確的判斷標準和操作性。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了《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下稱《紀要》),其中就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認定作了指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要從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數額、范圍以及給存款人造成的損失等方面來判定給金融秩序造成危害的程度。根據司法實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處罰:(1)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20萬元以上,單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100萬元以上的;(2)個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30戶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150戶以上的;(3)個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損失1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給存款人造成損失50萬元以上的。”從而給各級法院審理非法吸收公眾案件確定了可以量化的“客觀”標準,但仍未明確“公眾”的涵義。
現代漢語詞典將“公眾”解釋為“社會上大多數的人”。對“特定”一詞的解釋是:“(1)特別指定的;(2)某一個(人、時期、地方等)。而張明楷先生在其刑法學教科書中作過這樣的表述:“至于非法吸收某一單位內部成員的存款的行為能否成立本罪,則應通過考察單位成員的數量、吸收方法等因素,判斷是否面對不特定對象吸收存款。”[1]
從語義解釋的角度,筆者認為,對本案非法吸收存款的對象是否為“公眾”,可作如下理解:既然“特定”意為“特別指定的”,“不特定對象”則可解釋為“非特別指定的對象”。存款的38戶中包括單位外的15戶,雖然是該單位職工的親戚朋友,但分散于社會各個不同身份和職業,顯然屬于“非特別指定的對象”。根據張明楷先生的分析,非法吸收某一單位內部成員存款的行為并不排除是面對不特定對象吸收存款的可能性。運管所向本單位和單位外人員38戶集資246.8萬元,從數額上達到了司法解釋規定的單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100萬元的追訴標準,在吸收方法上承諾在一定期限內還本給付高于國家規定的利息,均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特征。
綜上,筆者認為,本案中犯罪嫌疑單位通過采取提高利率的手段,將大量資金集中到單位手中,從而造成大量社會閑散資金失控,同時規避了國家對吸收公眾存款的監督管理,構成非法吸
收公眾存款罪(單位犯罪)。
注釋:
[1]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6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