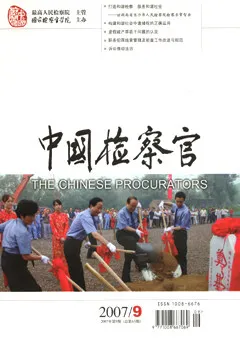為他人藏匿毒品的行為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粟某知道其丈夫扈某把大量毒品放在家中抽屜的三個香煙盒中并在家中吸毒,但對毒品的來源并不清楚且對扈某在家中吸毒也不干涉。在扈某被公安機關抓獲后,公安機關又去搜查其住處。粟某為使其丈夫逃避處罰,將扈某放在香煙盒中的毒品海洛因藏匿在身上,并在民警帶其上警車的過程中趁機把毒品扔掉,被民警當場發現。經依法鑒定,從粟某身上查獲的毒品海洛因重82.3克。經審理,扈某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
二、分歧意見
關于粟某行為的定性有四種分歧意見,主要如下:
1.粟某的行為構成窩藏毒品罪。粟某在明知其丈夫扈某把毒品放在家中,為了使其丈夫逃避處罰,將毒品藏匿在身上并伺機扔掉的行為符合窩藏毒品罪的構成要件,因此應認定為窩藏毒品罪。司法實踐中也有以此罪名作出判決的先例。[1]
2.粟某的行為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指是指違反國家毒品管理法規,非法持有毒品且數量較大的行為。嫌疑人粟某明知其丈夫將毒品放在家中,其對毒品也具有支配、控制的能力,并且在公安機關抓獲其的時候將毒品藏在自己身上,此類行為人事先未先通謀為非法持有毒品的犯罪人窩藏毒品,對行為人應單獨按非法持有毒品罪追究刑事責任。[2]
3.粟某的行為構成窩藏贓物罪。此種觀點認為,對窩藏毒品罪中窩藏的犯罪分子,應當限定為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所有的毒品,因此不能適用窩藏毒品罪。窩藏毒品罪與窩藏贓物罪屬特別法條與普通法條的關系,當作為特別法條的窩藏毒品罪不能適用時,應認定為窩藏贓物罪。
4.粟某的行為構成幫助毀滅證據罪。幫助毀滅證據罪是指幫助當事人毀滅證據,情節嚴重的行為。粟某扔掉毒品的行為侵犯了幫助毀滅證據罪的客體,即國家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
三、評析意見
(一)粟某的行為不構成窩藏毒品罪
首先,根據刑法理論的通說,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毒贓罪,是指為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財物的行為。[3]窩藏、轉移、隱瞞的對象毒品、毒贓,特指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毒品和其犯罪所得的財物。[4]本罪主觀方面為故意,要求行為人明知是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毒品、毒贓而故意予以窩藏、轉移、隱瞞。否則,不成立本罪。[5]
其次,刑法第349條第1款對包庇毒品犯罪分子,已經限定為“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那么,之后的文字“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財物的”的“犯罪分子”前,即使沒有寫明犯罪分子的具體范圍,也應該是指“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此外,該條第三款規定,“犯前兩款罪,事先通謀的,以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論處”。根據此款的規定,說明該條第一款對窩藏毒品罪所規定的“為犯罪分子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財物的”中的“犯罪分子”,顯然是指“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而不可能是指所有毒品犯罪分子。否則該款就應該寫以“毒品犯罪共犯論處”,而不必專門強調四種毒品罪的共犯。
本案中,在扈某家中的82.3克毒品海洛因不能認定為是走私、販賣、運輸、制造的情況下,其只能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因此粟某為使犯持有毒品罪的犯罪分子逃避處罰而予以窩藏毒品的行為不構成窩藏毒品罪。
(二)粟某的行為不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首先,粟某的行為不符合持有的基本特征。刑法中的持有型犯罪的“持有”,必須達到一定的時間要求,要求對物形成一定的持有狀態,并不是說一接觸就是持有,而必須達到一定的時間。持有時間既可以作為行為人主觀惡性的依據,也可以表現出對法益的侵害程度。但本案中粟乾春對毒品的實際控制時間過短,不能達到構成持有的時間要求。
其次,根據1994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指明知是鴉片、海洛因或者其他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數量較大的行為。如果有證據能夠證明非法持有毒品是為了進行走私、販賣、運輸、窩藏毒品犯罪的,則應當定走私、販賣、運輸或者窩藏毒品罪。該條說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適用是在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犯罪沒有證明的情況下對持有毒品者的毒品犯罪的堵截條款和補充條款,如果從行為人起獲的毒品能夠證明是為了窩藏毒品,則不能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本案中粟某的窩藏毒品的行為目的明確,且其沒有從事任何走私、販賣毒品等活動,沒有適用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可能性。
最后,根據刑法第348條之規定,非法持有毒品海洛因50克以上,應當判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假如對粟某與本犯扈某同樣適用非法持有毒品罪,則明顯導致罪刑不相適應。最好的做法還是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與客觀行為,并注重案件的處罰必要性,通過對其他法律條文的合理解釋達到最好的處罰效果。
(三)粟乾春的行為不構成幫助毀滅證據罪
本案中,粟某在民警將其控制之前將三盒毒品藏匿在自己身上,并在民警將其控制后將毒品扔掉的行為,主觀目的在于幫助其丈夫不受刑罰處罰,其扔毒品的行為可認為屬于毀滅證據。但粟某的行為在民警已將其控制的情況下根本不具有成功的可能性,因而屬于不能犯。根據我國刑法理論,不能犯作為未遂犯的下位概念,區分為對象不能犯與手段不能犯,對不能犯一律認為是犯罪未遂。
此外,如果將其扔毒品的行為認為是幫助毀滅證據罪的犯罪未遂還會出現一個問題,即對可能作為行為犯既遂評價的窩藏行為不予評價,卻僅僅對作為情節犯未遂的幫助毀滅證據行為進行評價,從處罰效果上看顯然不當。
(四)粟某的行為應認定為窩藏贓物罪
1.窩藏毒品罪與窩藏贓物罪屬于包容型法條競合關系。從犯罪構成上看,兩者有以下不同之處:(1)犯罪客體不同。雖然兩者都侵犯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但是窩藏毒品罪直接侵犯的是司法機關與毒品犯罪作斗爭的正常活動;而普通窩贓罪則直接侵犯的是司法機關與一般刑事犯罪作斗爭的正常司法活動。(2)行為對象不同。窩藏毒品罪的對象是特定的,即直接來源于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