賄賂犯罪特別自首條款探討
內(nèi)容摘要:特別自首條款的規(guī)定不違反《聯(lián)合國(guó)反腐敗公約》的規(guī)定,它既符合刑法的罪刑均衡原則,又貫徹了懲辦與寬大相結(jié)合的刑事政策,并且還有利于刑事實(shí)體法與程序法在功能上的協(xié)同,不但不能否定,反而有必要擴(kuò)大適用的主體范圍,即對(duì)受賄犯罪也應(yīng)設(shè)立類似條款。不過(guò)在刑事司法上,應(yīng)注意適用該條款的限制性條件。
關(guān)鍵詞:特別自首 賄賂 聯(lián)合國(guó)反腐敗公約 立法
《聯(lián)合國(guó)反腐敗公約》已正式生效,此前我國(guó)已經(jīng)加入該公約成為締約國(guó)。有學(xué)者認(rèn)為我國(guó)刑法部分條款與《聯(lián)合國(guó)反腐敗公約》(以下簡(jiǎn)稱《公約》)存在不相符的情形。即認(rèn)為《公約》第15、16、18、21各條對(duì)于賄賂犯罪的行賄方與受賄方在刑事處罰的措辭上基本一致,沒(méi)有厚此薄彼的考量,而在我國(guó),由于自首制度采用總則與分則同時(shí)規(guī)定的混合式立法模式,總則中的一般自首和準(zhǔn)自首制度適用于一切犯罪,分則中的特別自首條款不受總則自首制度的約束,刑事立法為了突出對(duì)公務(wù)人員的打擊,使行賄人能夠配合司法機(jī)關(guān)追究受賄人,在分則中設(shè)置了關(guān)于行賄犯罪的特別自首規(guī)定,致使行賄人得不到應(yīng)有的懲處,這種做法有違罪刑均衡原則,也與《公約》意旨不符,很是值得檢討。[1]
由于我國(guó)刑法分則第164條第3款、第390條第2款規(guī)定了對(duì)行賄人從寬處理的內(nèi)容,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dòng)交待”其犯罪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而受賄犯罪卻沒(méi)有類似條款。所以實(shí)踐中對(duì)行賄、受賄犯罪的法律適用效果存在事實(shí)上的不同,這就使有些學(xué)者就刑法對(duì)行賄、受賄對(duì)向犯采取區(qū)別對(duì)待的立法態(tài)度是否合理產(chǎn)生質(zhì)疑。因?yàn)樵谄淇磥?lái),既不應(yīng)當(dāng)因?yàn)槭苜V行為的危害程度嚴(yán)重就不認(rèn)定行賄罪,也不應(yīng)當(dāng)因?yàn)樾匈V方配合司法機(jī)關(guān)追查受賄行為而如實(shí)交待了行賄事實(shí),就將行賄行為認(rèn)定為無(wú)罪。[2]易言之,我國(guó)刑法設(shè)置行賄犯罪的特別自首條款是不合理的。特別是,非索取型受賄犯罪總是表現(xiàn)為行賄人主動(dòng)向公務(wù)員贈(zèng)送財(cái)物并請(qǐng)求對(duì)方在公務(wù)中酌情處理,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公務(wù)員也是被害人,所以對(duì)行賄人應(yīng)當(dāng)處以與受賄人同等甚至更嚴(yán)厲的刑罰,而不是相反。[3]
一、行賄犯罪設(shè)立特別自首條款與《公約》并不沖突
前述論者對(duì)刑事立法就行賄、受賄區(qū)別對(duì)待予以質(zhì)疑的見(jiàn)解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論者反對(duì)在刑法分則中設(shè)立特別自首條款對(duì)行賄人從寬處罰的意見(jiàn)則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一)特別自首制度與《公約》并無(wú)沖突
《公約》第15、16、18、21各條只是要求對(duì)各類受賄行為和行賄行為均應(yīng)當(dāng)“規(guī)定為犯罪”,并沒(méi)有進(jìn)一步要求處以完全相同的刑罰。相反,《公約》第37條規(guī)定,在根據(jù)《公約》確立的任何犯罪(當(dāng)然包括賄賂犯罪)的偵查或者起訴中,“應(yīng)當(dāng)考慮”對(duì)“提供實(shí)質(zhì)性配合的人”(包括被告人———引者注)就“減輕處罰的可能性”和“不起訴的可能性”分別作出規(guī)定。這充分說(shuō)明我國(guó)刑法關(guān)于行賄人刑事責(zé)任的特別自首規(guī)定與《公約》規(guī)范不但不沖突而且具有一致性,在賄賂犯罪中設(shè)立特別自首條款并在司法實(shí)踐中積極運(yùn)用是必要的。
(二)特別自首條款符合刑法的罪刑均衡原則
罪刑均衡的刑法原則是指刑罰的輕重與犯罪的輕重相均衡,而犯罪的輕重程度則由社會(huì)危害性的大小來(lái)決定。[4]也就是說(shuō)要根據(jù)犯罪性質(zhì)、犯罪情節(jié)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險(xiǎn)性三個(gè)方面全面評(píng)價(jià)來(lái)量定犯罪人的刑罰,而不是僅僅考慮罪質(zhì)卻忽略對(duì)犯罪情節(jié)和人身危險(xiǎn)性的綜合考察。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dòng)交代行賄行為的,其內(nèi)心的規(guī)范意識(shí)已經(jīng)部分覺(jué)醒,主觀惡性已經(jīng)降低,人身危險(xiǎn)性有所減輕,對(duì)于這類行賄人酌情予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并不違背罪刑均衡的刑法原則。
(三)特別自首條款貫徹了懲辦與寬大相結(jié)合的刑事政策
懲辦與寬大相結(jié)合的刑事政策要求立法者根據(jù)犯罪變化的具體情況,對(duì)現(xiàn)行刑法規(guī)范的目的性、合理性和有效性進(jìn)行科學(xué)考察,根據(jù)形勢(shì)擬制行之有效的政策并指導(dǎo)刑事立法的修改與完善以及指導(dǎo)刑事司法中定罪和量刑,最終體現(xiàn)“區(qū)別對(duì)待、寬嚴(yán)相濟(jì)、懲辦少數(shù)、改造多數(shù)”的基本精神。[5]運(yùn)用特別自首的規(guī)定從寬處罰行賄人,在我們看來(lái)是司法活動(dòng)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統(tǒng)一的體現(xiàn),正符合上述刑事政策。眾所周知,賄賂犯罪因?yàn)榕c公共管理權(quán)力直接相聯(lián),具有隱蔽性強(qiáng)、危害性大、發(fā)案率高、查處困難的特點(diǎn),而且由于利益的相關(guān)性,犯罪人往往訂立攻守同盟、堅(jiān)不吐實(shí),致使該類案件在偵破、審理上存在很大難度,往往由于無(wú)法獲取必要、充分的證據(jù)而不得不撤銷案件,任憑犯罪分子逍遙法外。因此針對(duì)從屬某些“主犯罪”而存在的“從犯罪”運(yùn)用特別寬大處理的自首規(guī)定,可望通過(guò)給予此類“外圍”犯罪人更加寬緩的處罰,瓦解攻守同盟,以嚴(yán)厲打擊危害嚴(yán)重的“核心”犯罪人。[6]正如有的學(xué)者所認(rèn)為,這是法律為了更徹底地揭露受賄者而規(guī)定對(duì)行賄犯罪實(shí)行所謂“赦免”的一種獨(dú)特形式。[7]基于此,世界各國(guó)刑事立法普遍規(guī)定了關(guān)于行賄犯罪的特別自首條款,對(duì)外圍犯罪人給予較之普通自首更為寬緩的處理。我國(guó)在行賄犯罪中設(shè)置特別自首條款可以說(shuō)是與國(guó)際刑事立法趨勢(shì)一致,并且充分體現(xiàn)了歷來(lái)強(qiáng)調(diào)的懲辦與寬大相結(jié)合的刑事政策。
(四)特別自首條款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bǔ)刑事訴訟規(guī)范的缺位
許多國(guó)家在刑事訴訟中對(duì)于賄賂犯罪都規(guī)定有污點(diǎn)證人制度。有賄賂犯罪污點(diǎn)的行為人,當(dāng)其在司法機(jī)關(guān)追訴賄賂犯罪時(shí),配合、幫助司法機(jī)關(guān)就有關(guān)案情提供證言,司法機(jī)關(guān)便對(duì)其作出不予起訴或者減輕刑罰處罰的決定。賄賂犯罪污點(diǎn)證人制度的采用源于下列刑事政策之理由:(1)偵查階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賄賂案件破案艱難的問(wèn)題;(2)審判階段有利于固定賄賂犯罪案件的證據(jù)從而使案件得以順利審理和判決;(3)有利于降低訴訟成本、節(jié)約司法資源和提高訴訟效率;(4)作證過(guò)程有利于促使該證人悔過(guò)自新,符合矯治改善犯罪人的目的;(5)制度所具有的威懾力有利于預(yù)防社會(huì)上某些賄賂犯罪的發(fā)生,這也有利于刑法目的實(shí)現(xiàn)。
我國(guó)刑事訴訟法中沒(méi)有污點(diǎn)證人制度,但是筆者認(rèn)為,污點(diǎn)證人制度所適用的法理卻應(yīng)當(dāng)是各國(guó)共通的。那么,在我國(guó)刑事訴訟法尚未確立污點(diǎn)證人制度的現(xiàn)狀下,刑法能否有所作為呢?答案應(yīng)當(dāng)是肯定的。當(dāng)今刑法已經(jīng)不再滿足于孤立、靜態(tài)的思維模式,它著眼于犯罪防控的科學(xué)體系,要求跳出絕對(duì)罪刑法定主義的僵化形式。德國(guó)學(xué)者就“整體刑法學(xué)”概念(gesamte-strafrechtswissenschaft)的提倡和近年我國(guó)學(xué)者“刑事一體化”思想的提出,[8]使人們認(rèn)識(shí)到刑法不僅僅是與犯罪作斗爭(zhēng)的手段之一,只有朝著“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目標(biāo),跳出刑法自身,立于刑法之外乃至刑法之上來(lái)思考刑法,并且超越傳統(tǒng)的規(guī)范解釋學(xué)視野,立于刑事政策的高度,慮及刑事訴訟的需求來(lái)運(yùn)用刑法,才能使刑法的運(yùn)行更合目的、更具理性和更富效果。[9]實(shí)際上,《刑法》第390條第2款關(guān)于特別自首的規(guī)定與《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2款關(guān)于相對(duì)不起訴的規(guī)定,二者結(jié)合運(yùn)用就可以在相當(dāng)程度上彌補(bǔ)我國(guó)賄賂犯罪污點(diǎn)證人制度缺位的不足(例如綦江虹橋倒塌案中的行賄人費(fèi)上利作為控方證人出庭指證被告人林世元,就得以被司法機(jī)關(guān)依據(jù)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而不起訴)。[10]僅從這一點(diǎn)看,對(duì)行賄人設(shè)立特別自首規(guī)定從寬處罰的刑法條文和相應(yīng)的實(shí)踐做法不但不應(yīng)該否定而且應(yīng)當(dāng)保留。
綜上,行賄犯罪中的特別自首規(guī)定既與《公約》意旨相一致,又符合刑法的罪刑均衡原則,不但貫徹了“懲辦與寬大相結(jié)合”的歷來(lái)刑事政策,而且有利于刑事實(shí)體法與程序法的功能在司法實(shí)踐中協(xié)同發(fā)揮,這項(xiàng)規(guī)定具有合理性。
二、受賄犯罪應(yīng)當(dāng)增設(shè)特別自首條款
由于司法實(shí)踐中賄賂犯罪案件在很多情況下涉及“一對(duì)一”的證據(jù),偵破難度非常大,因此為了及時(shí)破案,偵查機(jī)關(guān)不只是需要以行賄人為突破口,讓其作為污點(diǎn)證人出庭指控受賄人,某些情況下也需要以受賄人為突破口,讓其作為污點(diǎn)證人出庭指控行賄人。而且,行賄與受賄作為對(duì)向犯,從刑事政策考慮,通過(guò)任何一方遏制另一方(犯罪)都會(huì)是有效的。再者,不論是受賄行為還是行賄行為,應(yīng)允許在法律權(quán)利和義務(wù)上受到平等待遇。因此,刑法有必要對(duì)受賄犯罪賦予與行賄犯罪同樣的特別自首條款。
自我國(guó)特別自首制度肇始,其適用范圍就已經(jīng)包括職務(wù)犯罪本人和外圍犯罪人。[11]但是后來(lái)隨著對(duì)外圍犯罪人適用特別自首制度范圍的擴(kuò)大,反而忽略了對(duì)職務(wù)犯罪本人的特別自首制度。[12]我們認(rèn)為,對(duì)職務(wù)犯罪本人設(shè)置特別自首制度不應(yīng)該成為禁區(qū)。因?yàn)榭陀^地講,設(shè)置職務(wù)犯罪特別自首制度的目的在于,通過(guò)鼓勵(lì)外圍犯罪人自首來(lái)打擊隱蔽性相對(duì)更大的職務(wù)犯罪,然而,對(duì)于外圍犯罪人的判斷,不宜簡(jiǎn)單地看罪名是否屬于外圍型罪名,而應(yīng)當(dāng)擺脫原有的思維定勢(shì),以犯罪行為作標(biāo)準(zhǔn),根據(jù)這個(gè)標(biāo)準(zhǔn),賄賂犯罪的外圍犯罪行為,不應(yīng)僅限于行賄行為和介紹賄賂行為,還可以包括某些受賄行為(例如不是國(guó)家工作人員,但與國(guó)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此外,也不能說(shuō)所有的受賄犯罪公職人員都不可以適用特別自首制度的寬緩處遇,因?yàn)閺那拔奶岬降牟檗k職務(wù)犯罪司法實(shí)踐之需要、對(duì)向犯之理論、減少司法成本之考量,以及追求刑罰輕緩化的世界刑事司法趨勢(shì)看,對(duì)社會(huì)危害性較小的受賄犯罪公職人員設(shè)立和適用特別自首制度也是可取的,盡管這樣的規(guī)定目前還鮮見(jiàn)于世界各國(guó)刑事立法,但我國(guó)并非不可以遵循《公約》的意旨邁出率先的一步。
三、余論
司法機(jī)關(guān)在運(yùn)用特別自首條款減輕、免除行為人的刑罰時(shí)應(yīng)當(dāng)遵循程序上與實(shí)體上的要求,準(zhǔn)確把握特別自首成立的條件,嚴(yán)格適用,否則就可能放縱賄賂犯罪。
首先在形式上,認(rèn)定特別自首尤其要注意行為人主動(dòng)交代犯罪事實(shí)是否在“被追訴前”,這是判斷“特別自首”是否成立的重要形式條件。某些情況下進(jìn)行這種判斷并非容易,例如行為人實(shí)施行賄犯罪之后先自首,后逃跑,繼而又主動(dòng)投案,是否可以成立特別自首就值得研究。犯罪人前次投案屬于“一般自首”和“特別自首”竟合的行為,但是兩種自首均因行為人的逃跑而不成立,其后的再次主動(dòng)投案行為,根據(jù)司法解釋仍可以成立“一般自首”,但是無(wú)法成立“特別自首”,因?yàn)樘优苤蟮摹爸鲃?dòng)投案”行為發(fā)生在主要犯罪事實(shí)已被司法機(jī)關(guān)知曉、掌握并且已經(jīng)啟動(dòng)國(guó)家追訴程序之后,已不再屬于“被追訴前”。
其次在實(shí)質(zhì)上,決定是否從寬處罰應(yīng)當(dāng)重點(diǎn)考察兩方面的內(nèi)容:其一,行為人對(duì)國(guó)家工作人員職務(wù)行為的不可收買性侵犯的程度;其二,行為人在查處賄賂犯罪中所起的實(shí)際作用。正如《公約》第37條所規(guī)定的,行為人必須在與執(zhí)法機(jī)關(guān)的合作中提供“實(shí)質(zhì)性配合”才考慮給予從寬的處遇。因此建議司法機(jī)關(guān)在運(yùn)用刑法關(guān)于特別自首的規(guī)定決定是否“可以”對(duì)行為人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時(shí),應(yīng)以其是否對(duì)案件的偵破、審理起到實(shí)質(zhì)性作用為根據(jù)。由于這是刑法理論中的“規(guī)范性構(gòu)成要素”,在司法實(shí)踐中把握起來(lái)會(huì)存在一定的
困難,必要時(shí)有關(guān)部門可以就此作出司法解釋。
參考文獻(xiàn)
[1]范紅旗、邵沙平:《〈聯(lián)合國(guó)反腐敗公約〉的實(shí)施與我國(guó)反賄賂犯罪法的完善》,載《法學(xué)雜志》2004年第5期,第69頁(yè)。
[2]張明楷著:《刑法學(xué)》,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33頁(yè)。
[3][日]大谷實(shí)著:《刑事政策學(xué)》,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頁(yè)。
[4]馬克昌著:《比較刑法原理》,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76-77頁(yè)。
[5]馬克昌主編:《中國(guó)刑事政策學(xué)》,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2年版,第89-111頁(yè)。
[6]趙秉志、于志剛:《論我國(guó)刑法分則中的特別自首制度》,《人民檢察》2000年第3期,第21頁(yè)。
[7][前蘇聯(lián)]A·H·特拉伊寧著:《犯罪構(gòu)成的一般學(xué)說(shuō)》,薛秉忠等譯,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58年版,第283頁(yè)。
[8]儲(chǔ)槐植:《建立刑事一體化思想》,載儲(chǔ)槐植著:《刑事一體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頁(yè)。
[9]梁根林著:《刑事政策:立場(chǎng)與范疇》,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頁(yè)。
[10]梁玉霞:《論污點(diǎn)證人作證的交易豁免———由綦江虹橋案引發(fā)的法律思考》,載《中國(guó)刑事法雜志》2000年第6期,第67頁(yè)。
[11]參見(jiàn)1988年1月21日《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常務(wù)委員會(huì)關(guān)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bǔ)充規(guī)定》,第2條第3項(xiàng),第8條第2款。
[12]李文燕、于志剛:《論職務(wù)犯罪中的特別自首制度》,載《國(guó)家檢察官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2年第1期,第31-32頁(yè)。
*江西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zhǎng)、教授[330029]
**江西省人民檢察院干部,武漢大學(xué)刑法學(xué)博士生[4300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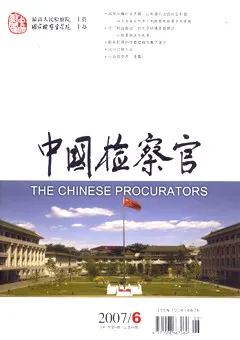 中國(guó)檢察官·司法務(wù)實(shí)2007年6期
中國(guó)檢察官·司法務(wù)實(shí)2007年6期
- 中國(guó)檢察官·司法務(wù)實(shí)的其它文章
- 地方動(dòng)態(tài)
- 檢察資訊
- 正義從哪里來(lái)
- 探索檢察工作的和諧創(chuàng)新路
- 一把手、小圈子與攫取資源
- 正義從哪里來(lá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