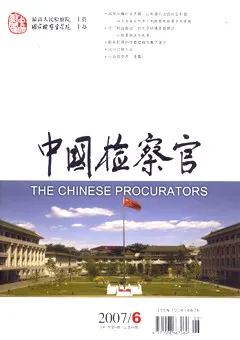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社會矯正對象之監管
內容摘要:
針對監管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社區矯正對象在實踐中所遇到部分監管措施遭到質疑和制裁措施乏力等問題,是由于資格刑的虛無性特點、過分強調監管手段等三個方面的原因所造成,因此,從立法和監管措施等不同方面,都應提出解決對策。
關鍵詞:
剝奪政治權利 社區矯正 資格刑
江蘇省蘇州市平江區是從2005年9月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筆者作為該區社區矯正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在負責對該項工作進行監督檢查中發現,社區矯正工作在逐步得到社會肯定的同時,也遇到了一些困難,其中關于對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矯正對象進行監管和處罰的問題尤其突出。筆者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初步梳理,分析了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粗淺的解決對策。
一、所遇到的問題
2005年9月至2007年3月,蘇州市平江區共接受社區矯正對象182名。其中被剝奪政治權利的28名,占總數的15.4%。在對這些矯正對象進行監管時主要遇到以下兩個問題:
(一)對部分監管措施有異議
根據《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第27條、《江蘇省社區矯正工作流程》第11條至16條的規定,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社區矯正對象除了不享有政治權利外,還得遵守下列監管規定:1.每周以電話或書面形式匯報思想和活動情況;2.遷居或離開居住區域時須經縣級社區矯正工作機構和公安機關批準;3.每月參加不少于12個小時的公益勞動。不僅是一些矯正對象,就連司法界的一些干警也對這三項監管措施提出了異議。有的認為剝奪政治權利的刑罰不應限制其它權利,而參加公益勞動和被批準后才能遷居就是變相地限制人身自由,匯報思想就等于變相地限制思想自由;有的認為只要這類矯正對象不行使政治權利,社區就不應再設置任何限制措施。鑒于這些異議,平江區司法局在得到上級司法局同意的情況下,暫時未要求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矯正對象參加公益勞動。
(二)制裁措施乏力
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社區矯正對象在剝奪政治權利刑罰執行期間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和有關監督管理的規定,但未構成犯罪的,《刑法》未對此作出相應的制約、制裁措施和規定,司法所只能依據有關規范性文件作出警告、記過兩種行政制裁措施,如《江蘇省社區矯正對象考核獎懲辦法》第11條、第12條的規定,對不按時向司法所匯報情況,不參加社區矯正活動,又不請假等情形給予警告處分。對多次拒絕參加社區矯正活動等情況予以記過處分。但警告、記過后若矯正對象仍不遵守監管規定,司法所除了再次給予警告或記過處分外,既不能象緩刑、假釋等監外執行罪犯,給予撤銷緩刑、假釋予以收監執行制裁,又不能延長剝奪政治權利的期限,當其剝奪政治權利的期限屆滿時,也只能宣布恢復其政治權利。所以這兩種處罰措施對矯正對象根本無威懾力。如在上述矯正對象中,表現差的9名主要是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矯正對象。他們有的拒絕參加各項活動,有的甚至謾罵、威脅司法所的工作人員。區司法局雖然對個別矯正對象予以警告處分,但收效不大。
二、產生的原因
上述問題的產生,既有剝奪政治權利刑罰本身的原因,也有矯正手段不適當、司法行政機關未聯合公安機關有機地行使處罰權的原因。
(一)由資格刑的虛無性特點決定的
資格刑是以剝奪犯罪人的資格為內容的刑罰方法。資格刑的虛無性主要是相對與生命刑、自由刑、財產刑能給犯罪人造成直接的、有形的、物質性的損失的特點而言的,資格是無形的、非物質的,資格刑不能給犯罪人造成直接的、有形的、物質性的損失,因此對犯罪人與不穩定分子缺乏威懾力。剝奪政治權利,是依照法律的規定剝奪犯罪分子一定期限參加國家管理和政治活動權利的一種刑罰方法,在我國是一種主要的資格刑。該刑主要適用于危害國家安全和其他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其內容主要是剝奪犯罪分子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擔任公職權、以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權利。由于歷史、政治體制等原因,我國政治權利的實現程度及公民對其的重視程度都還不夠,所以剝奪政治權利刑罰的制裁力就更加顯得虛無。
(二)過分強調監管手段
所謂社區,是指居民活動的場所。社區所體現的應是一種團結友愛、互幫互助,而非懲治、制裁的氛圍和內涵。顧名思義“社區矯正”應主要采取幫助、感化性質的手段幫助罪犯恢復已受損的心理、行為和社會關系。因此有人定義為,社區矯正不是行刑方式,而是綜合運用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等社會工作方法,協助矯正對象這一特殊群體“重新自我改善”的社會活動。其作用是:聯合所有的社會力量,幫助被矯正對象恢復家庭聯系,獲得就業和受教育的機會,找到自己在社會上的合適位置,進而從根本上減少重新犯罪的危險。但實際上,社區矯正卻成了一種行刑方式,通過采用限制和制裁手段,將原來由公安派出所監管的監外執行的“五種人”轉由社區監管而已。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下發的《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一開頭就將社區矯正定義為: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或裁定規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意識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
(三)司法行政機關未與公安機關聯合起來有機地行使處罰權
社區矯正工作的實施主體是司法行政機關,之前的監管主體是公安機關。一方面是由于公安機關通過多年的履行刑事偵查職能,打擊犯罪樹立了很高的威信,給犯罪分子產生了相當的威懾力。另一方面,就行政處罰職能來講,對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監管對象違反監管規定的行為,公安機關除了可給予監管對象警告外,還可根據《治安處罰法》的相關規定,給予罰款、拘留的處罰,甚至可根據其它規定給予勞動教養的嚴厲處罰。而司法行政機關除了作出警告、記過這類不能給矯正對象造成有形的、直接損失的處罰外,又未與公安機關有機地結合起來、建議公安機關對一些嚴重的行為予以治安處罰。處罰手段的偏弱也導致司法行政機關的威懾力不如公安機關。如有些矯正對象拒絕接受監管的話常常是“公安也不管我,你們來煩什么?”
三、解決對策
剝奪政治權利刑罰即可單獨適用,亦可附加適用。單獨適用的當然在監外執行。對附加適用的又分兩種情況:一是被判處管制而附加的。被判處管制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剝奪政治權利的期間與管制的時間相同,同時執行。由于管制是非監禁刑,是在監外執行的,剝奪政治權利的刑罰也是在監外執行的;二是犯罪分子被判處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緩期二年執行而附加的,剝奪政治權利期間從徒刑、拘役執行完畢之日或者假釋之日起開始計算,這里也是在監外執行的。可見該刑罰具有很強的監外執行性。因此解決好社區矯正工作中的上述問題,不僅有利于社區矯正工作,對剝奪政治權利刑罰本身也具有重大意義。
雖然筆者堅持社區矯正不應作為一種行刑方式的觀點,主張監管和制裁仍由公安或司法行政機關專門進行,社區矯正工作僅由社區作為主體對犯人進行幫教和考察。但從解決問題的實際出發,筆者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下發的《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的精神,在現有工作模式下提出以下對策:
(一)增加保障剝奪政治權利刑罰得以執行的制約性規定
主要是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的形式,增加有關違反剝奪政治權利刑罰行為的制約性規定,強化刑罰的懲罰性和威懾力,維護法律尊嚴。如對犯罪分子被判處剝奪政治權利刑罰執行期間,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和有關監督管理的規定,不服從監督管理或故意脫管、失控的,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通過司法解釋作出區別對待:對情節較輕、事后又有悔改表現的,作出延長原判執行期限時間的決定,將其脫管期間扣除后重新計算執行期的規定;對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由執行機關提請后,人民法院改判拘役或有期徒刑的規定。
(二)為社區矯正工作設計合理的監管措施
剝奪政治權利主要是剝奪犯罪分子以下各種權利:(1)選舉權和被選舉權;(2)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權利;(3)擔任國家機關職務的權利;(4)擔任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職務的權利。監管措施的設計應圍繞“有利于監督矯正對象是否行使這些權利”進行,而不應盲目地限定矯正對象人身自由。如選擇權和被選舉權一般只有在人大或基層換界時才行使,司法所只要在適當時候向相關組織說明某某矯正對象無這兩項權利就行了;如游行、示威具有突發性,結社具有隱秘性,言論、出版具有隨時性,因此若想事前控制矯正對象行使這些權利較難。較經濟合理的監管措施是知道矯正對象的行蹤;關于對擔任公職的控制是容易的,這是因為,一是公職的數量有限,二是因為公職的錄取都經政審程序,三是就算矯正對象擔任了,發現后邊罷免就是了,彌補容易。
綜上,筆者提出如下監管措施:
1.社區矯正機構應建立方便、有效的公示和查詢系統,使矯正對象的情況能為人所知;
2.矯正對象定期向司法所匯報活動情況;
3.矯正對象離開所居住的區域或遷居的,應當報司法所備案。對遷居的,原司法所應當核實矯正對象的新居住地,及時將有關文書材料送到新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和司法所,告知矯正對象按照規定時間向新居住地的司法所報到。
(三)司法行政、公安有機地結合,共同處罰
一方面被判處剝奪政治權利矯正對象不服從監管的多,另一方面對矯正對象是否行使結社、集會、示威等權利的監管難,所以社區矯正機構應重視事后的行政處罰。
1.依法分配行政處罰權。警告、記過處罰權由司法行政機關根據有關規范,如《江蘇省社區矯正對象考核獎懲辦法》第11條、第12條的規定行使;罰款、拘留的處罰權由司法行政機關提出建議,由公安機關根據《治安處罰法》第60條第4款行使;勞動教養處罰權由司法行政機關提出建議,由勞動教養委員會根據《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10條行使。
2.對應受到處罰的違法、違規行為進行細化。詳細規定什么樣的違法、違規行為及違反到什么程度應受到什么樣的處罰。在這方面我們可在實踐中摸索并不斷充實、完善。如江蘇省采取給矯正對象計分的辦法,規定回到多少分時給予什么樣的獎勵,扣到多少分時給予警告或記過的處分。
*江蘇省蘇州市平江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215001]
- 中國檢察官·司法務實的其它文章
- 地方動態
- 檢察資訊
- 正義從哪里來
- 探索檢察工作的和諧創新路
- 一把手、小圈子與攫取資源
- 正義從哪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