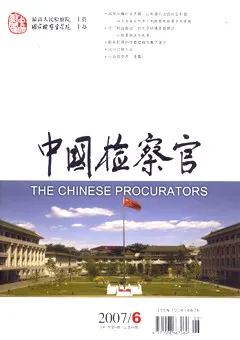趕走搶劫者而拿走被害人錢財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張某將被害人李某綁到樹上,準備搶劫其身上的錢物,王某趕來將張某趕走,而后其將被害人李某身上的錢物拿走,非法據為己有。
二、分歧意見
本案中關于王某的行為定性有如下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應認定為搶奪罪。理由是王某從被害人處取得財物,并未對被害人實施暴力侵害,只是借助于被害人不能反抗的時機,非法取得的。這種取得針對被害人來講是具有公然性的。符合刑法267條之規定,認定為搶奪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應當認定為搶劫罪。理由是王某是通過暴力手段獲取了被害人的控制權,然后將被害人身上的財物非法劫取的,是劫贓行為。符合刑法第263條之規定,認定為搶劫罪。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第一,王某實施了暴力侵害行為,不具備搶奪罪的特征。搶奪罪是行為人趁人不備或者公然奪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所謂趁人不備或公然奪取財物是指行為人在財物的所有人、保管人、使用人在場的情況下,當面奪取財物或者采取可以立即被發覺的方式奪取財物。該犯罪過程行為人不需要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強制手段。當然,行為人作案時也要用力,甚至可能因此而使被害人受到傷害。但其用力不是搶劫犯罪中的用力,搶劫犯罪中的用力是為了加害被害人,使其不敢反抗;搶奪犯罪中的用力是為了控制物,使物到其手中,力是用在了“物”上,即搶奪作案過程中,行為人為了奪取財物是不對人實施暴力的。而本案中,行為人王某從被害人李某身上取得財物應當說是建立在實施暴力侵害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說,王某在主觀上出于故意,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客觀上采取了暴力的手段,通過暴力手段來達到犯罪目的。具體表現就是王某將欲非法取得李某財物的張某毆打趕走,而后再從已經被強制失去人身自由的李某身上非法取得財物。王某對李某的侵害,是張某對李某侵害行為的延續。這一以暴力為達到犯罪目的的作案過程是搶奪罪完全所不具備的特征。
第二,王某實施的是“劫贓”行為。該案定性時應當將整個過程聯系起來,不能分開。王某從被害人李某處取得財物,是在被害人李某被強制的情況下進行的。錢物雖然是在李某身上,可此時的李某被張某捆綁到樹上已經完全喪失了反抗能力,包括其身上的財物已經被張某所控制,成為了其手中的“果實”,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王某采用暴力手段打走張某,又將李某轉到他的控制之下,取得錢物,簡言之,本案的不法侵害是兩步完成,先是張某侵害李某得財,后是王某侵害張某得財,王某、張某的得財均是侵害李某的合法利益,但王某是將張某作為了“加害”的對象,取得了李某的財物,這個財物是張某的非法占有對象,是張某的“利益”,這個利益就是贓物。所以說王某行為是“劫贓”行為。實踐之中,也有一種情況,就是行為人利用財物所有人或者保管人因患病、輕中度醉酒等原因而喪失或基本喪失防護財物能力但神智清醒情況下公然強力奪取或者拿走被害人財物的認定為搶奪罪。這種情況是有別于“劫贓”的,被害人防護財物能力的喪失雖然都不是行為人所為,但是,后者不存在行為人使用暴力或者威脅手段從他人處奪取被害人不能防衛、防護的先決條件的,即后者的行為人的行為不具備“劫”的特征。對于個案立法上不可能窮盡,但是,對于“劫贓”行為卻有類似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下發的《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條中明確規定“搶劫賭資、犯罪所得的贓款贓物的以搶劫罪定罪”。所以說對于王某的“劫贓”行為應認定為搶劫罪。
第三,立法上并未將搶劫罪僅局限于行為人對被害人實施暴力或威脅。刑法第269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證據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263條的規定定罪處罰。這一條就是轉化型搶劫。該類型犯罪,行為人為了保住既得的非法財物對其他人實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暴力或者以暴力威脅的侵害對象既可以是財物的所有者或者是保管者,也可以其他的人。這時的搶劫犯罪就不要求行為人的人身侵害必須是被害人。所以說,認定搶劫罪時要根據案情不能局限于行為人對被害人實施暴力或暴力威脅也是有立法依據的。
綜上所述,王某之行為應當認定為搶劫罪。
*內蒙古科左后旗人民檢察院[028100]
- 中國檢察官·司法務實的其它文章
- 地方動態
- 檢察資訊
- 正義從哪里來
- 探索檢察工作的和諧創新路
- 一把手、小圈子與攫取資源
- 正義從哪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