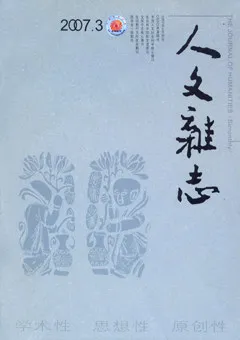科學技術的祛魅及其人類后果
內容提要 科學技術的發明與使用,提高了勞動效率,解放了人自己,為人類帶來了福祉, 這是近代以來人們直觀到的一個基本事實。然而,科學技術卻是一個悖論式的存在,在帶來 創價的同時,也把人們置于危險的境地。于是,對科學技術之原始發生的人性根源、科學技 術本身以及科技的人類學后果進行哲學上的反思與批判是可能的,也是應當的。
關鍵詞 科學技術 祛魅 錯置 返魅 人文生態
〔中圖分類號〕B0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 X(2007)03-0009-07
1.對科學與技術作出適當的區分,對于把捉科學技術的本質很有意義。
科學之能夠成為其自身的東西在于它所把握的那個對象以及把握那個對象的方式。人們為著 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無時無刻不在感知著這個世界,從而形成諸種表象,借以表達他們對事 物的看法。但這些感知和看法并不總是揭示出事物的本真狀態,因為人們的日常感知和日常 意識常常是既無興趣也無能力把捉這個本真狀態。當人們超越于個人基于日常需要的打算而 “陷入”對事物的沉思的時候,學術和科學才有可能產生。“在所有這些發明相繼建立以后 ,又出現了既不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樂為目的的一些知識,這些知識最先出現于人 們開始有閑暇的地方。數學所以先興起于埃及,就因為那里的僧侶階級特許有閑暇。”(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 版,第3頁。)閑暇產生理論學術。但這并非說科學毫無用處,它不是為著某個人的, 而是為著整個人類的利益。“科學的首要目標乃是發現事物和事件的本質和規律,從而我們 能夠理解和解釋它們。這種關于事物和事件的知識總是帶來高度的實利,以新的利益豐富人 類生活,幫助聰慧的人們在他們生活于這個偉大世界的短暫一生確定自己的方針。”(注:〔英〕亞?沃爾夫著:《十六、十七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下), 周昌忠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5月版,第518頁。)只有擺脫了日常雜務和生活 煩惱的糾纏而又執著真理的人才有可能從事科學研究,閑暇和興趣是科學得以可能的兩個必 要條件。科學起于日常觀察和日常生活但不終止于日常意見和日常意識,科學的目標在于把 握真理,由這一點所決定,科學始于觀察而止于沉思。真理與每個人相關,但并非每個人都 對發現真理和陳述真理有興趣。為著發現真理的目的,研究者除了具備靜觀和沉思之外,尚 需具備創造概念和語言的能力,并依照適當的秩序即邏輯將真理陳述出來。一當用極具統攝 力和穿透力的概念和語言去陳述那個與每個人須臾不可分離但卻難以顯現的真理時,就不再 是意見和常識,而是理論。“我們可以用簡單扼要的一句話來陳述科學的本質。這句話便是 :科學是現實之物的理論。”(注:〔德〕海德格爾著:《科學與沉思》,《海 德格爾選集》下卷,孫周興譯,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9月版,第956頁。)只有理 論把握世界的方式才是科學,但科學僅僅是人類把握世界多種方式中的一種,既不是唯一的 也不是全部。除了科學的方式之外,還有宗教的、藝術的、實踐-道德的以及日常經驗的, 可以說,包括科學在內,它們都是真理顯現其自身的方式,也許除了科學之外,其他的方式 更能接近真理。然而,在科學即知識,知識即權力的今天,科學帝國主義似乎把其他方式擠 壓到了生活世界以外,似乎它們已經不重要,于人的生活可有可無,實質上,這是經濟帝國 主義侵略一切的一個科學后果,經濟主義或功利主義是這一后果的價值觀基礎。
就其精神實質來說,科學原本是靜觀和沉思的產物,它同藝術一起將那些向人走來的是其所 是的事物的本質顯現出來、揭示出來,使它們亮出耀眼的光輝。這些光輝常常是隱藏著的, 它只把它的一部分、也許不那么光輝的一面顯現給人。“在古希臘早期的所思和所詩在今天 仍然是當下的,它們是如此地當下,以至于它們所具有的那些對其自身也遮蔽的本質處處都 在等待著我們并向我們走來。”(注:〔德〕海德格爾著:《科學與沉思》,《海德格爾選集》下卷,孫周興譯,上海三聯書店, 1996年9月版,第957頁。)科學和藝術作為人類靜觀、傾聽的結果,沉思和發見的產 物,原本是解蔽的方式,它們不是傷害真理,而是要使真理顯現它的光輝。這就是科學的真 理,它是科學得以存在的最為原初的理由。與技術相比,科學并未使事物發生任何實質性的 變化,事物依然作為事物保持其自身,無論是直觀的還是遮蔽的,它們都如其所是地在場著 ,是各種各樣的在場者。人也是這諸多在場者中的一員,然而他卻是特殊的在場者,他不但 通過理論的方式把那些與人有關的在場者納入到自己的表象中,而且有自身的目的,這與其 他在場者沒有本質區別,他還要把這種目的作為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從而在他所創造的對 象中直觀其自身,從而實現自己的目的,這是人作為在場者與其他在場者根本不同的地方。
技術是人實踐地改造對象的主要方式,它與理論把握世界的方式不同,它不滿足于觀念改造 對象的狀況,它要使世界發生現實的變化。實踐-技術掌握世界的方式使其他在場者甚至自 身發生結構、狀態與關系上的變化。它改變了事實狀態,關系不同,狀態不同,結構和功能 就必然不同。科學與技術具有錯綜復雜的關系:“科學或純粹科學關心的是發現真理;而技 術關心的則是發明新的東西和工藝或者改進舊的。兩者當然緊密相關的,今天尤其這樣。” (注:③〔英〕亞?沃爾夫著:《十六、十七世紀科學、技 術和哲學史》(下),周昌忠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5月版,第519頁。)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關系經常被誤解,技術經常被說成僅僅是“應用科學”。有時候,人們 先是得到某些現象的科學知識,然后再把這種知識運用于某個實用目的。這種情況多是近代 以來的事情。而在中世紀和古代則往往是技術先于科學。“在人類文明史上,無疑是實用發 明的進步走在有關現象的理論知識的進展的前面。甚至在近代最初的幾個世紀里,雖然有時 科學進展促進了實際應用,但更經常的是已有技術方法為科學發現提供了資料;而且恐怕技 術發明和改進大都是在根本沒有純粹科學幫助的情形下進行的。”③這可以從以下的實例中得到進一步地說明。農業、建筑、礦業、玻 璃與陶 瓷制造以及紡織工業等重要技術在十八世 紀以前,從科學得到的幫助微乎其微。有時實際上倒是科學向已有的技術方法學習,而不是 科學教給技術方法什么東西。近代科學的先驅們希望和期待科學和技術之間存在一種極端密 切的關系。那種為知識而知識的觀念對他們沒有什么魅力。事實上,他們的最大愿望是,這 新科學與舊的書本知識不同,將非常實用;新的知識將賦予人類以力量,使人類得以成為自 然界的主人。培根對獲得成果的實驗的愛好至少不下于對提供啟示的實驗的愛好;伽利略做 了建筑材料強度的實驗;早期的科學院全部都致力于實用的發明。實際上,科學與技術盡管 分屬于不同的領域,但它們同為解蔽的方式,由科學知識遷移到實驗和生產存在內在的邏輯 要求。問題不在于此,而在于倘若決定于科學之成為可能的形而上學基礎發生了質的改變, 并把這種改變了的形而上學基礎貫徹到技術中去的時候,科學技術的危機才會到來。
2.亞里士多德把人的靈魂肯定和否定真的方式分成五種:技藝、科學、明智、智慧和努斯。在這五種方式中,只有明智和智慧是德性。他進一步區分了理智與智慧的關系:努斯是把握 始點(原因)的,理智是派生的;而科學、技藝和明智是作為派生物的理智的三種形式,以 此來看,科學不屬于努斯的范圍;而智慧是對這三種衍生的理智以及努斯的總體把握。努斯 是事物是其所是的理由、根據,是事物運動起來的原因,發現這種根由并使之顯現出來乃是 科學的事情,然而讓事物顯現其自身而又不傷及自身,乃是智慧,智慧是一種德性,而科學 則不是,它只是理智的一種形式。技藝也是如此,不過亞里士多德更多地是使用技藝而少用 技術,即使使用技術也是在技藝的意義上進行的。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給出 了技藝的簡約而不簡單的表述:“可變化的事物中包括被制作的事物和被實踐的事物。但是 制作不同于實踐,實踐的邏各斯的品質同制作的邏各斯的品質不同。其次,它們也不互相包 含。實踐不是一種制作,制作也不是一種實踐。例如建筑是一種技藝,是一種與制作相關的 、合乎邏各斯的品質。如果沒有與制作相關的品質,就沒有技藝;如果沒有技藝,也就沒有 這種品質。所以,技藝和與真實的制作相關的合乎邏各斯的品質是一回事。所有的技藝都使 某種事物生成。學習一種技藝就是學習使一種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事物生成的方法。技 藝的有效原因在于制作者而不是被制作物。因為,技藝同存在的事物,同必然要生成的事物 ,以及同出于自然而生成的事物無關,這些事物的始因在于它們自身之中。如果制作與實踐 是不同的,并且技藝是同制作相關的,那么技藝就不與實踐相關。在某種意義上,技藝與運 氣是相關于同樣一些事物的。正如阿加松所說,技藝愛戀著運氣,運氣愛戀著技藝。所以, 如上面所說的,技藝是一種與真實的制作相關的、合乎邏各斯的品質。其相反者,無技藝, 則是同虛假的制作相關的邏各斯品質。兩者都同可變的事物相關。”(注:② ③〔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尼各馬可倫理學》,廖申白譯,商務印 書館2003年11月版,第171-172、3、174頁。)
從亞里士多德關于技藝的陳述中,我們解讀出這樣幾層意思。第一,技藝與制作相關。制作 的目的往往在制作之外。“每種技藝與研究,同樣地,人的每種實踐與選擇,都以某種善為 目的。”②當目的是活動以外的產品時,產品 就自然比活動更有價值,盡管制作有多種,目的也有多種,如醫術的目的是健康,造船術的 目的 是船舶,戰術的目的是取勝,理財術的目的是財富。主導技藝的目的就比從屬技藝的目的更 被人欲求,因為后者是因前者之故才被人欲求的。既然技藝作為制作常常在于欲求一個不是 制作本身的他者,因之技藝經常作為手段 而出現。第二,作為追求他者的技藝或制作并不是任意的,雖出于制作者而非被制作之物 ,但卻不是任性的活動,有邏各斯存在著。因而制作是一種合規律的活動。技藝所處理的是 可變化、可生成的事物。可生成的事物作為一個事物有它屬于它自身的生成方式,諸種生成 方式均是事物是其所是的方式。當技藝借助于其中的一種或多種生成了制作者所期望的過程 或結果而又未傷害被制作者,便是體現了邏各斯的要求,或具有了邏各斯的品質。第三,藝 術是技術的原生形態。因為,它使每一個在場者通過技藝的方式而彰顯出來,成為敞開的一 個領域。人之能夠做到這一點全都仰賴于智慧這種德性。第四,亞里士多德雖未像海德格爾 那樣給出關于技術的深刻分析,但這恰恰說明,古代的技術是作為技藝而存在的,而近代的 技術是作為純粹手段而使用的;在古希臘,在技藝之上不僅有智慧,還有努斯存在,而智慧 又是努斯與科學的結合,科學高于技藝,努斯高于智慧。“科學是對于普遍的、必然的事物 的一種解答。而證明的結論以及所有科學都是從始點推出的(因為科學包含著邏各斯)。所 以,科學據以推出的那些始點不是科學、技藝和明智可以達到的。”③而智慧顯然是各種科 學中的最完善者,在技藝上,智慧這個詞則用于述說那些技藝最完善的大師。有智慧的人不 僅知道從始點推出結論,而且真切地知曉那個始點。所以,智慧必定是努斯與科學的結合, 必定是關于最高等的題材的、居首位的科學。智慧不是現成之物,它是愛智慧的活動,即與 智慧不能分舍的追求智慧的活動,作為努斯與科學的結合,它便是哲思。這也是亞里士多德 把沉思視為幸福諸項中最幸福的項目的緣由。因為在他看來,享樂和政治的生活都是不完善 的。幸福是相應于人的特有活動的,在于人的合德性的活動。而人特有的活動就是他的靈魂 有邏各斯的部分的實現活動。所以幸福就是人的靈魂的有邏各斯的部分合于德性的實現活動 。然而靈魂的有邏各斯的部分又有理論的與推理的兩部分。若幸福是合于德性的活動,它必 定是合于我們自身中那個最好的部分即努斯的德性的活動。這就是沉思的生活。因為,努斯 的實現活動最完美、最能夠持續、最令人愉悅、最為自足,既有嚴肅性又除自身外別無目的 ,且擁有閑暇。努斯是我們的真正自我,是我們之中最好的東西。故過著沉思生活的、有智 慧的人最幸福。倘若丟掉了智慧,遮蔽了努斯,技藝就成了無根之在者。當技藝僅成了技術 ,成了單一的手段,技藝便變成了海德格爾筆下的促逼、挑戰。海德格爾的技術定義是現代 技術的哲學形態,與亞里士多德的技藝相比,海德格爾的技術顯得那樣冷酷,讓人覺得失望 與悲傷。這種悲傷不是哲學家的自憐,也不是自作多情,它是現代生活世界危機的科學技術 形態。那么,現代科學技術是一種何種樣式的科學技術呢?現代科學技術危機的形而上學基 礎在那里呢?
3.可以說,海德格爾對技術的追問是人類學式的,他把科學技術置于一個人類的視野內,并 從根源處找尋近代以來造成科學技術危機的緣由。可以說,現代化、現代性、現代主義、科 學、技術、解蔽、藝術是混為一體的,它們只是現代社會的諸項征候和癥候。當人們質問現 代性怎會如此這般的時候,危機意識便隨之產生,一如我們不能追問人是誰一樣。“人類學 是這樣一種對人的解釋,它根本上已經知道人是什么,因而從來不能追問人是誰。因為隨著 這一問題,它勢必要承認自己受到了動搖,被克服了。”(注:〔德〕海德格爾著:《世界圖象的時代》,《海德格爾選集》,下卷,孫周興譯,上海 三聯書店,1996年9月版,第923頁。)技術 也是這樣,當我們追問技術是什么、技術應該是什么的時候,技術的危機便昭然若揭了。
依照慣常的理解,技術是合目的的工具;技術是人的行為。實際上,關于技術的這種意見是 一體的,因為,設定目的,創造和利用合目的的工具,本來就是人的行為。“技術之所以是 ,包含著對器具、儀器和機械的制作和利用,包含著這種被制作和被利用的東西本身,包含 著技術為之效力的需要和目的。這些設置的整體就是技術。技術本身乃是一種設置,用拉丁 語講,是一種工具。”(注:③④〔德〕海德格爾著:《技術的追問》,《海德格爾選集》,下卷,孫周興譯,上海 三聯書店,1996年9月版,第925、931、932頁。)用工具性和目的性兩個特質來規定技術,表明了人們試圖既在觀念 上又在事實上控制技術的努力。而且,技術愈是有脫離人類統治的危險,人類對技術控制的 意愿就愈加迫切。把技術視為工具性的存在無疑是直接而確然的,即正確的,但單純正確的 東西還不一定是真實的東西。只有真實的東西才會把我們帶入一種自由的關系中,即與那種 從其本質來看關涉于我們的關系中。由此觀之,技術的工具性規定還沒有向我們顯明技術的 本質。我們必須問:工具性的東西本身是什么?一個工具乃是人們借以對某物發生作用、從 而獲得某物的那個東西。導致某種作用的東西,人們稱之為原因。但原因不只是另一個東西 借以產生出來的那個東西。工具之特性據以獲得規定的那個目的,也被看作原因。目的得到 遵循,工具得到應用的地方,也就是因果性即因果關系起支配作用。在海德格爾看來,亞里 士多德的質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和結果因乃是使某個在場者在場的招致方式。四種招致方 式把某物帶入顯現中,它們使某物進入在場而出現;它們把某物釋放到在場中,并因而使之 起動,亦即使之進入其完成了的到達之中,使某物成其為是其所是的東西。對總是從不在場 者向在場過渡和發生的東西來說,每一次引發都是出場,都是產出。“產出”就是帶出來,生產、創造、創作、帶來;使不在場者在場并顯現,使在場者但未顯現者顯現其為自身,這 就是技術的本質或宿命。這樣,我們便從關于技術的日常觀念即工具性的觀念那里起始而推 進到了技術的“真理”那里,到了解蔽那里。“一切生產制作過程的可能性都基于解蔽之中 。如此看來,技術就不僅是手段。技術乃是一種解蔽方式。倘我們注意到這一點,那么就會 有一個完全不同的適合于技術之本質的領域向我們開啟出來。此乃解蔽之領域,亦即真理之 領域。”③技術一詞來自希臘語,但亞里士多德 用技藝而很少用技術。因為,“技藝”不只 是表示手工行為和技能名稱,它也表示精湛技藝和美好藝術的名稱,技藝屬于產出,是某種 創作。“技術是一種解蔽方式。技術乃是在解蔽和無蔽狀態的發生領域中,在技藝即真理的 發生領域中成其本質的。”④
海德格爾用“解蔽”( das Entbergen)來表述技術的本質。“das Entberg en”是使某物由遮蔽狀態進入無蔽亦即敞開狀態的過程,這種進入是一種產出、帶出、引 發,它們不是強制,既不是揠苗助長也不是拔苗助長,而是順其自然,是自然而然。“不論 在自然中,還是在手工業和藝術中,這種產出是如何發生的呢?引發的四重方式 即亞里士多德所說的“質料因”、“形式因”、“目的因”、“結果因”。在海德 格 爾看來,這是幾百年來,哲學一直教導我們的。在其中起作用的這種產出是 什么呢?引發關涉到一向在產出中顯露出來的東西的在場。產出從遮蔽狀態而來進入無蔽狀 態而帶出。唯就遮蔽者入于無蔽領域到來而言,產出才發生。這種到來基于并且回蕩于我們 所謂的解蔽(das Entbergen)中。”(注:〔德〕海德格爾著:《技 術的追問》,《海德格爾選集》,下卷,孫周興譯,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9月版,第930頁。)而席勒早在韋伯 一個世紀前就注意到了自然的祛魅問題,他用的是“Entgotterung”一詞,其字面含義 是自然的非神性化,或去掉自然神秘性的、神性的過程。而韋伯在形容祛魅時用的是“Entzauberung”一詞,字面含義是“驅除魔力”。綜觀席勒、韋伯、伽利略、笛卡兒等 人的“祛魅”觀點以及物理學中的客觀化的、機 械論的、還原論的方法,其“祛魅”的基本主張是作為結果存在的自然的“裸化”,被現代 科學、技術和哲學“毀滅”了的自然,而未能像海德格爾那樣,看到了現代科學、技術、哲 學的二重性,它們既是造成自然被促逼、擺置的誘因,也是拯救地球的入口。“但哪里有危 險,哪里也有救。”也許席勒、韋伯等人也在“祛魅”的概念中蘊涵著拯救危機的出路,但 至少在一些后現代主義研究者那里被作了否定的、悲觀的理解。“自然的祛魅”的含義是什 么?從根本上講,它意味著否定自然具有任何主體性、經驗和感覺。由于這種否認,自然被 剝奪了其特性——即否認自然具有任何特質;而離開了經驗,特性又是不可想象的。在自然 被“祛魅”的過程中,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類精神可以感受到親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 何規范了。人類生命變得異化和自主了。在這些學者看來,自然的祛魅這種觀點最初是在二 元論的超自然論的框架內由伽利略、笛卡兒、波義耳和牛頓及其同道者們提出的。二元論的 超自然論認為,靈魂和個人神性具有解釋功能和因果力量,在物理學中客觀化的、機械論的 和還原論的方法的成功很快就使人們堅信,這種方法應適用于現實中的所有事物。上帝首先 被剝奪了除原始創造力量以外的一切因果力量;其后,思想家們將這種自然神論變成了徹底 的無神論。人類靈魂或人的心靈最初被說成是“副現象的”,意即它是實在的,但它只是果 ,而非因;再其后,思想家們相信自然不存在不旋轉的車輪,否認心是一個特殊的實體,宣 稱它不過是大腦所具有的一種性質而已。因而,將因果性歸因于人性力量的泛靈論觀點遭到 了徹底的否定。所有從人性到非人性過程的“向下的原因”都被革除;用基本的非人性過程 解釋一切的還原論方法被廣泛接受。就這樣,整個世界被祛魅了。這種祛魅的觀點意味著, 不僅在“自然界”,而且在整個世界中,經驗都不占有真正重要的地位。因而,宇宙間的目 的、價值、理想和可能性都不重要,也沒有什么自由、創造性、暫時性或神性。不存在規范 甚至真理,一切最終都是毫無意義的。(注:③〔美〕大衛?雷?格里芬著:《后現代科學——科學魅力的再現》,馬季方譯,中 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4、2頁。)格里芬雖然分析了世界祛魅過程的形而上 學基礎, 但把祛魅僅僅歸結為哲學與科學的原因,似乎值得進一步討論。“在祛魅的自然中,關于自 然的現代科學導致了自然本身的祛魅。這是由于,關于自然的機械論的、祛魅的哲學最終導 致了整個世界的祛魅;這種哲學最初是關于作為一個整體的實在的二元論和一神論觀點的一 部分。”③從某種意義上,這 種結論可能是正確的,但導致現代世界祛魅之結果一定還有更 為深層的原因。其中技術就是重要的方面。海德格爾對技術之二重性的分析已經深入到了科 學、技術等表象背后的深層問題,胡塞爾就曾以“作為歐洲人根本生活危機表現的科學危機 ”為題論證了,隨著科學的不斷成功,科學卻喪失了其對生活的意義。胡塞爾在《歐洲人的 危機與哲學》一文中的結尾處指出:“今天人們談論很多的、在生活的崩潰的無數征兆中表 現出來的‘歐洲生存的危機’,并不是一種神秘莫測的命運,也不是無法看穿的災難,相反 ,它在可以從哲學上加以闡明的歐洲歷史的目的論的背景上是可以理解和看清的……‘危機 ’是理性主義的表面上的失敗。但是合理的文化的這種失敗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理性主義本質 本身,而僅僅在于將它膚淺化,在于它陷入‘自然主義’和‘客觀主義’”。(注:〔德〕胡塞爾著:《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王炳文譯,商務印書館200 1年12月版,第403-404頁。))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技術變成了使自然祛魅的主要力量呢?
4.當我們以“技術是一種解蔽方式”這種觀念看待現代技術時,古希臘式的手工技藝已被現 代的動力機械技術所替代,海德格爾所指明的技術的真理領域已不見蹤跡。海德格爾說,恰 恰是這種動力機械技術,而且也只有這種動力機械技術,才是一種不安的因素,促使我們去 追問“這種”技術。其實,無論現代技術怎樣地不同于古代技術,但它依然是技術,只是技 術中一種不能令人滿意的那種類型而已。既是技術,它就依然是一種解蔽的方式。解蔽貫通 著并統治著現代技術。但這里,解蔽并不把自身展開于技藝意義上的產出。在現代技術中起 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種促逼(Heraus fordern),是一種挑戰、挑釁、引起,此 種促逼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與順其自然的古 代技術不 同,某個地帶被促逼入對煤炭和礦石的開采之中,這個地帶于是被揭示自身為煤炭區,礦產 基地。農民先前耕作的田野的情形則不同;這里,“耕作”還意味著:關心和照料。農民的 所作所為并非促逼耕地。在播種時,他把種子交給生長之力,并且守護著種子的發育。但現 在,就連田地的耕作也已經淪于一種完全不同的擺置著自然的訂造的旋渦中了。它在促逼的 意義上擺置著自然。于是,耕作農業成了機械化的事物工業。空氣為著氮料的出產而被擺置 ,土地為著礦石而被擺置,鈾為著原子能而被擺置,而原子能則可以為毀滅或和平利用而釋 放出來。
這種促逼著自然能量的擺置乃是一種雙重意義上的開采。在自然的意義上,自然的能量在被 開采之前,是遮蔽著的、隱藏著的。通過解蔽的方式,哪怕是促逼的方式,它被呈現為是有 能量的在場者,從而將其光輝的一面亮給人看。由此觀之,技術自始至終還是有其存在的理 由的。但技術卻包含著將開采帶入促逼的境地的危險,因為,作為被促逼的自然并未僅僅簡 單地作為煤炭或礦石而在某地現成地存在亮在那里,任其閃著耀眼的光輝而自在地擺置在那 里。開采者決不止于此,他要把基于促逼之上的擺置帶入屬于他自己的目的系列。看來,在 現代技術那里,解蔽者并非為著使與之相關的物出場、在場者顯現是其所是的那種東西,而 是把它們當作一個要素、一個質料、一個對象來加以擺置的,他是為著自身才對在場者現出 自身而感興趣的。煤炭蘊藏著,也即,它為著對在其中貯藏的太陽熱量的訂造而在場的。太 陽能為著熱能而被促逼,熱能被訂造而提供出蒸汽,蒸汽的壓力推動驅動裝置,由此,一座 工廠便得以保持運轉了。當開發、改變、貯藏、分配、轉換諸環節被關聯起來并保持一個流 動時,解蔽就進入到一個“持存”的過程,這個“持存”恰是解蔽者之目的系列。
通過促逼著的擺置,人們所謂的現實便被解蔽為持存。那么誰來完成這種擺置呢?顯然是人 。人何以能夠做這種解蔽呢?誠然,人能這樣那樣地把此物或彼物表象出來,招致出場,使 之成形,并且推動它。可是,現實向來于其中顯示出來或隱匿起來的無蔽狀態,卻是人所不 能支配的。而人卻常常受到來自于自身欲望的發動,超出此物或彼物設定給人的界限,或者 使在場者失去存在,或者沒有把在場者的存在揭示出來。受到促逼的就不僅是此物或彼物, 還包括人本身。于是,唯就人本身已經受到促逼,去開采自然能量而言,這種訂造著的解蔽 才能進行。如果人為此而受到促逼,被訂造,那么人不也就比自然更原始地歸屬于持存么? 一如馬克思所說,人首先是受動存在物然后才是能動存在物,一當人不能自主,不能變成能 動的存在物,只被欲望支配著,集體被聚集起來的欲望推動著的時候,人借助于技術滿足欲 望的活動就必定使自己被原始地置于促逼的狀態中。與馬克思的勞動異化論相比,這實際上 是技術異化論,被異化的不只是自然還包括人本身。每個人可能在一個自主的范圍內控制、 疏導自己的欲望,而由若干個人被膨脹起來的欲望組成一種社會流動時,被聚集起來的欲望 就像一個力大無比的怪物,就像霍布斯的“利維坦”一樣,牽制人并控制著人,科學技術和 社會規則是它的實現方式,自然和人是實現它的手段。在此情境下,技術獲得了控制人的假 象,實際上,技術不過是那個怪物控制人的一種手段。此時的技術,無論對自然和人來說都 不再是一種單純的解蔽方式,不再是設置、培育、引發、帶出,而變成了一種錯置,這種錯 置就是“座架”。“座架(Ge-stell)意味著對那種擺置(Stellen)的聚集,這 種擺置擺置著人,也即促逼著人,使人以訂造方式把現實當作持存物來解蔽。座架意味著那 種解蔽方式,此種解蔽方式在現代技術之本質中起著支配作用,而其本身不是什么技術因素 。相反,我們所認識的傳動桿、受動器和支架,以及我們所謂的裝配部件,則都屬于技術因 素。但是裝配連同所謂的部件卻落在技術工作的領域內;技術工作始終只是座架之促逼的響 應,而決不構成甚或產生出這種座架本身。”(注:〔德〕海德格爾著:《技術的追問》,《海德格爾選集》,下卷,孫周興譯,上海三聯書店 ,1996年9月版,第938-939頁。)于是,關于技術的追問就涉及到三個主 題:技術是 什么?技術是一組或若干組設備、配件、裝置,是在物與物之間、人與物之間、人與人之間 完成的一種設置。技術的本質是什么?技術的本質不是指技術因素,它不是一組或數組物的 要素,它是這些物的要素被擺置起來作用于物與人的方式,既是解蔽的方式,也是遮蔽的方 式。當技術使事物的真理得以顯現時,也即使在場者出場、在場并顯現存在時,技術不是強 制、促逼、挑戰,而是順其自然,是培養 、招致、引出,是真理顯現其光輝的方式;當技術不顧此物或彼物的呼聲,而是任性地、一 意孤行地任由擺置者的欲望的擺置,技術就成了一種促逼。“座架”是現代技術之促逼性質 的典型形態。現代技術的本質意味著什么?“促逼”、“座架”意味著現代技術變成了純粹 的手段,而且是不顧人之外的自然、人本身的自然的呼聲,而僅僅是滿足膨脹欲望的手段。 這種追問技術的方式,不僅僅是經濟學的、哲學的和 倫理學的方式,更是一種人類學的方式。只有也只有從人本身,從人是什么和應該是什么的 立場出發追問技術是什么才有意義,且是唯一徹底的追問方式,因為科學技術不過是人對待 自然和人本身的一種方式而已。“促逼”、“座架”之得以發生,并非僅僅在于促逼者和座 架者單獨造成,而是被預先聚集起來的已經不屬于人但卻控制人的膨脹欲望牽引出的。
在技術被錯置、人被聚集的欲望牽引出來的境域下,人類如何為呢?又向何處為呢?
5.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同時人又是社會的類的存在物,于是自然和社會就規定給人以命運。 命運不是宿命,而是一種敞開狀態,是真理,即自由。“自由掌管著被澄明者亦即被解蔽者 意義上的開放領域。”人既是解蔽者、澄明者,又是被解蔽者和澄明者。自由與解蔽處于最 切近和緊密的親緣關系中。一切解蔽都歸于一種庇護和遮蔽。而被遮蔽著并且自行遮蔽著的 ,乃是開放者,即神秘。一切解蔽都來自開放領域,進入開放領域,帶入開放領域。然而, 作為現代技術的促逼和座架卻改變了真理、自由指引給人的道路,把我們囚禁于一種昏沉的 強制性中,逼使我們盲目地推動技術;一方面,我們一味地發展技術、使用技術,另一方面 ,我們又無助地去反抗技術,把技術當作惡魔來加以詛咒。這是現代技術規定給人的命運。 解蔽之促逼、座架的命運卻是一種危險的命運,“在其所有方式中都是危險,因而必然是危 險。”此危險在兩個方面向我們表明自身:“一旦無蔽領域甚至不再作為對象,而是唯一地 作為持存物與人相關涉,而人在失去對象的東西的范圍內還只是持存物的訂造者,那么人就 走到懸崖的最邊緣,也即走到了那個地方,在那里人本身還只被看作持存物。但正是受到如 此威脅的人膨脹開來,神氣活現地成為地球的主人的角色了。由此,便有一種印象蔓延開來 ,好象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只是由于它們是人的制造品。這種印象導致最后的惑人的假 象。以此假象看,仿佛人所到之處,所照面的只還是自身而已。但實際上,今天人類恰恰無 論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質。”(注:〔德〕海德格爾著:《技術 的追問》,《海德格爾選集》,下卷,孫周興譯,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9月版,第945頁。)
技術原本是人的一種解蔽方式,然而作為一種設置,不僅改變著人外的自然和自身的自然, 也從根本上改變著人思維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總之改變著人本身。一如海德格爾所 言,我們已經進入一個世界圖象的時代。人要把包括人在內的整個世界統攝到它預先構置出 來的理念框架里,然后再根據它的偏好進行價值排序,借助技術的力量實現它所謂的人的需 要。如果說,在笛卡兒時代,一切存在物的合法性都取決于理性的審判與認可,那么今天, 包括人的身體在內,人的能力所及的事物都要接受技術的分解與構成。風險社會的來臨,雖 不完全是科學技術的結果,但今天,自然的裸化、心靈的直白總是和科學技術的祛魅功效有 著干系,在科學技術面前,一切神秘的東西都無所遁其身。科學技術之祛魅功效的人類后果 逐漸顯露出來。
由科學技術的祛魅所帶來的種種危險作為后果正在改變著人的生存境遇,也改變著人的生活 方式。解決問題的根本道路在于,將人類用于開發身外的自然和人自身的自然的努力轉向為 開發人的精神資源,亦即創造人的精神產品,培養用于提升心志力量的興趣與品質。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
責任編輯:張 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