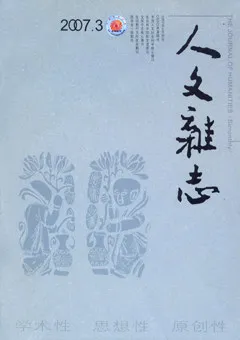境界形態與實然形態的雙重涵攝
內容提要郭象之逍遙義包含圣人之“無待”逍遙與眾生之“有待”逍遙兩個層次:前者從“心”上言逍遙,屬主觀的境界形態,是對莊子逍遙義的承接;后者從“性”上言逍遙,屬客觀的實然形態,是對莊子逍遙義的拓展。對郭象逍遙義兩個層次的分析,直接關系到對其性質的判定。學界以“適性逍遙”指稱郭象之逍遙義,遺落了其義中的圣人逍遙一層,對此的澄清,有助于對郭象逍遙義的深化理解。
關鍵詞逍遙義無待逍遙有待逍遙境界形態實然形態
〔中圖分類號〕B235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07)03-0031-05
郭象通過注解《莊子》,對莊子的逍遙理論進行了創造性的闡發,形成了所謂的“適性逍遙”論,學界也皆以“適性逍遙”稱述郭象的逍遙義,對其性質的判定亦有主觀的境界形態與客觀的實然形態之異。然細繹郭象《莊子注》對逍遙之論述,則可知“適性逍遙”僅限于對眾生逍遙之指稱。除此之外,在郭象的逍遙義中,還包含圣人之逍遙一層。故郭象之逍遙義實涵攝圣人之逍遙與眾生之逍遙兩個層次:就前者而言,表現為自“心”上言之境界形態;就后者而言,則表現為自“性”上言之實然形態。唯有以此雙重形態觀郭象之逍遙義,方可明郭象對莊子逍遙理論之承接與發展。
一、問題之提出
《莊子》的開篇是《逍遙游》,郭象對“逍遙游”所做題解為:“夫小大雖殊,而放于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于其間哉!”(注:郭象:《逍遙游注》,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第1頁。)并在《莊子注》中對此“適性逍遙”論進行了透徹的論述,這可能也是學界皆以“適性逍遙”稱述郭象逍遙義的原因。然而《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對于郭象之逍遙義卻有如下記述:
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茍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蕓蕓,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遙耳。唯圣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于大通矣。(注:對于《莊子注》作者的歸屬問題,筆者認為今本《莊子注》是郭象在向秀《莊子注》的基礎上“述而廣之”的結果,可以歸于郭象名下。而《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引的向、郭逍遙義,與今本《莊子注》中的逍遙義相合無殊,故可以郭象逍遙義稱之。)
《莊子?逍遙游注》中亦有相似的論述:
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游變化之途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茍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于大通矣。
就劉注所記與郭象所注可知,郭象的逍遙義分明內含兩個層次:一是圣人之無待逍遙,二是眾生之有待逍遙。眾生之有待,實源于其各自性分之限制,而圣人卻能夠順萬物之性,游變化之途,因超脫了具體性分的拘限,故為無待的存在。由此可知,所謂“適性逍遙”在內容上指的僅是眾生之有待逍遙。然而學界卻以“適性逍遙”指稱郭象的整個逍遙義,在對其性質的判定上亦有境界形態與實然形態之不同觀點。由此而產生的問題便是:圣人逍遙與眾生逍遙在本質上能否通約?“適性逍遙”在內容上能否涵蓋圣人逍遙與眾生逍遙兩層義理?郭象逍遙義的性質究竟是境界形態還是實然形態?本文即從圣人之無待逍遙、眾生之有待逍遙,以及二者的關系展開對郭象逍遙義的討論。
二、圣人之“無待”逍遙
郭象對逍遙無待、有待的區分來源于莊子,莊子將逍遙分為“有待”與“無待”,也即逍遙有相對與絕對之分,而只有無待逍遙才是真正的逍遙。莊子所說的無待逍遙可用一句話概而言之:“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注:莊子:《逍遙游》,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第17頁。)此又可分為二端:其一,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即是對無待逍遙的描寫,此是一博大無礙、物我相冥的自由境界;其二,無待逍遙之主體是至人、神人和圣人,此三者其實異名同實,且無待逍遙并非現成可得,而是要經過主體自我修證的工夫,去除一己成心的限制方可達到,所謂“無己”、“無功”、“無名”即是對一己之“心”所作的去執的工夫,是在“心”上用力,將“成心”轉化為“道心”,以突破一己形骸和外在環境的拘限,這與莊子所說的“心齋”、“坐忘”的工夫是相互通貫的。以莊子之意,唯有圣人有自覺的修證工夫,蕓蕓眾生卻缺乏這種自覺性,而拘限于一己成心的遷流之中,因此無待自由的主體只能是至人、圣人和神人,而所謂無待逍遙也只是一種主觀的境界形態,這由莊子言逍遙恒與“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塵垢之外”等連用亦可得證明(注:如《莊子?逍遙游》曰:“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徨乎吾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莊子?大宗師》曰:“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莊子?達生》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由此可以說,莊子所開顯的無待逍遙境界,是莊子超拔自然生命、向往生命自由解放的一種要求,而這種要求也是人類心靈的一種普遍祈向。同時,這種境界因為需要通過艱苦的修證工夫方可達致,因此并不具有普遍的現實性,而只能成為蕓蕓眾生向往的一種理想狀態。郭象對莊子所言無待逍遙的注解是:
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游變化之途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注:④郭象:《逍遙游注》,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第20、11頁。)
郭象以“順萬物之性、游變化之途”來解釋莊子所說的“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是極為恰當的,順萬物之性,即是玄同彼我、與萬物冥合為一,無所對待對立;游變化之途,即是不沾滯于外在條件的變化而與之俱化,不生是非好惡之心。毫無疑問,以上兩方面必須從“心”上用力,借助于自我修證的工夫方可達到。郭象又說:“若夫逍遙而系于有方,則雖放之使游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④“系于有方”即是對大小是非存有分別之心,有此分別即使放之使游亦無法達致無待的境界。由此可知,郭象所說的無待逍遙標舉的也是圣人經由心靈的超拔而獲得的精神境界和心靈自由狀態,此與莊子的逍遙精神遙相契合。以此而論,郭象所說的無待逍遙也同莊子一樣,屬于從“心”上言的境界形態。但郭象對此境界形態的逍遙也僅是如此一帶而過,并非其逍遙義的重點,其重點卻在于以“適性”言逍遙的實然形態。
三、眾生之“有待”逍遙
有待,在莊子看來正是由于眾生受限于外在客觀諸多條件的限制而不得超拔所造成,既依賴于外在的條件,則外在的條件一發生變化,自己也必隨之遷流,因此外在客觀條件的限制正是眾生獲得逍遙的障礙。究其根源,即在于蕓蕓眾生不具有自覺的自我修證工夫,不能向自己的“心”上用力,而永遠處于對待的關系網中,從而也就無法突破外在條件的限制而失去向上超拔的可能。郭象也承認眾生有待的客觀事實,但他卻反其意而用之,認為只要得到這些外在的條件即可獲得逍遙,即“茍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遙耳”。這是首先承認眾生獲得自由的可能,而此一可能之實現即是得其所待,而得其所待在郭象看來即是實現其各自的性分,他說:“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游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注:②③④郭象:《逍遙游注》,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第3、5、9、26頁。)郭象認為,莊子“逍遙游”的大意在于說明逍遙游放,無為而自得,這本不錯,也契合莊子逍遙的精神,但他卻隨即筆鋒一轉,又說莊子是通過大小的對比來說明逍遙在于各適其性,這明顯不符合莊子的原意,因為莊子是承認小大之辯的。郭象對于莊子所說的小大之辯卻皆從其各自的“性分”上加以泯除,認為大鵬上飛九萬里與小鳥飛往于榆枋之間,從其客觀的能力而言雖有所差異,但皆是其自性使然,就自適其性而言卻是一樣的,“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于適性一也”②,大鵬小鳥因各自適其性,故由此獲得的逍遙也是一樣的,“茍足于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于小鳥,小鳥無羨于天池,而榮愿有余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③。所謂大鵬與小鳥,在莊子的逍遙理論中僅是作為一種象征來比喻人類逍遙程度有高下的差異,郭象卻將此差異一并泯除在各自的性分之下,將適性與否確定為判定眾生逍遙與否的唯一標準,逍遙即是適性,只要適性即是逍遙。以此而論,則眾生若能實現其性分,則皆可歸于逍遙。郭象說:
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于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之行雖異,其于逍遙一也。④
依莊子之意,堯汲汲于世俗事務,是不逍遙的,而許由超脫于世外,不為世俗所羈,才是逍遙的。但郭象卻從自適其性立論,以為堯與許由的行為雖然不同,但都是其性分的實現,都是自得的,因此也都是逍遙的,此顯然與莊子不同。《莊子?刻意》中批評了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平世之士教誨之人游居學者、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以及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認為這幾類人皆不能“恬淡寂寞虛無無為”,不合“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但郭象卻對此注曰:“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此皆是就人的自然生命之所好而言逍遙,實不合莊子的原意。若以此為逍遙的進路,則人恣其性情的一切行為皆可稱為逍遙,實際上,郭象也確實對此給予了承認,他說:
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注:郭象:《齊物論注》,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第61頁。)
對于“成心”,在莊子是竭力批判、轉化的對象,也是人拘于小成不得逍遙的根源所在,對成心的批判轉化即直接與心齋、坐忘的修證工夫聯系在一起,也直接決定了自由只屬于有修養工夫的圣人和至人,蕓蕓眾生則因無自我修證的自覺而被排除在外。但郭象對成心卻在價值上給予了承認,以為各師其成心也會“付之而自當”,這就把自由的主體擴展為世俗中的一切個體,使人人皆有獲得自由的權利和可能,當然這就不免給一切世俗的價值賦予了高雅的色彩,實有價值下墮的危險。
在此還必須對郭象所論的有待逍遙與個體修證工夫的關系作一附帶的說明,雖然我們不能完全排除郭象所說的有待逍遙內在包含有個體主觀修證的內容,比如其所說的“安其所司”、“足于所受”、“靜其所遇”似乎也可作工夫論的理解,但考諸其對性分的論述,則知性分在郭象那里主要指個體自然稟賦的材質,不可變不可易,只是一種實然的狀態,而不具有價值的意義(注:如《逍遙游注》曰:“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跂尚之所及哉!”《齊物論注》曰:“言性各有分,……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養生主注》曰:“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外物注》曰:“性之所能,不得不為;性所不能,不得強為。”《秋水注》曰:“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跂。”同篇又曰:“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如此等等。)。故所謂實現其各自的性分即是安于其性分之所受,以此而實現的逍遙也就相應地成為一種實然可得的狀態。當然,對性分的實現可以通過自覺的修養以達到,但也可以在不自覺的狀態中達到,混冥狀態的對性分的順應也是性分的實現,郭象對此并未嚴格區分,即使含有修證的內容,則最終也必須下落于性分的客觀實現才可稱為逍遙;進而,如若再聯系其對“成心”價值的承認,則可知所謂性分的實現即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客觀實現,與人的主觀修養工夫并無必然的關聯,所謂“適性逍遙”也僅是就有待眾生之逍遙而言,并不包含至人的無待逍遙。由此筆者以為,若以有待眾生為主體,則郭象所說的有待逍遙并不需要主體的工夫實踐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即可實現,因此他說的有待逍遙更多地是一種從“性”上言的客觀實然形態,而非主觀的境界形態。
四、無待逍遙與有待逍遙之關系
郭象認為,至人之逍遙不僅僅是自通而已,而且還使有待眾生不失其所待,使之也同于大通,共得逍遙,也即眾生逍遙之獲得要得之于至人,他說:
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于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于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注:郭象:《逍遙游注》,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第20頁。)
此即表明至人之無待逍遙不僅僅限于一己自由之實現,而且有使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之功,也因此而使有待之眾生得其所待,同登大通逍遙之境。在郭象的語境中,至人之無待與眾生之有待的區別在客觀上是存在的,也是無法齊同的,即“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但從本質上言,圣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的逍遙與眾生各安其性天機自張的逍遙則是完全一樣的,即“至于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但郭象這里所說的至人使有待者不失其所待的方式具體是什么?是觀照的還是實然的?眾生由此而獲得的逍遙是圣人觀照式的還是實然客觀的?牟宗三先生直接以至人之觀照言“使不失其所待”,他說:“蕓蕓眾生雖不能自覺地作工夫,然以至人之去礙,而使之各適其性,天機自張,則亦即‘使不失其所待’,而同登逍遙之域矣。此即所謂‘不失,則同于大通矣’。‘同于大通’者,無論圣人之無待與蕓蕓眾生之有待,皆混化于道術之中也。此即圣人之功化。功化與觀照一也。在‘去礙’之下,功化即是觀照,觀照即是功化。”(注: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學生書局,1985年,第184頁。)以牟先生之意,圣人使眾生“不失其所待”僅是圣人觀照的結果,也即僅是眾生在圣人的觀照中呈現出逍遙的姿態,其實并非眾生實然逍遙的獲得。筆者以為,牟先生僅揭示出了問題的一個方面,除此之外,還有眾生逍遙實然獲得的另一方面。為此,必須對至人使有待之眾生不失其所待的方式進行具體分析。郭象說:
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忘其所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注:④郭象:《秋水注》,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第593、594頁。)
所謂天機之不可易,即是指事物自生之理及事物之性分天然不可改變,因此,至人對待眾生的做法是“捐聰明,棄知慮,魄然忘其所為而任其自動”,如此即可保持住事物的自性而實現萬物的逍遙。所謂“捐聰明”、“棄知慮”,即說明至人是通過主觀修養提升的工夫而與萬物冥合為一,所謂萬物的“任其自動”,皆是在至人之心的觀照下而呈現的藝術狀態和價值世界,此時,萬物的逍遙并不具有客觀的意義。就此而言,郭象確實能與莊子所表達的意思相契合。然郭象又說:
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群材之所為,使群材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逍遙矣。④
此是言圣人通過“無為”的方式“使群材各自得,萬物各自為”,所謂“恣其天機,無所與爭”,即是不以有為的方式牽曳萬物,而使其各安于自己的性分,此也即老子所說的“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三章)老子:《道德經》。之義,以此而使“群材各自得,萬物各自為”,使天下萬物性分自足各得逍遙。就此處之逍遙而言,則不能作為圣人之心觀照的結果來理解,而是圣人經由現實的“無為”政治使萬物的自性得到了客觀的實現,由此而實現的逍遙則是客觀實然狀態。“無為”是郭象在政治上的核心主張,并且在郭象那里,所謂“無為”即是具體可行的一種政治制度,而不僅僅是一種理論,因此,由“無為”所成就的萬物逍遙也必然具有客觀實在性。
五、對郭象逍遙義性質之判定
通過以上圣人無待逍遙與眾生有待逍遙之關系,我們可知,無待之圣人使眾生“不失其所待”的方式有兩種,一是以心靈觀照的方式泯除群異,而使有待之眾生得其所待而獲逍遙,此種逍遙僅呈現于至人的心靈境界中,與眾生的實際狀態并無關系,此與莊子實相一致;二是通過現實的“無為”政治使眾生得其所待,實現其各自的性分而獲得逍遙,此種逍遙是眾生實然客觀的獲得,就此而言,則實為莊子所無而為郭象所獨具。也正因為有此后面一義,使得圣人的無待逍遙在郭象的自由理論中為必不可少。但因郭象是將逍遙的重點落在現實的人身上,是為解決現實中人的自由問題而發,故其往往也以適性直稱逍遙,適性逍遙就成為其自由理論的核心內容,這恐怕是時人及后來學者對其逍遙義以“適性”相稱的原因,同時反而將其逍遙義中包含境界形態的圣人無待逍遙這一面遺落了,這實是對郭象逍遙義的一種誤解。
與此相關,對于郭象逍遙義的性質,亦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郭象的逍遙義屬于境界形態,皆是由主體之心觀照而來,如上述牟宗三先生所言;另一種看法則認為郭象的逍遙義屬于客觀的實然形態,如林聰舜先生認為,向、郭僅是通過玄學式的智解妙悟把握到了莊子的逍遙玄旨,但由于缺乏主體修證的工夫,最終則導致了價值意義與現象意義的混淆,他說:“向郭之適性說,當其就至人主觀心境所呈現之價值意義而言時,實能契合莊子之玄旨,其所謂之適性乃屬老莊式之境界形態。”但是,“向郭逍遙義于至人化境之把握,雖頗相應于莊子之原意,然化境之天機畢竟多宣說不得,若無主體工夫之撐持,則極易視為現成而流于光景之把捉。如是,圣人主觀心境所呈現之境界,即被誤認為客觀事實之存在。且向郭之把握逍遙游之境界義,既為由其解悟而來,而非得之于修證,則與其謂彼等真正契于圣人境界,毋寧謂彼等乃徒恃其智解妙悟,以求于俗世之行為中,抹上逍遙乘物之玄境。由是,向郭所把握之圣人主觀化境遂漸向客觀義而趨,價值意義與現象意義乃告混淆”林聰舜:《向郭莊學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第58頁。[ZW)]。筆者以為,對郭象之逍遙義,牟宗三先生的觀點只偏重于自境界方面言,且將眾生逍遙的實然性也一并歸于圣人逍遙的境界形態下,實有以莊子解郭象的傾向,并且無法統一于郭象對性分現實性所作的規定,也無法解釋郭象何以承認“成心”的價值。而林先生以向、郭對莊子逍遙義的把握無主體工夫的支撐、非得之于修證而造成了價值意義與現象意義的混淆,此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向、郭二人有無主體修證的工夫與其逍遙義表不表現為境界形態并無必然的聯系,前者是個人修養問題,后者是理論呈現問題,本不屬于同一層次,況且究竟向郭本人有無修證工夫也實不可考察;二是向、郭逍遙義呈不呈現為境界形態,應看其理論中有無工夫論,顯然在郭象的逍遙義中實內含著工夫論,如圣人之無待逍遙即是。由此即可以說其逍遙義可以表現為境界形態。林先生顯然是以前者立論,這本身即混淆了個人的修養實踐問題與其理論呈現問題之間的界限,且其觀點也內含著矛盾:既然向郭從圣人主觀心境所呈現之價值意把握了莊子的玄旨,則何以又會執境界形態為現象形態?因此,筆者以為,對郭象逍遙義的合理解釋只能是境界形態與實然形態二者并存,前者是言圣人無待逍遙,是對莊子本義的繼承,后者是言眾生有待逍遙,是對莊子本義的發展。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責任編輯:劉之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