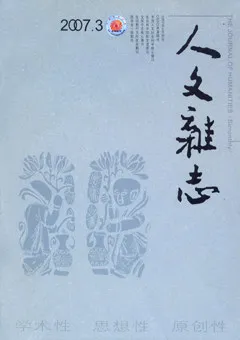革命話語(yǔ)與公共政策話語(yǔ):當(dāng)代中國(guó)公共政策話語(yǔ)變遷的歷史路徑
內(nèi)容提要 在革命歷史語(yǔ)境、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語(yǔ)境以及當(dāng)代中國(guó)社會(huì)利益關(guān)系變遷的現(xiàn)實(shí)語(yǔ)境這三重語(yǔ)境不同的結(jié)構(gòu)作用形勢(shì)下,以黨代會(huì)政治報(bào)告文本為代表的公共政策話語(yǔ),呈現(xiàn)出一種革命話語(yǔ)取向和公共政策話語(yǔ)取向交互存在的結(jié)構(gòu)化趨向,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出當(dāng)代中國(guó)特有的公共政策話語(yǔ)變遷的歷史路徑。
關(guān)鍵詞 革命話語(yǔ) 公共政策話語(yǔ) 當(dāng)代中國(guó) 歷史變遷路徑
〔中圖分類(lèi)號(hào)〕D6099〔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0447-662X(2007)03-0052-07
話語(yǔ)活動(dòng)是人類(lèi)社會(huì)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人們通過(guò)話語(yǔ)信息的發(fā)出、傳遞、理解和回應(yīng),進(jìn)行著彼此之間的交流和交往,話語(yǔ)是人類(lèi)社會(huì)在不同層面、不同領(lǐng)域和不同范圍形成人際整合的基本標(biāo)志。我們可以從話語(yǔ)活動(dòng)的角度對(duì)社會(huì)領(lǐng)域進(jìn)行系統(tǒng)式的劃分,認(rèn)為存在著一個(gè)關(guān)于公共政策活動(dòng)的話語(yǔ)領(lǐng)域或話語(yǔ)空間,即公共政策話語(yǔ)系統(tǒng),它包括作為語(yǔ)言符號(hào)的公共政策話語(yǔ)和圍繞著話語(yǔ)符號(hào)信息發(fā)出和傳播的公共政策話語(yǔ)的說(shuō)出、解釋乃至宣傳活動(dòng)。
本文在利益關(guān)系層面定義革命話語(yǔ)與公共政策話語(yǔ),把它們作為文本分析的理論框架或稱之為“理想型”,解讀從中共八大到十四大這七屆黨代會(huì)的政治報(bào)告文本,尋求揭示其中反映出來(lái)的公共政策話語(yǔ)變遷的歷史路徑,同時(shí),相對(duì)于革命話語(yǔ)而言,賦予公共政策話語(yǔ)以肯定的規(guī)范導(dǎo)向意義。
一、定義:革命話語(yǔ)與公共政策話語(yǔ)
革命話語(yǔ)反映的是一種不可調(diào)和的利益沖突關(guān)系,基本的利益關(guān)系主體即是革命一方和反革命的另一方,而且,他們之間的利益沖突關(guān)系往往是全方位的(指利益領(lǐng)域如政治、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革命話語(yǔ)就是由革命一方(通常是特定的代言人、代言群體或代言組織)發(fā)出的,關(guān)于自身利益整合,尋求獲取該利益目標(biāo),剝奪反革命一方利益占有的話語(yǔ)規(guī)劃。大體上看,革命話語(yǔ)有這樣幾個(gè)方面的特征:
其一是對(duì)象明確,反革命一方通常指控制公共權(quán)力(或政權(quán))的那些人,并以階級(jí)作為其群體標(biāo)識(shí),確定革命對(duì)象本身也就是對(duì)于革命一方的內(nèi)部整合,整合的標(biāo)準(zhǔn)通常就是與現(xiàn)政權(quán),確切地講是與現(xiàn)政權(quán)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之間的利益關(guān)系性質(zhì)。對(duì)于革命一方來(lái)說(shuō),這種整合方式有著濃厚的政治動(dòng)員色彩,但就革命勝利將意味著政權(quán)的占有這一點(diǎn)而言,它又可以被看作是民主機(jī)制的原初形式,或可看作后來(lái)民主化建設(shè)的合法性基礎(chǔ)。
其二是利益關(guān)聯(lián)領(lǐng)域的普遍性,這其中可能隱含著一個(gè)不同領(lǐng)域利益占有狀況呈正相關(guān)趨向的基本假設(shè)。因此,從利益的獲取(或剝奪)角度看,革命話語(yǔ)又是一種整體性的話語(yǔ)規(guī)劃,它指向革命方與反革命方之間利益關(guān)系地位的全面顛覆。某種程度上,正是因?yàn)槠湔w性特征,革命話語(yǔ)大都包含有大量的意識(shí)形態(tài)話語(yǔ)內(nèi)容。作為一種權(quán)威性的價(jià)值觀念信仰或價(jià)值觀念體系,意識(shí)形態(tài)在這一整體性的話語(yǔ)架構(gòu)中發(fā)揮著異常重要的語(yǔ)境整合功能,其整合功能體現(xiàn)在整體性的各個(gè)層面,如利益的存在狀態(tài)、利益的歸屬領(lǐng)域、利益主體的群體歸屬劃分以及利益關(guān)系的性質(zhì)等等。意識(shí)形態(tài)話語(yǔ)的另一面,即是革命話語(yǔ)的意識(shí)形態(tài)合法性,或者說(shuō),意識(shí)形態(tài)內(nèi)容總是代表著話語(yǔ)規(guī)劃的合法性要求。
其三是革命話語(yǔ)中對(duì)于利益獲取(或剝奪)手段的激烈性,往往有著明確的暴力對(duì)抗取向。革命話語(yǔ)的利益后果對(duì)于反革命一方具有根本性的顛覆,它們不可能輕易退出自己優(yōu)越的利益關(guān)系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既定的利益關(guān)系形勢(shì)下,反革命一方往往擁有著壓倒性的行為資本或行為能力,表現(xiàn)在制度、組織以及實(shí)際利益占有等多個(gè)層面。因此,在制度、組織固有的穩(wěn)定性慣性以及利益固有的自我維護(hù)面前,顯然很難設(shè)想所謂溫和的革命方式。
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成立以后,經(jīng)由其整合并說(shuō)出的革命話語(yǔ),在當(dāng)代中國(guó)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乃至社會(huì)主義革命中發(fā)揮著至關(guān)重要的集體(或階級(jí)群體)整合以及集體行動(dòng)規(guī)劃作用,促成這一系列革命話語(yǔ)說(shuō)出的一個(gè)重要的語(yǔ)境來(lái)源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也是促成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組織建立的一個(gè)基本的組織整合工具和組織建設(shè)原則,是其組織意識(shí)話語(yǔ)最重要的語(yǔ)境來(lái)源,某種意義上,可以說(shuō)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當(dāng)代中國(guó)的組織載體(考慮到馬克思主義強(qiáng)烈的改造現(xiàn)實(shí)取向)和組織代言人。經(jīng)由革命話語(yǔ)的構(gòu)成特征以及革命話語(yǔ)說(shuō)出的歷史經(jīng)歷,馬克思主義成為了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組織話語(yǔ)說(shuō)出的一個(gè)內(nèi)在的合法性傳統(tǒng),這一合法性傳統(tǒng)自然延伸到黨組織在革命勝利后,代表著公共權(quán)力的公共政策話語(yǔ)說(shuō)出。八大政治報(bào)告文本就是黨組織指向國(guó)家范圍的第一次系統(tǒng)的公共政策話語(yǔ)說(shuō)出。
對(duì)應(yīng)于革命話語(yǔ)的上述特點(diǎn),公共政策話語(yǔ)有這樣幾個(gè)方面的不同之處:
首先,在對(duì)象上,雖然都是關(guān)于特定集體(或群體)行動(dòng)的規(guī)劃,但革命對(duì)象強(qiáng)調(diào)其在革命集體(或革命群體)之外,而政策對(duì)象則指向集體(或群體)內(nèi)部(即使是指向國(guó)家間關(guān)系的外交政策,也以規(guī)劃自身行為為基本內(nèi)容),這就是公共政策話語(yǔ)最為基本的利益關(guān)系協(xié)調(diào)功能。公共政策話語(yǔ)往往指向集體(或群體)內(nèi)特定的人員或人員群體,從這里生出公共政策話語(yǔ)固有的相對(duì)于個(gè)體利益、群體利益或組織利益、集體利益的公益取向。在自然生成的意義上,公益來(lái)自于眾多個(gè)體利益、群體利益的內(nèi)部整合,公共政策話語(yǔ)就是這一整合的話語(yǔ)呈示,公益的優(yōu)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公共政策話語(yǔ)的強(qiáng)制性內(nèi)涵。基于公共政策話語(yǔ)固有的制度話語(yǔ)地位,公益的整合往往經(jīng)由穩(wěn)定的制度、組織和儀式程序,但是,穩(wěn)定的公共權(quán)力有著自我維護(hù)甚至擴(kuò)大化的本能,常常會(huì)強(qiáng)化其話語(yǔ)的強(qiáng)制性意義,相對(duì)于革命話語(yǔ)政治動(dòng)員式的民主意味而言,公共政策話語(yǔ)或者說(shuō)公共權(quán)力代言公益本身,還是會(huì)滋生一些事關(guān)代表性或利益整合的民主問(wèn)題。
其次,在利益關(guān)聯(lián)領(lǐng)域?qū)用妫舱咴捳Z(yǔ)的利益調(diào)節(jié)極少指向集體成員整體性的利益占有。集體(或國(guó)家)內(nèi)有不同的利益群體或利益階層,不同的利益主體又有著多重的利益取向,因此,集體(國(guó)家)內(nèi)的利益關(guān)系狀況往往表現(xiàn)為以不同利益群體或利益階層為關(guān)節(jié)點(diǎn)的一個(gè)多維的利益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而且利益關(guān)系性質(zhì)又各有不同(比如,即使考慮到公共資源有限所帶來(lái)的機(jī)會(huì)成本問(wèn)題,也可能存在不同利益關(guān)系線路之間的并列不相關(guān)等等),公共政策話語(yǔ)所要調(diào)節(jié)的,通常只是其中的某些線路,它們并不必然有著內(nèi)在的利益關(guān)聯(lián),而且,相對(duì)于革命話語(yǔ)可經(jīng)由明確對(duì)象的內(nèi)部整合方式,公共政策話語(yǔ)的內(nèi)部整合功能卻主要表現(xiàn)在,通過(guò)對(duì)不同利益主體,多重利益獲取狀況的調(diào)節(jié),使集體(國(guó)家)范圍內(nèi)不要出現(xiàn)“革命”的一方。因此,相對(duì)于革命話語(yǔ)的對(duì)象明確性,公共政策話語(yǔ)更強(qiáng)調(diào)其利益取向,確切地說(shuō)是利益關(guān)系取向性。利益關(guān)系內(nèi)容的紛繁復(fù)雜,一方面使得公共政策話語(yǔ)很難做出整體性的話語(yǔ)規(guī)劃,這是其意識(shí)形態(tài)淡化的基本理由;另一方面,不再附隨于特定主體的利益的各種物化、儀式化以及制度化載體形式,又為多門(mén)科學(xué)理論話語(yǔ)進(jìn)入公共政策話語(yǔ)的語(yǔ)境背景提供了條件,所以,相對(duì)于革命話語(yǔ)的合法性取向,公共政策話語(yǔ)又可能有著較為突出的科學(xué)性合理性取向,這可能進(jìn)一步推動(dòng)其意識(shí)形態(tài)色彩的淡化。
最后,在公共政策話語(yǔ)中,利益獲取手段主要表現(xiàn)為利益關(guān)系的調(diào)節(jié)上,基于利益關(guān)系的不同性質(zhì),公共政策的調(diào)節(jié)手段也具有多樣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人際關(guān)系的協(xié)調(diào),并通過(guò)人際關(guān)系協(xié)調(diào)來(lái)推動(dòng)集體(國(guó)家)內(nèi)部的整合,乃至集體成員對(duì)于集體以及經(jīng)由公益話語(yǔ)說(shuō)出代表集體的公共權(quán)力的歸屬感。因此,相對(duì)于革命話語(yǔ)激烈的零和博弈取向,公共政策話語(yǔ)的調(diào)節(jié)更強(qiáng)調(diào)正和共贏的行為互動(dòng)模式。在這里,利益的得失問(wèn)題不再是簡(jiǎn)單的強(qiáng)取與剝奪,它涉及到更多,也更為具體化的利益交易問(wèn)題,利益交易不僅是多邊主體的,而且相關(guān)主體的涉入利益也可能是多重的,因此,關(guān)于部分利益的補(bǔ)償、退讓、交換等等往往是公共政策話語(yǔ)主要的調(diào)節(jié)手段。公共政策話語(yǔ)又直接表現(xiàn)為公共權(quán)力的話語(yǔ)說(shuō)出。公共政策話語(yǔ)的這種雙重產(chǎn)生機(jī)制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狀況其實(shí)就反映可特定國(guó)家的公共管理機(jī)制,正是在不同的公共管理機(jī)制下,公共政策話語(yǔ)調(diào)節(jié)分別展示出其特有的民主取向、權(quán)力取向或科學(xué)性取向。
二、分析對(duì)象
本文選取八——十四大政治報(bào)告(下文中分別簡(jiǎn)稱為《政治報(bào)告》如《十一大政治報(bào)告》)作為文本分析的對(duì)象,理由主要在于以下兩個(gè)方面:
其一,《政治報(bào)告》是當(dāng)代中國(guó)政治體制下公共政策的代表性文本。
(A)共產(chǎn)黨是國(guó)家政治權(quán)力的中心,而《政治報(bào)告》乃是由共產(chǎn)黨組織內(nèi)部的領(lǐng)導(dǎo)核心——中央常委會(huì)制定,其公共性、規(guī)范性和強(qiáng)制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B)五年一次(正常情況下)的《政治報(bào)告》對(duì)國(guó)家范圍內(nèi)重大的利益關(guān)系事件、事態(tài)進(jìn)行解釋和安排,有著明顯的計(jì)劃性和公共意義;
(C)共產(chǎn)黨有著強(qiáng)大的社會(huì)代表性,共產(chǎn)黨組織對(duì)國(guó)家范圍內(nèi)重大事件、事態(tài)的應(yīng)對(duì)建立在廣泛的群眾基礎(chǔ)之上,《政治報(bào)告》的社會(huì)認(rèn)同性也毋庸置疑;
(D)歷次《政治報(bào)告》都會(huì)通過(guò)文件、大眾媒體等等途徑向社會(huì)公示,公開(kāi)性是理解性的基礎(chǔ)。
其二,《政治報(bào)告》的產(chǎn)出與變遷,能夠代表當(dāng)代中國(guó)宏觀意義上的公共政策變遷過(guò)程。
(A)基于共產(chǎn)黨組織在國(guó)家政治生活中穩(wěn)定的領(lǐng)導(dǎo)地位以及全國(guó)代表大會(huì)召開(kāi)的周期性,《政治報(bào)告》具有歷史的穩(wěn)定性和延續(xù)性,有著巨大的政策信息含量,幾乎涵蓋了這一時(shí)期所有重大的公共政策主題,同時(shí),也反映了歷史的變遷。
(B)《政治報(bào)告》的現(xiàn)實(shí)化過(guò)程,往往就是其文本沿著政府組織的權(quán)力等級(jí),由高向低地傳播,傳播也即是對(duì)《政治報(bào)告》進(jìn)行解釋、宣傳和執(zhí)行等一系列的具體化過(guò)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現(xiàn)實(shí)的公共政策過(guò)程相一致的。
三、兩個(gè)重要概念
元政策話語(yǔ):元政策話語(yǔ)處于公共政策話語(yǔ)活動(dòng)等級(jí)的頂層,經(jīng)常充當(dāng)特定公共政策話語(yǔ)系統(tǒng)的主題標(biāo)識(shí),對(duì)于系統(tǒng)內(nèi)的政策話語(yǔ)說(shuō)出,發(fā)揮著規(guī)范性的語(yǔ)境制約功能。從最高公共權(quán)力只能以同一個(gè)聲音說(shuō)話的角度看,特定時(shí)期的元政策話語(yǔ)也應(yīng)當(dāng)是唯一的。“唯一”主要是指主題取向(利益關(guān)系狀況的認(rèn)知取向和規(guī)劃取向)上的同一或一致,并不強(qiáng)調(diào)話語(yǔ)文本上的單一。在話語(yǔ)文本層面,正如我們?cè)谇懊娴挠懻撝幸呀?jīng)指出的,元政策話語(yǔ)往往表現(xiàn)為多層次的構(gòu)成特征,比如在十一大政治報(bào)告文本中所揭示出來(lái)的“階級(jí)斗爭(zhēng)”、“文化大革命”與“反對(duì)四人幫”。因此,在話語(yǔ)產(chǎn)出的意義上,特定的公共政策話語(yǔ)通常可以被看作是,在多重的語(yǔ)境制約背景下,關(guān)于特定元政策話語(yǔ)主題的具體化說(shuō)出,與元政策話語(yǔ)的縱向?qū)哟涡詷?gòu)成不同,語(yǔ)境因素主題處于一種橫向的并列(或交叉)結(jié)構(gòu)狀態(tài)。不過(guò),這里并不排除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特定的話語(yǔ)信息有著元政策話語(yǔ)和政策話語(yǔ)語(yǔ)境的雙重角色地位,比如在九大、十大以及十一大政治報(bào)告文本中的“毛主席語(yǔ)”。
語(yǔ)境:語(yǔ)境是指公共政策文本形成的外在制約條件。與元政策話語(yǔ)的縱向?qū)哟涡詷?gòu)成不同,語(yǔ)境因素主題處于一種橫向的并列(或交叉)結(jié)構(gòu)狀態(tài)。在話語(yǔ)產(chǎn)出的意義上,特定的公共政策話語(yǔ)通常可以被看作是,在多重的語(yǔ)境制約背景下,關(guān)于特定元政策話語(yǔ)主題的具體化說(shuō)出。
四、文本分析:中共八大——十四大政治報(bào)告
在八大政治報(bào)告文本中,處于最高元政策話語(yǔ)地位的是那句關(guān)于“總路線”的語(yǔ)句表述:“在一個(gè)相當(dāng)長(zhǎng)的時(shí)間內(nèi),逐步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主義的工業(yè)化,逐步完成對(duì)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huì)主義改造。”其基本的語(yǔ)境前提乃是語(yǔ)句“過(guò)渡時(shí)期的基本特點(diǎn)”。在語(yǔ)義關(guān)聯(lián)的意義上,圍繞元政策話語(yǔ)的文本表述主要集中在前三個(gè)主題語(yǔ)段,即“過(guò)渡時(shí)期的總路線”、“社會(huì)主義改造”和“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而后面三個(gè)主題語(yǔ)段“國(guó)家的政治生活”、“國(guó)際關(guān)系”和“黨的領(lǐng)導(dǎo)”則顯示出相對(duì)的獨(dú)立性趨向。從字面上看,前三個(gè)主題指向國(guó)家的經(jīng)濟(jì)利益領(lǐng)域,后三個(gè)主題則集中于政治利益領(lǐng)域,但是正像我們?cè)谇懊娴姆治鲋兄赋龅模?jīng)過(guò)社會(huì)主義改造后形成的企業(yè)組織形式,對(duì)組織的個(gè)體利益有著全面的(指涵蓋取政治利益、經(jīng)濟(jì)利益和社會(huì)利益)承載或決定功能,更重要的是,由于企業(yè)組織可以被納入公共權(quán)力的運(yùn)行等級(jí),本身就發(fā)揮著政治主體、政策主體的公共治理功能,當(dāng)然,也是“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政策話語(yǔ)現(xiàn)實(shí)化過(guò)程中主要的依托主體。因此,又可以說(shuō),對(duì)于后面三個(gè)主題語(yǔ)段而言,“社會(huì)主義改造”主題語(yǔ)段,確切地說(shuō)關(guān)于“總路線”的元政策話語(yǔ)表述有著整體性的政策關(guān)聯(lián)意義,把它們聯(lián)結(jié)到一起的,乃是關(guān)于“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的語(yǔ)義展開(kāi),它們分別可以被看作是“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的經(jīng)濟(jì)建設(shè)內(nèi)涵、政治建設(shè)內(nèi)涵、國(guó)際關(guān)系內(nèi)涵以及共產(chǎn)黨組織建設(shè)內(nèi)涵,因此可以說(shuō),“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就是八大政治報(bào)告文本的一個(gè)最重要的關(guān)鍵詞,作為建國(guó)后黨的第一屆全國(guó)代表大會(huì)的政治報(bào)告文本,這一關(guān)于“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的系統(tǒng)的話語(yǔ)表述,標(biāo)志著共產(chǎn)黨組織關(guān)于集體行動(dòng)的話語(yǔ)規(guī)劃,已經(jīng)由革命話語(yǔ)形式轉(zhuǎn)換成為公共政策話語(yǔ)形式。
八大特殊的時(shí)段位置意味著由此發(fā)出的政治報(bào)告文本具有革命話語(yǔ)和公共政策話語(yǔ)的雙重性質(zhì)。一方面,黨組織在公共權(quán)力中的地位決定了政治報(bào)告文本基本的公共政策話語(yǔ)屬性;另一方面,基于黨組織沿自革命時(shí)期的合法性傳統(tǒng)以及組織模式的慣性等因素,文本表述中仍有著大量的革命話語(yǔ)形式與內(nèi)容。
“總路線”的元政策話語(yǔ)地位標(biāo)志著八大政治報(bào)告文本中居主導(dǎo)地位的經(jīng)濟(jì)利益取向,雖然經(jīng)由社會(huì)主義改造的組織化整合,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個(gè)頗具整體性關(guān)聯(lián)的利益歸屬主體現(xiàn)象,但是總體上看,這些“單位人”的利益占有本身并不是直接的改造對(duì)象,被改造的主要是他們?cè)趪?guó)家范圍內(nèi)利益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位置,使得個(gè)體利益、組織(群體)利益以及國(guó)家利益(公益)在其獲取活動(dòng)中建立高度的正向相關(guān),并統(tǒng)一于公共權(quán)力的話語(yǔ)規(guī)劃即公共政策話語(yǔ)之中。因此,社會(huì)主義改造也是“五年計(jì)劃”得以展開(kāi)的一個(gè)非常重要的組織化條件。在這里,上述三個(gè)方面利益的關(guān)聯(lián)性整體雖然也有著某種程度的革命話語(yǔ)意味,但是由以生成的關(guān)聯(lián)性整體并不具有相對(duì)立的另一方(至少在國(guó)家范圍內(nèi)),關(guān)于這一系列利益目標(biāo)的獲取活動(dòng)也就不再具有相對(duì)的利益剝奪意義。“五年計(jì)劃”中,不同的利益目標(biāo)、眾多的利益主體之間甚至不存在公開(kāi)的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在國(guó)家計(jì)劃的全盤(pán)安排下,它們分別充當(dāng)國(guó)家利益在不同層面、不同領(lǐng)域內(nèi)的子目標(biāo)。如果說(shuō)以“五年計(jì)劃”為標(biāo)識(shí)的公共政策話語(yǔ)具有整體性意味,那么,這種整體性很大程度上就體現(xiàn)在把它們連接到一起去的“全盤(pán)安排”上,以及經(jīng)由它們量上的累加所形成的計(jì)劃目標(biāo)即“五年計(jì)劃的基本任務(wù)”。
在八大政治報(bào)告文本中,集中反映其革命話語(yǔ)色彩的是在“國(guó)際關(guān)系”主題語(yǔ)段,以“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作為群體整合工具,尋求在二分(指資本主義與社會(huì)主義相敵對(duì))的國(guó)際關(guān)系形勢(shì)下確立自身的國(guó)家群體歸屬地位,中國(guó)革命的歷史經(jīng)歷以及馬克思主義話語(yǔ)的合法性延續(xù)都使得這種群體歸屬取向具有特定的革命話語(yǔ)色彩。不過(guò),群體利益的存在狀態(tài)(正如前文指出的,主要存在于觀念層面,表現(xiàn)為輿論上的支持等等)以及關(guān)于和平共處五項(xiàng)原則的表述又在某種程度上削減了這種革命話語(yǔ)色彩。
“階級(jí)斗爭(zhēng)”和“文化大革命”是統(tǒng)攝九大、十大和十一大這三屆政治報(bào)告文本的元政策話語(yǔ),單從字面便足以斷言它們強(qiáng)烈的革命話語(yǔ)取向,來(lái)自于公共權(quán)力的革命話語(yǔ)說(shuō)出的兩個(gè)重要特征:其一,話語(yǔ)本身不容挑戰(zhàn)的公共權(quán)威地位,意味著其對(duì)象制約取向上濃厚的強(qiáng)制性色彩,這與革命話語(yǔ)“敵我”關(guān)系二分式的必然性斷言密切相關(guān),從“敵我”不可調(diào)和的利益沖突關(guān)系角度看,“必然性”斷言主要表現(xiàn)在四個(gè)層面即(A)利益歸屬劃分上的非敵即我;(B)價(jià)值判定上的我方全部肯定,敵方全部否定;(C)利益尋求上的我方獲取,敵方剝奪;(D)利益得失后果上的我方必得,敵方必失。貫穿這一系列必然性斷言邏輯的乃是話語(yǔ)意義的現(xiàn)實(shí)化取向。其二,話語(yǔ)效力實(shí)現(xiàn)方式上的符號(hào)化趨向,顯示出話語(yǔ)表述的利益關(guān)系狀況與現(xiàn)實(shí)中真實(shí)的利益關(guān)系狀況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此時(shí),話語(yǔ)本身固有的強(qiáng)制性將從另一側(cè)面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其主觀性的規(guī)范構(gòu)建意義。但是,國(guó)家公共管理活動(dòng)必須面對(duì)的基本職能、相關(guān)主體的利益自我維護(hù)本能以及其他既有制度規(guī)范(如社會(huì)風(fēng)俗、社會(huì)慣例等等)的交叉制約等因素又將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話語(yǔ)效力的主觀性向度,在這種情況下,對(duì)于相關(guān)主體而言,話語(yǔ)規(guī)范所包含的利益關(guān)聯(lián)往往更多地存在于利益得失感相對(duì)薄弱的觀念層面,而話語(yǔ)外在行為制約效力的實(shí)現(xiàn),則主要表現(xiàn)在能夠反映觀念認(rèn)同(乃至遵從)與否的話語(yǔ)行為上,比如張貼的相關(guān)政策話語(yǔ)內(nèi)容的宣傳標(biāo)語(yǔ)、會(huì)議上的口頭表態(tài)、圍繞著政策話語(yǔ)內(nèi)容的學(xué)習(xí)討論等等都可以看作這方面的政策話語(yǔ)現(xiàn)象。
高強(qiáng)制性和符號(hào)化取向這一公共政策話語(yǔ)活動(dòng)的雙重特征,主要表現(xiàn)為這一時(shí)期盛行的“運(yùn)動(dòng)”式的政策運(yùn)行現(xiàn)象。一方面,一旦公共權(quán)力頂層做出元政策話語(yǔ)性質(zhì)的話語(yǔ)說(shuō)出,基于革命話語(yǔ)取向固有的強(qiáng)制性壓力,話語(yǔ)信息就會(huì)在社會(huì)中迅速傳播,并形成廣泛的遵從性政策回應(yīng)形勢(shì),這就是所謂“扁平”狀的公共政策話語(yǔ)傳播機(jī)制。另一方面,由于話語(yǔ)說(shuō)出行為的低成本以及話語(yǔ)符號(hào)本身的彈性解釋特征等因素,使得指向觀念層面利益制約的元政策話語(yǔ)(指處于“階級(jí)斗爭(zhēng)”、“文化大革命”制約等級(jí)下的元政策話語(yǔ))說(shuō)出活動(dòng)變得較為頻繁的同時(shí),也可能意味著政策話語(yǔ)制約取向(即使只處于觀念層面)上的不明確(如政策對(duì)象現(xiàn)實(shí)利益取向上的不明確)。因?yàn)楫?dāng)本來(lái)以穩(wěn)定性為基本特征的元政策話語(yǔ)趨向于多變的時(shí)候,其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利益關(guān)系狀況的指涉功能也就發(fā)生可變化,成為了以話語(yǔ)為標(biāo)準(zhǔn),根據(jù)話語(yǔ)到現(xiàn)實(shí)中尋找乃至構(gòu)建話語(yǔ)中設(shè)定的利益關(guān)系狀況(包括如政策對(duì)象或批斗對(duì)象等內(nèi)容)的局面。
顯然,無(wú)論是“扁平”狀的公共政策話語(yǔ)傳播機(jī)制,還是根據(jù)元政策話語(yǔ)尋找政策對(duì)象的公共政策話語(yǔ)制約機(jī)制,從制度運(yùn)行角度看,它們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原本應(yīng)當(dāng)作為制度落實(shí)行動(dòng)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的組織因素。盡管在尋找政策對(duì)象以及元政策話語(yǔ)傳播中可能經(jīng)由不同政府組織層級(jí)這一中間環(huán)節(jié),但是對(duì)于元政策話語(yǔ)的最終傳播及其實(shí)現(xiàn)既定的制約效果(主要是話語(yǔ)層面的遵從)而言,各級(jí)政府在其中發(fā)揮的作用似乎并不是關(guān)鍵性的,更不用說(shuō)革命話語(yǔ)中的顛覆權(quán)力取向還會(huì)導(dǎo)向沖擊政府的政策回應(yīng)行為了。因此,低組織化水平可以看作是“運(yùn)動(dòng)”式公共政策話語(yǔ)運(yùn)行機(jī)制的又一個(gè)形式化特征。
組織依托于特定人員、機(jī)構(gòu)乃至物資載體,組織化水平是制度化水平的一項(xiàng)基本指標(biāo),公共組織承擔(dān)著公共資源的直接使用權(quán)力,在很多情況下都代表了制度落實(shí)活動(dòng)中穩(wěn)定的合理性計(jì)劃內(nèi)容,所以,公共組織的非關(guān)鍵地位又顯示出革命話語(yǔ)中固有的合法化趨向在這一時(shí)期公共政策話語(yǔ)活動(dòng)中的主導(dǎo)性地位。
在十四大政治報(bào)告文本中,用“十四年”把這三屆黨代會(huì)概括進(jìn)同一的公共政策話語(yǔ)系統(tǒng)之中,其元政策話語(yǔ)的主題標(biāo)識(shí)——“改革開(kāi)放”顯然有著明確的行動(dòng)語(yǔ)義內(nèi)涵。八大政治報(bào)告文本中的“總路線”以及九大、十大、十一大政治報(bào)告文本中的“階級(jí)斗爭(zhēng)”、“文化大革命”中階級(jí)理論內(nèi)容為其行動(dòng)規(guī)劃添加了太多的理論描述內(nèi)容,因此,總體上看,即使有各個(gè)主題語(yǔ)段的進(jìn)一步展開(kāi),它們?nèi)匀狈?duì)于特定行為方式或行為取向的具體化制約,前者集中于子目標(biāo)的設(shè)定,而后者則執(zhí)著于合法化的轉(zhuǎn)引或論證。
從元政策話語(yǔ)角度看,“改革開(kāi)放”有著雙重的語(yǔ)境制約形式。一方面,它明確指向特定的行為方式本身,可以說(shuō)“改革行為”或“開(kāi)放行為”;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抽象性質(zhì),不像“總路線”和“文化大革命”那樣有著鮮明的公益或革命利益取向。在后一方面的意義上,“改革開(kāi)放”最初僅是一個(gè)相對(duì)性的行為取向選擇,其相對(duì)性的語(yǔ)境即是在“階級(jí)斗爭(zhēng)”、“文化大革命”元政策話語(yǔ)下形成的既定的利益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乃至其制度化形式。如果說(shuō)“開(kāi)放”尚有一定的利益取向性質(zhì)——尋求與他國(guó)(或地區(qū))建立特定利益關(guān)系的行為取向,那么,“改革”則有著與革命相似的形式化特征,反映的是對(duì)現(xiàn)有利益關(guān)系狀況的變革。但是對(duì)于公共政策話語(yǔ)而言,最重要的是為解決特定利益關(guān)系狀況的構(gòu)建或引導(dǎo)問(wèn)題,即建設(shè)問(wèn)題,在“改革”的形式話語(yǔ)下,它在十四大政治報(bào)告文本中被明確、系統(tǒng)地提出,但僅就政治報(bào)告文本來(lái)看,其基本內(nèi)容則是自十二大、十三大以來(lái)逐漸形成的,具有事后總結(jié)性質(zhì)。
對(duì)于這一時(shí)期的公共政策話語(yǔ)系統(tǒng)而言,元政策話語(yǔ)的這種事后總結(jié)性質(zhì)意味著兩個(gè)密切相關(guān)的話語(yǔ)說(shuō)出取向。其一是開(kāi)放性,指話語(yǔ)說(shuō)出受到較少的利益觀念限制,尤其是根植于“階級(jí)斗爭(zhēng)”、“文化大革命”元政策話語(yǔ)中的意識(shí)形態(tài)限制,更多地反映到特定主體特殊的利益欲求和實(shí)際占有層面;其二是非整體性,不僅表現(xiàn)為話語(yǔ)說(shuō)出缺乏系統(tǒng)的意識(shí)形態(tài)觀念的嚴(yán)格限制,更重要的是各利益歸屬領(lǐng)域的話語(yǔ)規(guī)劃呈現(xiàn)出一種逐漸的分化趨向,即相對(duì)于政治掛帥的分化趨向。當(dāng)然,這一非整體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反映的是一種長(zhǎng)期的發(fā)展過(guò)程,我們看到,最初其實(shí)在很大程度上表現(xiàn)為近似于整體性的替代,即以“經(jīng)濟(jì)中心”取代政治掛帥。但是“經(jīng)濟(jì)中心”只表示經(jīng)濟(jì)利益取向在多重利益取向中突出的政策話語(yǔ)選擇地位,并不代表經(jīng)濟(jì)利益取向可以涵蓋其他的利益取向。在具體的文本表述上,表現(xiàn)為經(jīng)濟(jì)利益取向主題占據(jù)了大量的文本內(nèi)容,但并不排斥關(guān)于其他利益取向又有著并列的主題表述。(盡管有那么一段時(shí)期,在現(xiàn)實(shí)的公共政策話語(yǔ)活動(dòng)中,出現(xiàn)了用經(jīng)濟(jì)成就統(tǒng)帥其他利益成果的矯枉過(guò)正現(xiàn)象。)而且,經(jīng)濟(jì)利益取向本身特有的合理化標(biāo)準(zhǔn)也使得“經(jīng)濟(jì)中心”帶有了內(nèi)在的具體化趨向。其實(shí),從十二大政治報(bào)告文本,到十三大、十四大政治報(bào)告文本,其中交織的就是一條“經(jīng)濟(jì)中心”取代政治掛帥的話語(yǔ)變遷邏輯,一個(gè)重要的標(biāo)志就是由計(jì)劃經(jīng)濟(jì)、有計(jì)劃的商品經(jīng)濟(jì),再到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語(yǔ)詞轉(zhuǎn)換。十四大政治報(bào)告文本中關(guān)于十四年公共政策活動(dòng)成果的總結(jié)在很大程度上就標(biāo)志著經(jīng)濟(jì)中心整體性話語(yǔ)地位的全面確立,而這又將意味著非整體化的全面展開(kāi)。
但是,作為由公共權(quán)力發(fā)出的權(quán)威性話語(yǔ),公共政策話語(yǔ)(尤其是處于元政策話語(yǔ)地位的公共政策話語(yǔ))無(wú)法回避政治合法性問(wèn)題,尤其是考慮到其有著長(zhǎng)期的革命話語(yǔ)傳統(tǒng),它必須要提出話語(yǔ)的合法性基礎(chǔ),或者說(shuō),做出某種合法化論證。就特定的公共政策話語(yǔ)說(shuō)出而言,合法性關(guān)聯(lián)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gè)層面,一是現(xiàn)實(shí)層面,指向民主機(jī)制的兩端,即話語(yǔ)說(shuō)出的公共權(quán)力合法性以及反映的人民利益需求的公益合法性,在政治報(bào)告文本中分別由關(guān)于“四項(xiàng)基本原則”的話語(yǔ)表述和人民生活水平來(lái)指示;二是傳統(tǒng)層面,指向話語(yǔ)說(shuō)出的語(yǔ)境連續(xù)性,具有一定的意識(shí)形態(tài)色彩,我們看到,經(jīng)由“建設(shè)有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理論”,“改革開(kāi)放”已經(jīng)具有了馬克思主義的合法性語(yǔ)境基礎(chǔ)。
五、結(jié)語(yǔ)
綜上,參照革命話語(yǔ)和公共政策話語(yǔ)這兩個(gè)理論模型,我們就可以把從八大到十四大的政策話語(yǔ)變遷歷史,進(jìn)一步劃分成三個(gè)階段或者三個(gè)大的公共政策話語(yǔ)系統(tǒng):其一,八大階段,指從八大政治報(bào)告文本說(shuō)出到九大政治報(bào)告文本說(shuō)出這一時(shí)間段,公共政策話語(yǔ)的主導(dǎo)性逐漸確立,但仍有著較為明顯的革命話語(yǔ)取向,具有系統(tǒng)標(biāo)識(shí)地位的元政策話語(yǔ)是“過(guò)渡時(shí)期的總路線”;其二,九大、十大、十一大階段,指從九大政治報(bào)告到十一屆三中全會(huì)(注:十一屆三中全會(huì)在當(dāng)代中國(guó)公共政策變遷歷史中占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囿于本文以各次黨代會(huì)政治報(bào)告文本作為解讀對(duì)象,所以這里僅根據(jù)十二大、十三大以及十四大中關(guān)于十一屆三中全會(huì)的評(píng)價(jià),把它作為一個(gè)重要的劃分關(guān)節(jié)點(diǎn),而不對(duì)其具體的政策話語(yǔ)產(chǎn)出做進(jìn)一步分析。)這一時(shí)間段,這是公共政策話語(yǔ)取向式微,革命話語(yǔ)取向突顯其主導(dǎo)性的時(shí)期,具有系統(tǒng)標(biāo)識(shí)地位的元政策話語(yǔ)是“文化大革命”和“階級(jí)斗爭(zhēng)”;其三,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時(shí)期,指從十一屆三中全會(huì)到十五大政治報(bào)告說(shuō)出這一時(shí)間段,這是公共政策話語(yǔ)主導(dǎo)性地位再次逐漸形成,革命話語(yǔ)式微的時(shí)期,具有系統(tǒng)標(biāo)識(shí)地位的元政策話語(yǔ)是“改革開(kāi)放”。
把這個(gè)階段納入同一的公共政策變遷過(guò)程的語(yǔ)境背景是革命斗爭(zhēng)的歷史語(yǔ)境、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語(yǔ)境以及當(dāng)代中國(guó)社會(huì)利益關(guān)系變遷的現(xiàn)實(shí)語(yǔ)境,只是在不同階段,這三重語(yǔ)境所發(fā)揮的制約作用地位有所不同。
在八大階段,這三重語(yǔ)境因素占有著大體相當(dāng)?shù)闹萍s作用地位,代表性的主題語(yǔ)段分別是“國(guó)際關(guān)系”、“社會(huì)主義改造”和“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在九大、十大、十一大階段,革命斗爭(zhēng)的歷史語(yǔ)境發(fā)揮著主導(dǎo)性的制約作用,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語(yǔ)境則變成了直接的元政策話語(yǔ);在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階段,當(dāng)代中國(guó)社會(huì)利益關(guān)系變遷的現(xiàn)實(shí)語(yǔ)境上升至顯著的主導(dǎo)性地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語(yǔ)境仍然通過(guò)“建設(shè)有中國(guó)特色的社會(huì)主義”發(fā)揮著合法化的話語(yǔ)整合作用,而革命斗爭(zhēng)的歷史語(yǔ)境(此時(shí),革命斗爭(zhēng)很大程度上是指“文化大革命”這一特殊的革命斗爭(zhēng)時(shí)期)則主要充當(dāng)著“改革開(kāi)放”的相對(duì)性語(yǔ)境。
從話語(yǔ)活動(dòng)角度看,革命斗爭(zhēng)的歷史語(yǔ)境不僅承載著公共政策話語(yǔ)活動(dòng)最重要的組織延續(xù)內(nèi)容——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它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語(yǔ)境合法性的一個(gè)重要的歷史論證基礎(chǔ),并影響到對(duì)利益關(guān)系變遷形勢(shì)做出合理性判斷的成本計(jì)算(如制度傳統(tǒng)、組織繼承和社會(huì)心理慣性等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語(yǔ)境的合法化功能不僅體現(xiàn)在對(duì)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理論話語(yǔ)的轉(zhuǎn)引與解釋?zhuān)瑢?duì)于特定價(jià)值觀念的意識(shí)形態(tài)表述,它還必須適應(yīng)利益關(guān)系變遷的現(xiàn)實(shí)語(yǔ)境,要能夠解釋乃至整合現(xiàn)實(shí)利益關(guān)系語(yǔ)境的合理性目標(biāo);利益關(guān)系變遷現(xiàn)實(shí)語(yǔ)境的合理化功能主要體現(xiàn)在如何做出相應(yīng)的公共政策認(rèn)知和話語(yǔ)表述,在這里,即使代表合理性目標(biāo)的公益有著終極的價(jià)值取向意味,但是考慮到現(xiàn)實(shí)利益關(guān)系的復(fù)雜性以及實(shí)現(xiàn)各種利益目標(biāo)的現(xiàn)實(shí)路徑,以革命斗爭(zhēng)為基本內(nèi)容的歷史觀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話語(yǔ)整合都將是不可或缺的。
正是在這三重語(yǔ)境的交合作用形勢(shì)下,形成了這一時(shí)期特有的公共政策話語(yǔ)變遷的歷史路徑,或可稱之為公共政策話語(yǔ)方式,即規(guī)范意義上的革命話語(yǔ)取向和公共政策話語(yǔ)取向交互存在的結(jié)構(gòu)狀況,革命話語(yǔ)取向與公共政策話語(yǔ)取向之間,既有此消彼長(zhǎng)的替代關(guān)系(如縱向地比較八大階段、九大十大十一大階段以及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階段),又有體現(xiàn)于不同政策話語(yǔ)主題的共存關(guān)系(如在八大政治報(bào)告文本中),這種公共政策話語(yǔ)方式,集中地反映在處于最高權(quán)力層級(jí)的元政策話語(yǔ)說(shuō)出之中,基于公共權(quán)力在整體社會(huì)系統(tǒng)中的強(qiáng)勢(shì)地位,并通過(guò)元政策話語(yǔ)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的傳播及其效力現(xiàn)實(shí)化過(guò)程,作用于整個(gè)國(guó)家的公共政策活動(dòng)形式、政治運(yùn)行機(jī)制乃至社會(huì)文化生活、日常話語(yǔ)活動(dòng)的方方面面,比如文學(xué)、文藝作品中好壞人的二元?jiǎng)澐帧⒄呋顒?dòng)強(qiáng)烈的政治化(意識(shí)形態(tài)化)色彩以及日常話語(yǔ)表述的泛政策化(或泛政治化)等等。在革命話語(yǔ)取向和公共政策話語(yǔ)取向之間,元政策話語(yǔ)可能通過(guò)話語(yǔ)信息或文字信息上的廢止、更替等方式實(shí)現(xiàn)相關(guān)的轉(zhuǎn)換,但是由于制度規(guī)范的多重性、組織利益以及個(gè)人心理慣性等原因,特定話語(yǔ)取向(主要是指革命話語(yǔ)取向)的影響力的消解必然是一個(gè)長(zhǎng)期而緩慢的過(guò)程,在此意義上,這一政策話語(yǔ)方式對(duì)當(dāng)代中國(guó)人的思維認(rèn)知方式和話語(yǔ)表述方式的影響又將是極其深遠(yuǎn)的。
作者單位:河海大學(xué)公共管理學(xué)院
責(zé)任編輯:劉之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