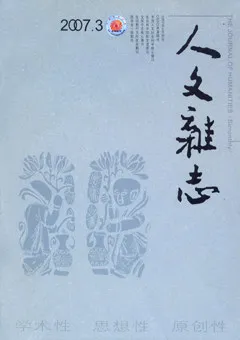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新賢妻良母主義”論析
內容提要 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男女平等觀念的廣泛傳播,傳統的“賢妻良母”觀念也開始吸收一些具有時代特色的內容,有人將婦女“賢妻良母”的傳統角色定位,與國家、社會的發展相聯系,并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重新定義“賢妻良母”的標準和內涵,在一種新式的情境下強調婦女的“母職”和“妻職”。盡管“新賢妻良母主義”仍然充滿了封建守舊色彩,但是它對于傳統家庭分工模式的重新思考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 男女平等 賢妻良母 母職 妻職 家庭分工
〔中圖分類號〕C913.6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07)03-0150-07
“賢妻良母”作為中國女性的傳統形象和生活的基本范式,在近代中國曾引起廣泛而又激烈的爭論,有人將之看作女性行為方式的最高典范,也有人將之斥為婦女解放的絆腳石。進入民國時期,特別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賢妻良母主義”在與女性獨立、個性主義等思潮的論戰中,也開始融入一些新鮮的時代特征,從一些全新的角度和內涵來闡釋“賢妻良母主義”(注:關于賢妻良母主義,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呂美頤:《評中國近代關于賢妻良母主義的論爭》,《天津社會科學》1995年第5期;林吉玲:《中國賢妻良母內涵的歷史變遷》,《社會科學輯刊》2001年第4期;李卓:《中國的賢妻良母觀及其與日本良妻賢母觀的比較》,《天津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沈倩:《賢妻良母與英雄豪杰——晚清時期男女異路的女權運動》,《浙江學刊》2003年第3期;夏蓉:《20世紀30年代中期關于“婦女回家”與“賢妻良母”的論爭》,《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程郁:《二十世紀初中國提倡女子就業思潮與賢妻良母主義的形成》,《史林》2005年第6期;鄭雷:《也論“賢妻良母”》,《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這些文章或整體回顧近代以來關于賢妻良母的幾次大論戰,或分析賢妻良母概念內涵的歷史變遷,或將賢妻良母與“婦女回家”、女性就業等思潮相聯系,論述它對婦女解放運動所造成的負面作用。),這就是所謂的“新賢妻良母主義”。
一
在五四時期,男女平等問題一時“成為社會人士聚爭的問題”(金仲華:《節制生育與婦人生理的解放》,《婦女雜志》第17卷第9號,1931年9月。)。與此前的女權理論不同,五四時期人們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女性形象——“娜拉”,將男女平等放在個性解放的角度來論證,發出“女人是人”的呼聲。這種女權觀念或許可以用女作家廬隱的一句話來予以說明:“今后婦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籬到社會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過人類應有的生活,不僅僅作個女人,還要作人。”(注:廬隱:《今后婦女的出路》,錢虹編:《廬隱選集》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頁。)將女性視為可獨立于家庭、丈夫與兒女之外的個人,“啟示婦女到社會去,脫離‘傀儡家庭’和男子的奴隸”(旅岡:《漫話“娜拉年”與“戲劇年”》,《申報》1935年12月27日。),是這種觀念帶給中國女性最強烈的沖擊。婦女問題研究專家舒蕪先生曾說過,新文化運動中提出的婦女問題,“其實就是婦女的人格獨立、人身自主、人權平等的問題,就是‘人的發現’推廣應用于婦女身上,發現了‘婦女也是人’,婦女發現了‘我也是人’,由此而生的種種問題”(注:舒蕪編錄:《女性的發現——知堂婦女論類抄》,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4頁。)。五四以后,“女人是人”的呼聲更加響亮。
盡管“女人是人”的呼聲在五四時期已經響起,并且得到了一部分人的響應,但是并未在社會各個階層中得以普及,它在向下傳播的過程中,更是遇到了強大的思想抵抗,“賢妻良母主義”即為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一股思潮。“賢妻良母主義”有其西方的理論源頭,因提倡戀愛自由而備受近代國人青睞的愛倫凱(EllenKey)就非常重視婦女的“母性”特征,認為婦女最重要的天職便是母職,婦女之所以是婦女,就在于她的母性,女子的天性就適合母職。如果做母親的不能充分履行其天職,那么無論做別的什么事業,都是不足取的。因此婦女不應該從事職業,婦女的真正的事業是生育兒女,她們如果拋棄天賦的職務去從事勞動,就勢必會使文化中最重要最寶貴的要素——母性,一代一代地消滅下去。(注:鏡影:《婦女在家庭中的任務》,《婦女雜志》第15卷第10號,1929年10月;蓬洲:《婦女就職與母性問題》,《婦女雜志》第13卷第2號,1927年2月;黃石:《婦女果不適于職業么》,《婦女雜志》第10卷第6號,1924年6月。)
近代中國的“賢妻良母主義”者以愛倫凱等人的學說為理論參照,也著重強調養育幼兒、照料家事的“母職”、“妻職”才是婦女的“天職”。他們一開始常常借口婦女生理上特殊的構造,有的認為女子天生的習性特質,就是“溫柔而精密”,所以非常適宜治理煩瑣的家務(注:王漢威:《夫妻的義務》,《婦女雜志》第15卷第12號,1929年12月。),從男女兩性的能力上看,“男主外,女主內,實為不易之論”(注:心冷:《新女子與家庭》上,《申報》1921年10月30日。)。有的則拿婦女的“生殖機能”大做文章,認為由于只有女子擁有這項機能,所以女子的專職就是“延種的生產”,男子則應專職“延命的生產”,“我們簡直可以說,男子最神圣的是勞動,女子最神圣的是生育”(注:許地山:《現行婚制之錯誤與男女關系之將來》,《社會學界》第1卷,1927年。)。
2007年第3期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新賢妻良母主義”論析由于自晚清以來,人們對于傳統綱常禮教進行了持續的批判,仍然以充滿封建色彩的“三從四德”為號召,顯然已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和宣傳市場。并且到了抗戰以后,由于戰爭的需要,婦女英勇參戰和廣泛參與到生產領域的事實,使得那些僅以生理和心理上差異的立論已經明顯不再適用。于是很多人開始對傳統道德觀念進行全新的詮釋,在婦女“個性”的宣傳熱潮下,將婦女“賢妻良母”的傳統角色定位,與國家、社會的發展相聯系,在一種新式的情境下強調婦女的“母職”和“妻職”,“在增強婦女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和爭取自身幸福的掩護下,發揮議論”(注:白霜:《回家庭?到社會?》,《解放日報》1944年3月8日。)。以此反對婦女走出家庭、就職社會。
在強調婦女治理家庭對于國家和社會的意義時,當時中國的“賢良主義”者往往首先模糊社會和家庭的界限,認為社會只不過是一個空名,并沒有實在的本質,要說社會實在的本質,就是“家庭”、“學校”等團體,“講社會兩字,不能籠統,家庭豈不就是社會?”(注:劉伯明演講,張友鸞、陳東原記:《女子問題》,《婦女雜志》第8卷第5號,1922年5月。)既然如此,那么婦女在家庭做她的賢妻良母,不就等于在社會上服務了嗎?因此有人說既然男子為了家庭經濟的重擔,在社會上為生活掙扎,那么女子把家庭弄得整整齊齊,安慰男子在社會服務的辛勞,“間接的也是為社會服務” (注:莫湮:《中國婦女到那里去》,《東方雜志》第33卷第17號,1936年9月。)。“管理社會一部分的事務,不是作社會的事業么?不是盡那社會的一員的責任么?”(注:范隅:《婦女的家庭工作》,《婦女雜志》第10卷第6號,1924年6月。)這樣看來,妻子的工作就不是為一家或一人而做的,乃是為全社會、全人類而做,所以“妻”的責任是非常重大宋孝璠:《妻的責任》,《婦女雜志》第15卷第10號,1929年10月。)。為了安慰那些主婦們失落之心,他們又給治理家務的主婦們戴上了高帽,稱“主婦之持家,若總理之治國,其天職之重要,不勝枚舉” (注:豪:《主婦之天職》,《申報》1923年8月30日。);“我們要知道婦女們,把家務措置得當,把子女管理得法,其造福社會,與男子是相等的,無絲毫退讓的。……如車有兩輪,鳥有雙翼,缺一不可的” (注:張銘鼎:《何謂內助》(小家庭的主婦征文),《婦女雜志》第13卷第1號,1927年1月。)。并稱如果婦女紛紛走出家庭,必然會導致家庭動蕩,并最終導致社會的崩潰。“所以欲求充實家庭,便更只有驅逐婦女回到家庭去。”(注:邦彥:《誰是家庭的主持者?》,《家庭星期》第1卷第23期,1936年5月3日。)當抗戰爆發,男人們紛紛走上戰場的時候,人們更有理由理直氣壯地要求婦女留在家中治理家政,因為當將士效命疆場之時,顯然不能擔負家庭責任,常常不免有后顧之憂,如果妻子們能夠治理好家務,代負其責,就會使前方將士勇于前進了(注:朱綸:《抗戰建國時期婦運的理論及其實際工作》,《婦女文化戰時特刊》第20期,1938年9月1日。)。
還有一些人從著力強調婦女對于兒童教育重要性的角度立論,認為“對于綿延宇宙之生命,促進社會進化者,總是賴后進的兒童們”,兒童們的教育,當然離不開家庭,而家庭教育任務的承擔者,又總是母親們(注:謙弟:《近代已婚婦人解放論》,《新女性》第2卷第2號,1927年2月。)。那么,做母親的如果不能好好負起教育兒童的責任,則國家民族的衰落,便是不能避免的。因此,他們認為女子應當回到家庭去教育自己的子女(注:莫湮:《中國婦女到那里去》,《東方雜志》第33卷第17號,1936年9月。))。雖然也有人承認女子除了“為母”的職責外,也有“為人”的職責,然而比較起來,他們認為還是前者更為重要,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時候,只好舍“人職”(humanhood)而盡“母職”(motherhood)了(注:⑩黃石:《愛倫凱的母性教育論》,《婦女雜志》第10卷第5號,1924年5月。)。因為婦女如果到社會就職,在社會公益設備不完備,孕育嬰兒工作不能避免的情況下,職業生活的結果,“總不免有損害母性之虞”(注:蓬洲:《婦女就職與母性問題》,《婦女雜志》第13卷第2號,1927年2月。)。所以如果顧及家庭就不能置身職業,“雙方兼顧勢所難能”(注:云裳:《中國式的丈夫》,《婦女共鳴》第4卷第11期,1935年11月。)。西方學者泰伯爾(Tarbell)就曾論道:“在各種職業和工業中,有很多成功的婦人,但沒有偉大的婦人。”又說:“職業生活的成功,是壓迫模范而健全的婦人的天性最強的壓力。”愛倫凱也說“如果不使女子做‘靈魂的教育者’,而使她們和男子一樣,從事家外勞動,實在是精力的大誤用”(注:黃石:《愛倫凱的母性教育論》,《婦女雜志》第10卷第6號,1924年6月。)。這一點也正是中國的“賢妻良母主義”者所信奉的。
通過對古今中外思想資源的援引,很多人得出這樣的結論:“為母的職務,不只是女子最高的使命,并且是女子最高的福樂。……我們不欲拯救世界則已,茍欲拯救世界,非實行母性復興運動不可!換句話說,拯救人類出于墮落的責任,完全放在女子的身上。”⑩既然婦女留在家中,盡尊嚴神圣的“母職”是如此重要,他們質問:“為什么新的婦女寧愿放棄尊嚴神圣的母責,向‘家庭工作’之外的職業上奮斗呢?”(注:范隅:《婦女的家庭工作》,《婦女雜志》第10卷第6號,1924年6月。)他們聲稱即使娜拉生在當時的中國,就是知道家庭是一個傀儡,也不能不忍苦耐勞下去,否則解放和自由固然能夠得到,但幸福仍然不能得到。因為娜拉出走以前是女子單方受苦,單方受拘束,如果出走了,就會變成雙方都受苦,雙方都受拘束了。所以娜拉即使已經離開了家庭,也應該為了責任而回到家庭來。“這并不是說回到家庭來做良妻賢母,而乃是說回家來與丈夫相愛以終,共策進行。我們不可只顧自己的歡快和融洽,也應看到他人的苦痛與不和諧。”(注:鋗冰:《娜拉走后究竟怎樣》,《國聞周報》第11卷第11期,1934年3月19日。)總之,重視女子的“母性”、“母職”和“妻職”,而輕視女子的“人性”和“人職”,是這一派共通的根本觀念。
二
“回家庭?到社會?是婦女運動中的基本論爭,貫穿了中國婦女運動的整個歷程”(注:白霜:《回家庭?到社會?》,《解放日報》1944年3月8日。),這是民國時人準確的歷史總結。五四以后,“新賢妻良母主義”者從國家與社會的角度來論述“母職”與“妻職”的重要性,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這也引起了許多有識之士的警惕,并對此展開了批判。堅持婦女應該就業的人認為,“母性保護論”者既然承認女子也是個“人”,就不能否定女子的勞動權,因為每個人都有勞動權與生活權。他們根據紀爾曼夫人(CharlottePerkinsGilman)的學說,認為凡人都具有兩種機能,一種是“自我保存”的機能(thefunctionofself-preservation),一種是“種族保存”的機能(thefunctionofrace-preservation)。“母權論者只許女子發揮種族保全的機能,不許女子發揮自我保全的機能;只許女子發揮她們的母性,不許發揮她們的‘人性’,持論未免太偏頗了!”黃石:《婦女果不適于職業么》,《婦女雜志》第10卷第6號,1924年6月。另外在當時國民經濟崩潰、人民貧苦化程度不斷加深的情況下,叫婦女回到家庭去或者叫她們安心地住在家中,經營家務,除了極少部分的特權者、富有者之外,基本上沒有這個可能。所以他們指出這種為絕對大多數婦女所不能實行的“回到家庭去”的理論,只是反映了最上層的、最少數的貴人們的要求與心理,在事實上也是不可能實現的(注:莫湮:《中國婦女到那里去》,《東方雜志》第33卷第17號,1936年9月。)。至于母權論者所強調的母職、妻職,他們借用母權論者的理由——天性、天職——譏諷道:“至于母職的應該尊重,原是不錯。但我們要曉得母職是婦人天然的本能,決不會因職業的緣故而薄弱。”(注:Y.D.:《職業與婦女》,《婦女雜志》第7卷第11號,1921年11月。)
參照近代社會關于“賢妻良母主義”的幾次大爭論,如果我們仔細體味反“賢妻良母主義”者的意見,會發現反對者的理由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強調經濟狀況和抗戰現實不允許婦女回到家庭,二是反對“賢妻良母”這個字眼,或者說反對“賢妻良母”這四個字所體現的封建色彩及其所代表的舊倫理標準。“賢妻良母”一詞是從封建社會沿襲下來的,其傳統含義的確蘊有將婦女當成男子寄生蟲和附屬品的意味,“使伊作丈夫的奴隸,那便是'賢',叫伊做孩子們的奶媽,那便是‘良’”(注:蜀龍:《新賢良主義的基本概念》,《婦女共鳴》第4卷第11期,1935年11月。)。所以這四個字確實有點令人望而生厭,難怪很多人將賢妻良母的思想與封建勢力直接掛起鉤來,認為“這種思想能在中國社會流布著,而形成一種現實的勢力,是與封建思想在我國尚有穩固的基礎,有極大的關系”(注:莫湮:《中國婦女到那里去》,《東方雜志》第33卷第17號,1936年9月。)。但是面對著母權論者這樣的詰問:“凡是婦女都要為妻為母的,做了妻母,當然應該賢良,反對良妻賢母主義的人,難道主張女子不該做妻做母,做了妻母應該以不良不賢為正宗么?”(注:⑦光義:《良妻賢母主義的不通》,《婦女雜志》第10卷第2號,1924年2月。)我們注意到幾乎沒有人反對婦女應該“賢”和應該“良”。
反對者雖然從各個方面駁斥“賢良”論,卻沒有人敢于公然聲稱婦女應該不良不賢。他們只是強調要將婦女應不應該賢良的問題,與“賢妻良母主義”問題劃清界限。例如有人從“賢妻良母”的詞義出發,來說明這四個字的不通,認為“婦女的須做妻做母,做了妻母的應該賢良,乃是不待言的事,本來不成為主義”,比如說我們是人,我們應該做人,而且應該做好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所以根本用不著立一個“好人主義”的名詞來玩玩。妻和母同樣原不過是人的職分之一,除了做妻做母之外,婦女還可以做教師、做議員、做官吏、以及做學者、技術家等等,難道婦女只有做妻做母時應該賢良,做別的事情便該不賢良了么?“所以我說,良妻賢母主義這一個名詞,實在是不通的。”⑦有的干脆承認賢良是婦女的美德,但又從其它方面來強調“賢妻良母”不應該成為一種主義,或者說現實情況不允許“賢妻良母”成為主義。例如有位女士首先聲明她并不主張“惡母壞妻”運動,不過她認為要把“賢母”或“良妻”作為人生最高的價值,則大錯特錯。因為近代社會經濟困難,男子不可能獨力撐持一個家庭,女子非出來共同工作不可,這是必然的趨勢。所以說賢妻良母主義是事實上所不可能實現的,“如此對這個方面的運動,直可謂之‘向時代開倒車’!”(注:何覺我女士:《婦女運動的錯誤及正軌》,《婦女雜志》第10卷第4號,1924年4月。)一個署名盤石的論者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反對賢妻良母,并不是希望每個女子將來都成為刁妻惡母,而是反對那不合時代的賢妻良母,也就是反對以封建社會的道德標準來度量今日的婦女。”(注:盤石:《中國婦女婚姻上所受的壓迫》,《東方雜志》第33卷第11號,1936年6月。)這實際上道出了問題的本質。
當賢妻良母、母職、氣質、職業這幾個概念糾纏在一起的時候,人們很容易無所適從,不知道究竟如何才是“賢良”,應不應該就業。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就無法從根本上厘清傳統“賢妻良母”觀念在人們思想中的消極影響,也就無法順利地開展婦女職業運動。故而盡早澄清這幾個概念之間的關系,就顯得非常重要。1942年擔任中共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親自撰寫了一篇《論“賢妻良母”與母職》的文章,解答婦女的賢良與就業的關系問題。文章一開篇就承認“無論在何社會,做母親的當然要良,做妻子的當然要賢,這猶之做父親的當然要良,做丈夫的當然要賢,一樣成為天經地義不可變易的真理”。站在解放婦女的立場上,周恩來并不反對良母或者賢妻這兩個獨立的“美稱和贊意”,但是認為一旦“賢妻良母”作為一個固定的連結在一起的名詞,就具有了特定的含義,“是專門限于男權社會用以作束縛婦女的桎梏”,因此必須反對。即使在“賢妻良母”的前面加上一個“新”字,或者對“賢妻良母”進行新的定義,也是需要加以反對的。盡管這種做法可能是完全站在男女平等的立場,要求婦女盡其應盡的母職和妻職,但只要保持了這個舊的固有的名詞,“你便先陷入男權社會的立場,而將婦女在社會上地位定型化了之后,再加以新的解釋,這無論如何是不妥的,而且也不合邏輯的”。
周恩來也承認母性的偉大和母職的重要,“我們尊重母職,提倡母職……母職,是婦女在人類社會中最光榮的天職”,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任務,再比母職光榮和永恒的了。但是提倡母職并不意味著婦女應該回到家庭,“婦女于盡母職的時候,少做一點其它事情,不僅是許可的,而且是分工的必須”。所以周恩來認為應該反對借口婦女應盡母職,因而取消其社會職業的做法。文章最后主張以尊重母職提倡母職為中心的新觀念來代替“賢妻良母”的舊觀念(注:周恩來:《論“賢妻良母”與母職》,《新華日報》副刊《婦女之路》,第38期,1942年9月27日。)。
周恩來的意見同樣可以適用于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新賢妻良母主義”言論的評判,也就是說婦女的母職和妻職都很重要,但是不能據此就認為婦女的職業只有母職和妻職,更不能就此提倡“賢妻良母主義”。在周恩來看來,個性與母性、社會職業與母職并不是極端對立、非此即彼的,所以不能以母職、妻職為借口來反對婦女的解放運動。這種看法無疑有其深刻之處,但是在周恩來的文章中,有一個問題卻沒有論述清楚,就是究竟什么是母職?他承認母職和妻職是重要的,但是對母職和妻職的具體內容卻沒有做出詳細的界定,更沒有指出男性在家庭中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應該分擔哪些傳統社會里的母職和妻職。這種理論上的含糊性,導致了當時有很多人一方面承認女子是“人”,她有人的自由、權利同責任,應該有機會培養她的人格、知識和技能;而同時卻又將傳統社會里的母職和妻職的內容一股腦地加在新女性的身上,讓她們同時承擔個性發展與母性、妻性發展的雙重任務。例如有人說:“一個要達到她做‘人’的地位的女子,既要保存她的女性同母性的滿足,又須發展她的個性的機會。”王國秀:《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與婦女運動》,《東方雜志》第32卷第21號,1935年11月。他們既承認“婦女經濟獨立,實在是婦女解放的根基,婦女就職的確是很重要的了”,又認為“母性當然是婦女最重要的事,婦女最大的職務,不可廢棄的”(注:蓬洲:《婦女就職與母性問題》,《婦女雜志》第13卷第2號,1927年2月。當時這樣的言論很多,還可參見三無:《婦人職業問題之學說及批評》,《東方雜志》第17卷第10號,1920年5月。)。這就是他們認為在現有的社會關系下的女子的“自立”(注:莫湮:《中國婦女到那里去》,《東方雜志》第33卷第17號,1936年9月。)。但是這樣的雙重發展,其實就是加在婦女身上的雙重壓力,其結果是必然極大地影響女性在職業之路上的進取。
三
為了回應反對者的責難,“新賢妻良母主義”者對“賢”和“良”的標準做出新的界定,以別于“舊”賢良主義。如屠哲隱就注明,所謂“賢妻”并不是指服從丈夫,而是要與丈夫共建優美的家庭,扶助丈夫的事業。所謂“良母”更無服從兒子的意思,而是要教育兒子,使之成為有用的國民(注:屠哲隱:《賢妻良母的正義——為“賢妻良母”四字辯護》,《婦女雜志》第10卷第2號,1924年2月。)。盤石也聲言:“新時代的賢妻,是要知道把自己從家庭勞役中解放出來,與男子同樣的走向社會;新時代的良母,是知道教導她們的子女繼續著她們未完成的工作,并且知道教導他們成為有益于大眾的人。”盤石:《中國婦女婚姻上所受的壓迫》,《東方雜志》第33卷第11號,1936年6月。鄭錫瑜則認為,新賢良主義“就是女子用科學的精神,幫助丈夫的事業,用合乎衛生方法處理家政,用新教育法撫育教育兒女” (注:鄭錫瑜:《評新賢妻良母主義》,《婦女月報》第1卷第5期,1935年6月。)。
1935年《婦女共鳴》雜志曾刊發了一期“新賢良專號”,專門闡述自己的宗旨和新賢良主義的基本概念。概括起來,他們的看法主要是兩點:第一,賢良的前提是家庭內的男女雙方必須平等,是基于男女兩方平等原則下所負的一種家庭責任。“妻的責任乃是與夫的責任相對待。夫如不盡責任,妻沒有獨盡責任的理由。母的責任乃與父的責任相平等,父如不盡責任,妻〔母〕沒有單盡責任的理由。”(注:⑦蜀龍:《新賢良主義的基本概念》,《婦女共鳴》第4卷第11期,1935年11月。)第二,在男女責任平等的基礎上,不僅要提倡“賢妻良母”,也要提倡“賢夫良父”,因為賢妻“是相對賢夫而存在的”(注:峙山:《賢夫賢妻的必要條件》,《婦女共鳴》,第4卷第11期,1935年11月。)。所謂新賢良主義,乃是贊成賢良的原則而反對偏于女性的賢良,進一步提倡男女兩方共同賢良,以維持幸福的家庭。“賢良必求之于男女兩方平等。我們必要男子作起賢夫良父來,不能單求女子作賢妻良母。”⑦新賢良主義甫一出現,立即引起很多人的反對,他們認為其實質是一方面要求知識婦女回家做“賢妻良母”,這無異于賢良主義的“借尸還魂”;另一方面則進一步要求青年知識男性也回家做個服服帖帖的“賢夫良父”,使那些漢奸投降派能夠從從容容地做他們“睦鄰”的工作(注:羅瓊:《從“賢妻良母”到“賢夫良父”》,《婦女生活》第2卷第1期,1936年。)。“所以不管他們怎樣在賢妻良母之上,冠以一個‘新’字,實際上決不會超過封建意識的范圍。‘新’字的作用,最多不過是一種麻醉或是一種欺騙而已。”(注:梅魂:《婦女到社會去的論據及其目標》,《婦女共鳴》第5卷第1期,1936年1月。)當代研究者對其也多持批判態度。正如前文所述,“賢良”這個概念經過封建社會的長期打磨,已具有特定的內涵,它意味著對女性的束縛和壓迫,是將婦女捆綁在家庭的鎖鏈。不加甄別、不加解釋地套用這一概念,只能造成思想的混亂或成為復古思潮的幌子,使復古思潮借其旗號而大行其道。“新賢妻良母主義”雖然對賢良的標準進行了重新定義,立論看似新意迭出,但是大多數的言論恰如時人所言,都只是在“賢良”兩個字義上布置迷魂陣(注:集熙:《“賢妻良母”的認識》,《婦女共鳴》第4卷第11期,1935年11月。)。而且如果僅僅圍繞著“妻”、“母”來定義婦女的價值,那么無論怎樣定義,婦女的價值實現,總還是圍繞著丈夫和兒子,缺乏自己的獨立價值。從這一角度說,對“新賢良主義”的批評確實很有必要。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新賢良主義”宣揚男女平等和夫婦共賢,要求夫婦共同擔負起家庭的責任,卻是相當合理性的。當時,也有少數有識之士在提倡男女共同承擔家務勞動。例如新女性代表之一、《婦女共鳴》雜志主編李峙山在談到自己對于理想配偶的要求時,就表示:“因為我是一個做革命事業的女子,當然無暇來做管家婦;所以他必須愿意同時和我操作臨時家庭中的一切瑣碎事宜。”“因為女子對于兒女已盡了生育的責任,所以我希望他對于子女盡養育和教育的責任。”(注:峙山:《我的理想伴侶與實際伴侶》,《女星》第32期,1924年3年6日。)另一位女性也希望自己未來的配偶能夠做到:“我的公事較他忙的時候,他能代我稍理家務,預備飲食。當他忙的時候,當然,也幫他忙。”(注:若吾:《我之理想的配偶》五十,《婦女雜志》第9卷第11號,1923年11月,第129頁。)更有人進而主張男女應根據“分工”和“互助”的原理來對家庭負上責任:
譬如說,男的方面在能力上及事業上均有較好的地位和收入時,則男子方面至少應擔負大部或全部的經濟責任,而女的或因學識能力與社會地位較差的原故,則至少應擔負家庭日常生活之布置和處理;相反地,若女的因社會地位及旁的能力稍長于男子,則男子至少也應該擔負家庭之日常生活的責任。至于男女兩方均能從事于職業,而且均能對家庭擔負經濟上及日常生活上的責任的話,那是再好沒有的事情了!(注:葉輝:《男女對于家庭的共同責任》,《婦女共鳴》第4卷第12期,1935年12月。)
這些言論與“新賢妻良母主義”的主張可謂異曲同工。“新賢妻良母主義”宣揚夫婦共賢,共同擔負家庭責任,正是在男女平等原則的基礎上對夫妻社會分工與家庭分工的重新考慮。只是由于過去中國婦女的唯一職責就是困守家庭整理家務,這種觀念沿襲到民國時期,導致人們形成了這樣的一種思維定式:管理家務一定是全職的,管理家務就意味著退守家庭。在這種語境限制下,“新賢良主義”的主張自然而然就被誤解為不僅要女子退回家庭,而且要將男子也拉回到家庭中去。從“新賢良主義”理論的本身來說,其實并未含有這樣的意思。新賢良主義的主張者在回應批評時曾解釋道:“擔負責任,并不必回家庭。”(注:李峙山:《賢良問題之再論辯》,《婦女共鳴》第5卷第2期,1936年2月。)他們認為批評者最大的錯誤在于“把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完全混為一談了”,“所謂新賢良主義者,當然是指的家庭生活的主義。大前提范圍在家庭里面,何嘗說過要叫人整個的生活葬送在新賢良主義中去呢?……我們不曾主張男女都死守在家庭中,對于家庭負責與死守家庭或與以家庭為人生最后目的,當然兩樣”(注:蜀龍:《讀了“從賢妻良母到賢夫良父”以后》,《婦女共鳴》第5卷第2期,1936年2月。)。從這樣的表白來看,“新賢妻良母主義”還是具有一定合理內涵的,只是這些內涵,在那個時代不被人看重和認同。
綜言之,“新賢妻良母主義”與傳統的“賢妻良母”觀念已經有了很大的區別。盡管“新賢妻良母主義”仍然充斥了一些帶有封建倫理色彩的陳詞濫調,但是它也吸收了一些男女平等的觀念,對“賢妻良母”的標準和內涵進行了重新定義和闡釋。綜觀“新賢妻良母主義”者及其反對者的言論,我們發現其實這二者對于傳統的社會分工和家庭分工模式都缺乏足夠的理論反思。“賢妻”、“良母”固然是每個婦人都應該做到的行為規范,但是“新賢妻良母主義”者往往就因為過于強調這一點而忽視了婦女職業的問題,結果與“婦女回家論”同聲共氣;同樣,強調婦女經濟獨立權和職業權的論者往往著力論證母性、家事不是婦女的天職,而不去從理論上進一步厘清男人是否同樣具有處理家務、撫育嬰兒的義務。這正是導致民國時期有關賢妻良母的爭論嘵嘵不休的根本原因。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
責任編輯:黃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