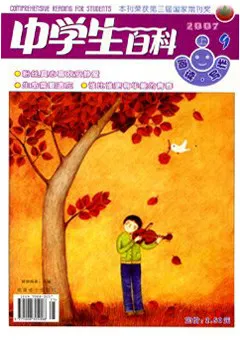小“荷管”
一個有女孩名字的男生比一個有男孩名字的女生要慘。
十六七歲的時候,如果是一個女孩,那么剪一個短短的頭發,穿亨利領T恤,牛仔短褲露出光滑的膝頭,雙肩包單手提著,單車坐椅調到最高,像運動員那樣翹著屁股快速地騎過同學身邊,大家喊出她那男生一樣的名字時,她幾乎很得意。相反,一個男生名字像女生,不論他本身多么有型也是注定要被減掉幾分的。世事無常,我們都無法預料會不會碰上一對喜歡給兒子取女孩名的父母。
所以那天點名時我們哄堂大笑。他站在教室最后一排,白衣服沒有任何圖案,臉上也沒有任何表情,他那雙細長漂亮的手,蒼白地按在絳色桌面,身后是豆綠的粉墻。他不笑。他不笑更像在笑。我們一廂情愿地認為那是幽默感,是滑稽的和可愛的。我們甚至期待他會成為班里的諧星。可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是一個要強愛面子又心事重重的男孩,他開始覺得了名字帶來的壓力。每天上學,為了避免同學喊他,他低著頭走路。高高個子,少年老成,他的背微僂,像銀川沙漠游樂場里的瘦駱駝。
那是缺少自知之明的年紀,放學的路上我們又總喜歡叫他。喊出他的名字未免便被別班的陌生同學聽到,漸漸大家都知道了學校有一個男生叫著女孩的名字。有人給他起了各種外號,他慢慢憤怒了。終于有一天,他跟我們發火。在周末補習回來的中午,公車站旁邊,他指著我們每一個人大聲質問:你們覺得這有意思嗎?他忽然拿出一把小刀子,當著我們的面劃在手背上。他漂亮的手,有血一絲絲流下來。他的舉動讓我們害怕,卻也讓我們興奮。每一個人都想逃開他的憤怒,卻又目不轉睛地看著他。有一段時間的冷場,接著天邊忽然響起了一聲悶雷,五月天空的兩大塊云撞到一起,雨傾盆而落。大雨里不知誰開始沒心沒肺地發笑,接著我們都大笑起來,好像只有大笑才可以解釋我們的歉意,以及我們那淡淡的故意。
而他站在原地。驟雨在猛烈地降落到地球,他也許第一次生出了外星人一般的疏離感,覺得自己不如回到火星上去。
后來,我們畢業,與他失去聯系。不是我們不去打聽,而是他故意封鎖了一切聯絡的可能。他拒絕往任何人的校友錄里寫自己的名字,他的固執與堅持,就像我們當年嘲笑他一樣顯得那么別扭和不懂事,但是,沒什么的,青春過去,一切都過去了。
多年以后,我在澳門永利大廈看我的游伴們在賭博。在澳門的每一間賭場,都有人專門替人發牌。他們穿著統一的純黑制服,統一的蒼白皮膚,統一黑框的眼鏡后面,是沒有表情彼此相似的眼神。在澳門,這種職業叫作荷官,如果你問一個荷官他叫什么名字,他會回答你:荷官。荷官沒有名字。
有一位荷官在手指上戴著鉆戒,靠手吃飯的男孩,一般都有好看的雙手。
我忽然想起他的手,那雙好看的手。
不知道那雙手的主人現在在哪里,會否有人問起他的名字。
編輯/孫櫟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