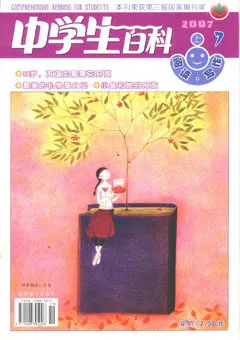藍鵬
藍鵬是我在高一時認識的。我們兩個都喜歡音樂,暑假同在一家音像店打工。
他很瘦,且容易緊張,脾氣似乎也不太好,經常和顧客吵架,沒幾天就被解雇了。但不知道為什么,他很喜歡和我在一起,只要我在店里他就來泡著,或者在街邊等我。也不多說什么,無非是彈段吉他給我聽。說實在的,一個男生這么黏人,心里覺得怪怪的,但又擔心他,于是敷衍著。
后來好久沒有他的消息,我給他發短信問好也沒回,心想:這個朋友興許不用我擔心了。
某天,藍鵬突然打電話給我,第一句話就是:“你能不能把你的吉他借我用用啊?”
我心里莫名其妙,問他:“最近怎么樣?兩年多沒有你的消息了。”
“你能不能借我你的吉他用用?”他說。顯然他對我的問候無動于衷。
我心里有些起急,想他怎么自說自話,完全沒聽我在說什么。
他又說:“我是說,你的吉他借我用一陣。”
我還是沒有理會:“最近好不好?現在忙什么?”
“我問你呢,借我你的吉他用用!”他竟然有些著急得嚷起來。
我聽得不耐煩,說:“怎么了你到底?”
“我是說,你借我你的吉他……”
我不可能借給他,一方面那是我的心愛之物,另一方面,我怕借給他。他是個沒有邏輯的人,至少從我這個角度上看,兩年沒見,藍鵬仍舊沒有成熟起來。于是,我說:“我把吉他賣了。”
他聽后竟然歇斯底里地大叫起來:“你就借我吉他用用吧,我快不行了。沒有琴彈,我受不了了!你就借我吧,求求你了,借我吧!”
我是了解藍鵬這個脾氣的,但是兩年的時間,我以為他能學會理智。我沒有說話,而是聽著他粗重的喘息聲,隨后,又趨于平靜。
他說:“幾個月前,我差點死了。”
“怎么回事?”我問。
“吃了半瓶子安眠藥。”
“啊?”我對此感到驚訝,但又一想,他現在好好地再跟我講話,應該沒有生命危險了。 “后來呢?”
“樓上的小孩給我送醫院了。”
“瞎鬧!”我有些生氣,心想這人怎么還是不懂事,多少道理我都講過給他聽,他根本不能自己從一種悲傷的情緒中解脫出來。我又開始為他擔心了。
“根本沒有人關心我,沒有!我死了也沒有人知道!”他又開始大喊大叫。
“那這樣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么了,只有你自己走出來,才能擺脫。”
“你不用再講大道理給我聽,你把琴借我吧,借我吧!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他忽然嗚嗚地哭起來,邊哭邊喊著,“借給我吧,求求你了!”
我越聽心里越害怕。我從沒遇到過這樣的人。我同情他,心里卻很煩。我不知道怎么解開這個結!
慌亂中,我一下子掛了電話……
整晚上,我的心一直在劇烈地跳動。他現在心里肯定在想,沒有人愿意幫助他,沒有人理解他,沒有人關心這個世界上是不是還有他這個人活著。一瞬間,那年夏天的情景在我眼前清晰起來:下雨的街口,藍鵬從遠處走過來,面無表情,走到我面前的時候,一下緊緊地抱住我……
我從未問過藍鵬的生活細節。我只知道,他完全不懂得自食其力,不懂得依靠自己,不懂得愛自己。他就像暴風雨中的小鳥,渾身都淋濕了,卻無處可藏。
后來,我又失去了藍鵬的消息,我也沒有主動和他聯系過。去年春節的時候問另一個朋友,那個人告訴我說,前幾天還看見藍鵬了,還是老樣子。
我想著,他始終都會是那個老樣子了。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