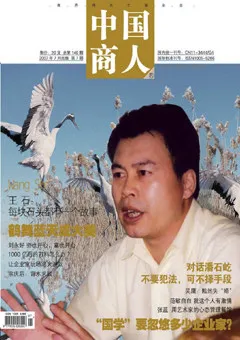1000億后的萬科怎么辦?
在中國的迅速發展過程中,萬科作為一個開發商在城市化發展中也得到了長足發展。中國在城市建設當中,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出現了爛尾樓等問題,但是這兩年都沒有了。
為什么呢?不是說發展商的道德水準提高了,而是現在城市發展對住宅的需求非常的旺盛,所以爛尾樓什么的就沒有了,由于住宅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建筑行業的事業發展非常好,所以也不會發生欠民工錢等問題。
1000億后的萬科怎么辦?
萬科作為一個上市公司發展非常快,我記得在2004年的時候萬科做過一個十年規劃,就是從2005年到2014年萬科發展到什么地步的規劃,在2004年萬科的規模是73億,當時規劃到2014年發展到1000億。
大家都非常得好奇萬科怎么發展到這一步?我們說是按30%的遞增得出來的結果,在過去六年當中,萬科的增長是36%,在未來十年當中不是按36%而是按30%,因為數字基數大了不可能這么快。
然而在這兩年發展的速度比我們預計得快得多,我們預計是30%,但是實際的增長率是超過50%,比如說去年超過200億達到213億,根據今天的情況估計要超過400億,這就帶來這樣一個問題,就是1000億預計2010年就能達到。
我今天講的主題就要講我們1000億之后應該怎么辦?遇到什么問題?在住宅這么多年發展中,萬科一直嘗試保護自然生態,也就是怎么保持生態原貌。一般的情況都是把溝填平、山鏟平,但是萬科是尊重生態原貌,保護原生態。
比如在上海有一個項目叫做假日風景,那個區幾萬畝的城市新區都是農田,但是到現在我還想知道原來的農田怎么樣,只有在我們這里,當初的生態規劃中留下了一塊生態地,讓大家知道曾經是農田。
雖然當時留下來的地影響了整體的規劃,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反而成了提高住宅環境,提高產品質量的很好賣點,這是我們當初沒有想到的。
再一個是萬科作為給中產階級以上人群開發的,所以萬科在這一方面也從作為企業公民的角度拿出錢,當然也要通過董事會的批準,來解決低收入的廉租房,但是不是這樣就夠了呢?
我想來談一談就是萬科1000億之后也就是在三年之后要面臨哪些問題。我們面臨著幾大問題,現在建筑的生產效率和耗能方面是什么樣的狀態,我們以2006年為例,產值達到213億,這一年的鋼材損耗在正常使用之外,由于勞動使用率比較落后我們的損耗是2900噸,就是不應該損耗的量,我們的水泥損耗是600萬噸,生產污水500萬噸。
這是我們現在2006年生產造了35000套房子給社會帶來的負面代價。顯然如果我們這樣下去由現在的216億到1000億還繼續發展下去,顯然我們對社會上造成能源的浪費是極大的。
如果按照這樣的模式繼續發展下去,我們認為不但萬科的管理是進行不下去了,而且給社會上城市化將是一個災難。必須要改變現在的生產方式,走住宅產業化的道路。
萬科是一個非常粗放的企業
我們認為住宅產業化基本從三個層面來解決:第一,從管理的需求提高效果;第二,客戶價值,要大大提高住宅質量;第三,環境責任要節能、節水、節材、環保。
我們從效率來看,我們和日本的一個同行進行比較,這是日本的一家建筑公司,具有一百年以上的東京房地產開發商,比較的結果得出的結論是這樣的:
人員管理水平和效率。東京建屋的效率是萬科的2.5倍,比如說人均銷售,萬科目前是919萬,東京建屋是2291萬。人均管理項目,萬科一個項目只是東京建屋的1/20,雖然增長很快,但是卻是非常粗放的。這就是我們和工業發達國家的差別。
而生產方式的差距也是相當大的,比如說傳統的誤差是20毫米,而工業化是2毫米。更不要說環境的責任。建筑總能耗占社會總能耗的30%,其中83%是在使用過程中消耗的。
建節能住房、環保住房是當務之急,如果我們作為一個住宅開發商不再進行大量的推廣,而只是為了現在賣最好的價錢,能夠利潤最大化,顯然跟和諧社會、節能社會、友好社會是不相承的。
萬科2000年的時候希望建研究中心,我們向政府申請用地,規劃部門就有疑問,問開發商怎么來搞研究,最后申請的1萬平方米的用地就批了3000平方米。
到了2005年,我們建設研究中心地方不夠用了,就又建設了400畝,所以發展商真正去研究節能環保的時候,在政府規劃部門絕對是用一種半信半疑的眼光來看的。
2007年工業化占到萬科的比例是多少呢?很慚愧的說只有1%,這個項目也是在上海的。到了明年也不會很高,明年是3%,2009年是20%。
那我們再看一看下面的數字,就這20%看看給我們帶來的效益,節水、節能、節鋼材、節水泥的消耗可以看到,計算出來連我自己都不相信,按照萬科的規劃到2014年我們將達到80%。
我們相信按照美國和日本的市場來看,第一就是站在最前面的幾大開發商,占的市場比例一般不會超過25%,我們就算達到20%,如果萬科帶頭走必須要改變方式,必須要節能、必須要環保。
如果中國在2014年的時候都用工業化來生產,節能、節材是相當可觀。所以萬科在重新調整2014年的規劃,我們高達1000億之后怎么辦,我們必須要加快萬科發展,達到住宅產業化。
在這里也引發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市場突然成長起來,萬科發展起來了,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不僅僅從微觀的角度來看應該從更高的社會角度來認識自己的社會地位。
應該認識到你的能力有多大,你的責任就應該有多大,這種責任不僅僅是對你的職工,你的消費者,你的合作伙伴,你要從相關的利益者、從整個社會,從整個全球來思考自己處在什么樣的位置上。
當然,我相信中國的城市化不可能一直這樣持續下去,到某種程度也會停下來,所以城市的住宅發展也會萎縮在這個過程中,因為萬科已經非常明確地定位自己就是一個住宅開發商。
所以一些風險投資者在問我,你作為一個董事長作為一個戰略規劃者,是不是要考慮到住宅市場不再這么發達,在萎縮的時候還要考慮工業化?我的回答是即使有一天中國不需要住宅了,但是我要說的是最后一套住宅是由萬科來蓋的。
“海盜”萬科
2000年,萬科制定了命名為“海盜”的挖人行動。
中海成為“海盜行動”針對的對象:中海有嚴密的人才培養體系,它的許多優秀員工都是從最基層的工作做起,經過系列精細的產品制造培訓,對成本和流程有非常深的了解。在中海成長為中高級職員的,幾乎都是業內的佼佼者。萬科完全有理由對中海內地公司及香港公司的人才青睞有加。
隨著中海的預算人員、質量工程師、項目經理開始流向萬科,中海也開始覺察。通過雙方的人力資源系統交流,張一平代表孫總說:希望萬科不要繼續“挖”中海的人,否則雙方的友好關系就不容易繼續維持。
然而,包括中海一線公司副總級別的更多骨干依舊流向萬科。這使得孫總感到惱火,發紅頭文件至萬科:鑒于萬科的不友好行為,斷絕兩家公司的關系。
2002年,中海進行業務從香港向內地轉移的戰略調整。與此同時,萬科人力資源部密切注視中海的動向,或許,這里可能蘊藏著中海管理層中高級管理人員離開的可能性。
可以說,孫總在中海擁有相當具有說服力的權威,高層也處于相當穩定的狀態,并不為萬科的“海盜”行動所撼動。此時,孫總上調中建總公司,而接任孫文杰的孔總在調兵內地的戰略轉移中,無疑面臨著是啟用深圳中海公司班底或者香港總部班底的選擇。如果啟用香港的班底,深圳中海公司的班底就不免流失。
當孔總啟用香港總部的管理團隊時,萬科掌握到:中海深圳公司總經理劉愛明萌發離開中海的念頭。
萬科通過關系同劉愛明取得聯系。通過人力資源總監解凍安排,我在一家酒店會所同劉愛明見面,正式邀請其加盟萬科。
不久,我在歐洲考察。突然接到解凍的電話,建議我即刻給劉愛明去個電話。
“等回到國內再打行嗎?”
“在國外電話的效果才明顯。郁亮剛和他談了一次。”
“啊,是這樣。”
原來,解凍了解到深圳一家民營房地產企業為劉愛明開出人民幣200萬元的年薪,另配住宅和專車。解凍建議給劉愛明一次性補貼,以抵消那家民營企業的優厚條件。
當公司提出這樣的想法時,劉愛明卻清楚地表示:“如果考慮離開中海,萬科是第一選擇,我并不會為私營企業的高薪所動。既然選擇萬科,就按萬科的工資體系辦,該拿多少就是多少。不要為我打破原有的制度。”
果然是中海培養出來的干部,不僅具有職業精神,也有高級管理人員的氣度胸懷。人力資源部建議劉愛明任集團副總經理。
總部征求意見到萬科深圳公司管理層,遭到反彈:“劉愛明領導的深圳中海是萬科的競爭對手,真槍真刀比拼多年,又不是競爭不過,憑什么讓他過來當我們的領導呢?”
我又親自到深圳公司做解釋說服工作。
幾番努力,2002年下半年,劉愛明加入萬科,任集團副總經理,后負責集團運營線及北京區域業務,現負責上海區域業務。
無論是“海盜行動”的成果,還是萬科高層的管理者,這里所講述的僅僅是萬科職業經理人隊伍的頂端一角。在激烈的市場競爭面前,萬科需要的是眾志成城,需要的是每一位職員都能夠充分發揮合作、進取、創新的精神。惟此,萬科才稱得上是一支能戰斗的團隊,一支充滿希望的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