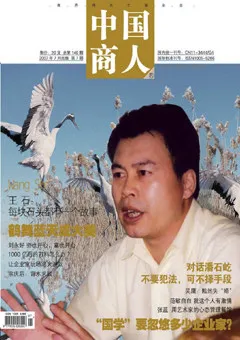華為崛起與“國學”有多大關系?

對“圣人們”一崇拜,濫觴就不可避免
數千年的歷史中,中國的傳統是以榜樣的力量來維系的。
榜樣中最高的勞動模范是圣人,圣人之上,則還有真人、天人等等。
孔子,以及孔子以前的皇帝、堯、舜、禹、湯、周武王都是圣人。
這個圣人譜系是很有趣的,如果國家可以被當作企業,思想文化可以被當作產業,那么皇帝、堯、舜、禹、湯、周武王都是創建了“特大型企業”的“既得利益者”,孔子則是創建了儒家文化產業集團的“成功人士”。
孔子之后,成功人士大有人在,圣人卻再也看不到了,這是一大歷史疑團。
孔子其人的成功是遵循“托古改制”的思路,靠著宣揚“仁義”,把皇帝、堯、舜、禹、湯、周武王這些獲得政治權威的大老板們尊為圣人而成功的。
孔子如此行為,孔子以后的學者們亦如此因襲,乃是因為普通人類有個心理,他們崇拜權威、仰視成功者,他們的話總是有人聽。
成功之后的孔子,被自己的徒子徒孫們綁架為思想文化界的權威,中國的國學傳統由此而在漢以后失去了自由交流、百花齊放的可能性。
在這樣的國學傳統里,鮮有人追問:皇帝何以會將權位禪讓于堯,堯又如何讓位于舜、湯如何取得權力的歷史真相,禹如何隱忍很多年后逼死舜,自己做了大皇帝,而周武王又是如何以臣子的身份背叛了君主,殺人盈野,最后獲得了最高統治權的暴力之路更少人過問。
如此,在“為尊者諱”的“國學傳統”指導下,中國的歷史一直是一部浪費自然資源、社會資源,浪費生命資源、浪費文化成果的歷史,西方的“國學傳統”也沒有導致什么好結果,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最好的明證。
然而,盡管東方的、西方的國學傳統并沒有給全球企業家在商業傳統、商業制度和商業倫理上帶來多少有益的推進作用,但是對于“圣人們”的崇拜一經形成,對于成功人士及其事業的隨意解釋、自由發揮、附會穿鑿的濫觴就不可避免。
由于這種群眾無意識和精英階層有意識操作下的全球性濫觴的勢能和傳染作用,甚至成功人士自己也被搞得云里霧里,漸漸無從理性看待本人以及其事業的成功,更遑論營造一種具有教育和引導作用的文化了。
你看看華為的“狼”害了多少人
在國學沉渣泛起的時刻,我們重點看看中國高科技企業一個最優秀的勞動模范——華為的崛起究竟跟“國學”有多大的關系。
提起華為,人們不能不不想起《華為的冬天》和“狼”。但是2000年以后,任正非很少再提及他鐘愛的狼了,因為一條離開狼群的小狼79jdGo3aXC5hkjVxOj7RqA==——港灣,正在向華為發起殘酷的挑戰,它的“頭狼”正是一度被視為華為接班人,也被任正非當作兒子來看的李一男。雙方殘酷撕咬到2006年,小狼重新歸隊,李一男重回華為,一切才風平浪靜。
這是華為“狼文化”導致的一個最典型以及災難性的后果。“狼文化”造成的后遺癥和綜合癥并不僅僅是“小狼與大狼”的決斗,華為什么時候不能淡漠掉“狼文化”的痕跡與色彩,它就會成為長期困擾華為的毀滅性力量。
如今回過頭來看,華為的崛起首先從精神上和國學沒有任何關系,因為中國的文化精神不具備土狼那么強烈的血腥性格、侵略精神和團結精神。同時,將華為的文化簡單地總結為“狼文化”,或許在企業處于成長時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他所帶來的麻煩,任正非本人最清楚。
其次,華為的崛起從其行為模式上也和中國的國學沒有關系。從1988年幾個人2萬元的家底開始,不到20年的時間,成長為一家世界級的高科技企業,任正非本人也和比爾·蓋茨、史蒂夫·喬布斯等全球IT巨頭出現在美國《時代周刊》“2005年度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人”的名單中。華為依靠的是從事至終在自主核心技術研發的執著,和國際化品牌與市場競爭中的強勢突擊精神。
試問,華為的這種堅持和表現究竟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沖淡與調和有什么關系?如果牽強地理解,或許只有儒家弟子的經典之一《易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可以套用,問題是全球那么多比華為還要強勢的企業,不是都可以如此總結嗎,難道它們都受到了周易精神的熏陶?
1988年以來,華為在“頭狼”任正非的帶領下,愈挫愈勇,最終在第一個十年在國內成為強人,第二個十年在國際市場大出風頭。

一段時間,任正非曾經認為,這是“土狼精神”的成功。
土狼的嗅覺敏銳,風中雨中,無論多遠,哪里有肉它都嗅出味道,一但發現食物出現,隨即奮不顧身、群起而上。
這是任正非所欣賞的精神。然而,土狼畢竟是土狼,獸類畢竟是獸類,華為不惜血本堅持核心技術研發,想方設法突破國際市場的努力,分明不再是土狼而進化為一只“帶槍的土狼”,世界上有這樣為自己創造食物,通過與別人共享食物而贏得成功的“虎狼之師”嗎?
在被所謂“土狼精神”鼓舞下的華為迅速崛起,而由于無形中簡單化的“狼文化”,崛起的華為也在經受“狼”的困擾,2000年之后的那場小狼與老狼的漫長決斗,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案例。
華為的“狼文化”不僅給自身帶來積弊,也給一大批中國企業和企業家帶去流弊,任的崇拜者甚至包括楊元慶和周鴻一這樣的人物。
事實上,在中國企業中,所謂的“狼文化”不僅出現在大陸,更早出現在臺灣。臺灣的明基、鴻海都可以說是其中的代表性企業。只不過和華為比較,這些企業不是“帶槍的狼”,他們靠低廉成本為別人代工奪取市場份額。
“不帶槍的狼群”由于缺少“武裝力量”,它們在更高層面參與國際競爭中時是極其缺乏自信的,從而蛻變為一頭在野外徘徊不定的狼。
這一點,我們從中國狼群們在國際化并購中的案例可以看得很清楚,李焜耀的明基收購具有150多年的西門子,楊元慶帶領聯想不惜一切代價收購IBM PC,李東生率領TCL收購阿爾卡特與湯姆遜彩電,他們的初衷無一不是企圖借助被收購方的全球品牌價值和市場份額來確立自己的行業地位。
這場由明基、TCL和聯想幾乎不約而同在短時期內先后發起的跨國并購,曾經令世界為之震驚。然而其結果是,李昆耀已經稱認明基收購西門子慘敗,TCL對于阿爾卡特和湯姆遜彩電的收購案也遭遇挫折,聯想收購IBM PC的滋味如何,或許只有楊元慶自己最清楚。
“不帶槍的狼”們進入全球事業時是如此的境遇,“帶槍的狼”華為的遭遇也并不美妙,華為收購英國電信巨頭馬可尼,在印度投資建廠的計劃,均受到經濟民族主義保護勢力的阻撓,華為的前路并不全是凱歌。
事實上,華為之所以受到國內企業和企業家的敬重,是因為它在自主科技研發和國際化拓展方面作出了成功的探索,而華為要真正進化為一家世界級別的企業,它的文化精神和經營理念,還必須能夠得到所在國家和地區的認同和敬重——華為的進化,其要害在于其核心價值觀的進化。
這不僅是華為的歷史任務,也是有志于向世界級企業奮斗的中國企業的歷史任務,“狼文化”不能幫助今天的華為及其效仿者,當他們試圖在國際市場建立自己的正面形象和影響力的時候,“華人文化”對他們的幫助也是有限的,有時候反可能還會帶來相反的效果。同樣,“民族企業”這樣的口號也許對中國人有號召力,但是不一定對購買了華為股份的中國以及國際投資者具有同等的號召力——首先,一家“民族的”、“如狼似虎”的外來競爭者對任何國家和地區的對手都會帶來精神壓力;其次,所有的投資者都不會對“民族的”或者“狼文化”的企業保持長久的信心,無論這個企業的名稱叫做“華為”還是“微軟”。
圣人不死,大盜不止
就地球經濟的演變歷史和趨勢來看,經濟全球化一直是一個大的方向。今天的經濟全球化由于其資本、信息和技術的平民化特征可謂最接近“全球化”的狀態,但它并非第一次大規模的全球化。
經濟的發展為什么會造成全球化的趨勢?
這是由于其本質決定的,經濟活動中的經濟人(個體,以商人為代表)和經濟組織(企業)總是在尋求其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這種目標促使了對資源、資本、技術和人才的需求一再地超越既有的活動空間。
經濟和經濟組織的這種趨利性和進取性,決定了其在任何族群、國家和地區可以逐漸建立具備共同語言的商業制度、商業倫理和商業文化。
如果用“商業文化”來總體涵蓋經濟人和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造成的以上三種效果,那么這種商業文化本身具有全球性,具有對本族文化和傳統的叛逆性。
這就是為什么在中國歷史上會長期出現“重農抑商”的傳統,在歐美文化語境下也會出現此類思潮的原因。
在中國,商人長期以來地位是很低的,其處境甚至不如戲子和妓女,歷朝歷代的中國統治者,總是把商人群體作為壓制乃至消滅的對象。統治中國思想長達2000多年的儒家文化系統,其本質更是反對商業文化的。
在歐美語境下,老牌商業帝國英國是一個典型。英國的地理和自然特征,決定了它不能像中國一樣長期維持自己自足的經濟結構,它必須向外部世界尋求資源和財富。但即便在英國,對自由商業文化的狙擊也曾經是長期的傳統,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成果直接建立在他和重農主義經濟學派的斗爭基礎上。
擔心少數人控制大量財富,對多數人形成資本迫害,這是東西方文化系統共同的擔心。儒家文化鄙視商業和商人,基督教文化把商人和拜偶像者、文士等等列為需要防范的幾類人之中,也無非出于同樣的考慮。
然而一個顯見的事實說明,無論東方文化中的“大同世界”,還是西方文化系統中的“天國理想”,離開經濟的充分發展就會喪失起碼的物質基礎。
但是,經濟的力量并非萬能,更簡單地說,錢對人的作用終究不是萬能的,盡管有了足夠的錢,幾乎可以買來一切。
經濟充其量只能解決人類生存的物質基礎,而人類生活的幸福指數和精神需求只有依靠政治和文化的力量得到改善。
比如,商人的努力可以使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進而他們可以奪取更多的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但是任何國家和社會都可以通過多數人的政治與文化的合力來對少數人的財富進行合理合法的分割,鼓勵大量中產階級出現,鼓勵慈善事業,利用稅收手段調財富分配都是有效的辦法。
因此,當我們參考經濟、文化、政治在歷史和現實中的種種博弈,來分析商業文化大題目下——企業文化——這個小題目的時候,我們將會發現種種的悖謬和不自量力。
首先,一個經濟人和經濟組織無法承擔人類的終極關懷和終極價值。
有無數的中國醫藥、保健品企業以及醫療機構,總是通過公共媒體把自己打扮成救苦救難的活菩薩,乃至于“救世主”的形象,但是,中國人目前蒙受的醫療苦難恐怕是全人類最慘重的之一;
其次,一個經濟人和經濟組織無法承擔族群大義,特別是在今天的全球經濟背景下,當一個經濟組織發展到一定規模,比如一個企業上市后,它的投資者可能是全世界的有錢人甚至窮漢——他必須為自己的投資者負責。
有無數的中國企業,動輒把自己打扮成“民族產業”的代表,實際上可能正在拖民族產業的后腿。當然,全球各國都會有“民族產業”和“本國利益”的訴求,但是如果一個企業能夠成為優秀的跨國企業,它同時就已經為民族產業和本國經濟作出了貢獻。這是無需辯論的問題。
再次,經濟人和經濟組織的趨利本性可能使他無法同時在人類公平和正義方面作出更多努力,因而,一個經濟人或者經濟組織過多吹噓自己在這方面的貢獻是徒勞的。
比如,全球各國都有販賣軍火的經濟組織,他們可能會賺取巨額的利潤,你能說他們做“殺人買賣”值得去大肆表揚嗎?
當然,出于各國和其族群的安全和防衛的需要,只能說這是一筆無奈的生意,而無法說它是正當的生意。
綜合以上的分析,對于目前的中國企業,如果不能不建立自己的文化,那么其文化的立足點起碼應該回避三個企圖:終極價值的體現者、民族希望的體現者、人類公平的體現者,更糟糕的是——竟然會成為“國學”和“某方文化”的發揚者。
因為它實際上做不到,無論中國的企業還是外國的企業,他首先應該做到的是:合法合理地發展,為社會提供更多更好的產品和服務,當它賺取了利潤的時候,及時給自己的投資者、自己的員工、給社會(通過照章納稅或者慈善事業)以應有的回報。
這是一個經濟人,一個經濟組織最起碼的義務,做到這一點,才算一個文明的經濟人或者經濟組織,其次,才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文化。否則,就算把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從全部請來也不能幫它建立可靠的“企業文化”。
更加反面的例子,就挑選最近的新聞列舉兩個:
山西、河北等地的黑磚窯可以說是中國最可怕的民營企業,它們的企業文化,只能總結為“絞肉機文化”,盡管山西曾經是黃帝(中國的圣人)的根據地之一,然而“圣人”的余光無法阻止野蠻和殘忍的上演。
最近還有欺騙了八家銀行,用數十億信貸資金去炒股的兩家“央企”,它們的企業文化又該如何來總結呢?
不知中國的國學大師們被請到這樣的企業去講課,能夠幫助其建立起什么樣的企業文化,也不必去猜測了。
照目前中國企業的普遍現狀來看,在更多企業還沒有普遍成為“遵紀守法”的文明企業前,企圖建立企業文化是奢侈的。當他們有條件有資格建設自己的企業文化時,恐怕也只能讓“國學”走開!
圣人不死,大盜不止。
(周向陽,副總經濟師,現供職于中國核工業集團陜西鈾濃縮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