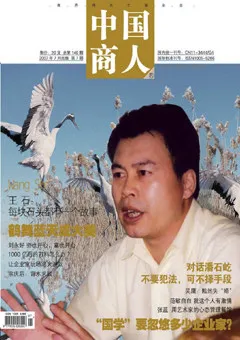從借來的380元到“心驚肉跳”的80萬

1981年至1988年之間,鄭志恩經歷了兩次至關重要的抉擇,也經受了人生中第一個八年獨立生存的考驗。
第一次抉擇是被迫的。鄭志恩出生在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兄妹四人,鄭排行老三。1981年,鄭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高中。此時有兩條路擺在這位17歲的少年面前,一條是“學而優則仕”,在國家免費教育框架下繼續苦讀,進入體制內的人生循環。盡管當時中國飽受文革的沖擊,但是通過考學或者參軍從農村進入城市,成為“國家的人”,仍然是底層民眾的最高理想。
另一條路是立即輟學,學得一技之長,養家糊口。這里有一個關于文革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狀況的誤會必須澄清:七十年代中后期,浙江的私營經濟已是春江水暖鴨先知,裁縫、木工、泥瓦工等手藝人開始吃香,短短幾年后,溫州著名的牛皮紙制作的冒牌皮鞋和大量的箱包已經涌向大江南北——新中國的民營經濟并非在1980年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萌芽的。
事實上,此時的鄭志恩毫無選擇的余地。他必須輟學,盡管那時上學不必掏太多的學費,貧困的家境卻使他無法享用這份“免費午餐”。
在父親安排下,鄭志恩拜一名裁縫為師,成了一名學徒。
學徒生活平淡而乏味,鄭志恩卻不敢等閑視之,因為這是他唯一求生存的機會。我們在這里不可能用過多筆墨描述鄭志恩當年是如何用一把大剪刀和家用縫紉機對付那些布料的。但由他此后的從業經歷,可以知道當年的小學徒并沒有浪費光陰。出師后的鄭志恩,進了當地一家相當紅火的鄉鎮企業——蕭山梅西服裝廠,由于頭腦靈活,做事嚴謹,沒過半年,就被提拔為分管技術的副廠長。
在依然論資排輩的社會里,一個19歲的年輕人能夠獲得副廠長職位,可謂空前的奇遇了,鄭志恩卻并不滿足于現狀。由于業績突出,他成為數家企業爭搶的管理人才。不久之后,鄭志恩出任梅西毛巾做營銷部經理,最后到上海藍天時裝廠蕭山分廠任廠長。
這是一個火箭般的升遷之路,然而在國營或者鄉鎮企業做高層的經驗,使鄭志恩不得不考慮人生中的另一次抉擇。促使他開始這些思考的根本原因,是個人與體制之間的沖突。鄭志恩的同僚都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在他們看來,鄭不拘一格的做事風格和思考問題的方法是稚嫩的,沒有經驗的。
“一個二十多歲的人,能明白多少事呢?”這是人們的普遍看法。
鄭志恩不這么認為。他發現,雙方的沖突并不在于究竟一個人的能力和他的年齡是否有成正比的關系,而在于:如果一個企業不幸做垮了,那些體制內的管理層換一個地方可以繼續干,而他鄭志恩還是一個赤手空拳的人。
1988年,鄭志恩最終選擇了走人。
四個人,兩臺家用縫紉機,一間租來的小小門面房,多方告借來的380元現金充當流動資金,這就是“蕭山藍天制衣有限公司”的全部家底。
如同暴風驟雨中的寒雀,小小的家庭作坊式的新生企業開張了,它許諾給員工每個月150塊工資,這是當地國家干部工資的兩倍多,是鄭志恩本人當廠長時月工資的將近四倍。它面對的競爭對手是那些社會資源和生產規模均比自己強大的國營企業、鄉鎮企業;它面臨的直接威脅是只要有一個月發不出工資,僅有的四名員工就可能開始流失。而一個不能贏得員工信任的企業還能有什么前途呢?
“訂單就是我們的飯碗。”大約在這時候,這句出現在今天藍天鶴舞新廠區的標語已經成為鄭志恩刻骨銘心的認識。
鄭志恩首先盯住的是仿制市場,當時呢子制服正在流行,一個人能穿上一件呢子衣服,就是莫大的榮耀。
他想在呢子服裝的加工和銷售上賭一把,然而這個年輕人缺少最起碼的“賭資”。他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沒有錢買布料。當時杭州的呢料是按筒來賣的,一筒五十米,售價1200多元,而鄭只有380元!
新廠開張的那一天夜里,鄭志恩懷揣著僅有的380塊錢,輾轉難眠:明天就要去買布料了,錢從哪里找呢?
起初他想到繼續去借,可該借的人都借了,時間也來不及啊。后來他又想到了去賒賬,可人家憑什么相信你呢?那個年代,是國營企業瞧不起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瞧不起個體戶啊!
怎么辦?怎么辦?
如此思來想去,一夜沒睡著。第二天一早,鄭志恩忽然有了辦法。他又從家里搜羅出二十塊錢,湊足整400元,騎上摩托車直奔杭州。
半個小時后,杭州百貨店的布匹營業員遇到了一個奇怪的年輕人,他提出一個離奇的交易形式。
“我這里有400元,全部給您,我今天只拿300元的布料。這一筒呢料我全要了,我想分四次買完。如果明天我不來,多出的100塊錢我就不要了!”
柜臺外面,鄭志恩在忐忑不安地游說著一臉愕然的營業員。
最后對方終于被打動了,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接受了他的提議。
又是半個小時后,藍天人為客戶量體裁衣,收取訂金,兩臺縫紉機全部開動。
第二天,鄭志恩依然是支付400元買回第二批布料。
第三天,買回第三批。
第四天……
如此周而復始,艱難滾動。慢慢地杭州百貨店認定了鄭志恩是一個講信用的人,他可以隨時去那里拿布料,為了直接服務蕭山的服裝企業,杭州百貨店甚至在蕭山設立了一家分店。
生產可以正常進行后,接著就是銷路問題。鄭志恩在浙江最大的服裝批發市場四季青租了一個最大的攤位定點銷售自己的呢子制服。下一步,他瞄準了中國的時尚之都上海。
第一次去上海,他帶了兩麻袋衣服,也不知道到那個市場去賣。正在躊躇中,一個意外的機緣幫了他的大忙。在去上海的公交車上,一個老先生遇到困難,鄭熱心地幫了他的忙,老先生非常感激。下車后,鄭志恩找了住處安頓好,第二天一早就帶著樣品趕到一家百貨商場,當他在跟營銷部的人交涉,請求銷售自己的衣服時,竟然再次遇見了這位老先生,原來他就是這家商場的負責人。
此時的鄭志恩,充其量只是一個個體戶,帶去的衣服也無所謂什么品牌。本來商場的人很為難,幸好有了老先生出面,他的衣服上了這家商場的柜臺。此后,老先生還幫他引薦了其他幾家商場的負責人。上海的市場就這樣打開了。
呢子制服之后,緊接著火起來的是皮衣。浙江當地的大小服裝企業一擁而上,紛紛開始仿制皮衣。鄭志恩也加入了這個市場的角逐。然而好景不長,由于生產皮衣的企業太多,導致局部市場供大于求,庫房里也出現了大量的存貨,而且越來越多。
市場經濟那只看不見的手,給什么時尚做什么,什么賺錢做什么,這給老是跟在別人后面跑的服裝企業提出一個教訓:一個企業不能光顧著生產,還必須解決銷售渠道問題,只有生產和銷售同時強勢,企業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為了徹底清理這批庫存,鄭志恩決定做大異地市場,采取了推銷、批發、專賣“一箭三雕”的銷售策略。
他首先派出業務員分赴杭州、寧波、上海等地成立辦事處推銷皮衣。
隨后,鄭志恩仔細考察了杭州、上海等地所有的服裝批發市場,最后選定了18家市場,每個市場選定一家可靠的商戶。這18家合作伙伴以成本價從藍天制制衣進貨,然后再批發給其他的零售商。
此外,鄭志恩還在海寧縣服裝市場租了一個攤位,每天早晨5點到9點批發給零售商。
當其他的企業還在為大量的庫存發愁時,僅僅一個半月的時間,鄭志恩卻把自己的庫存徹底清理掉,回籠了大量的資金。
這次走出去多渠道銷售初戰告捷,不僅使步履蹣跚的藍天鶴舞站穩了腳跟,對于如何做企業鄭志恩也有點恍然大悟了。此時,經過兩年半的經營,當初的380元已經變成了80萬,面對這沉甸甸的第一桶金,鄭志恩坦誠:“當時湊著錢就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