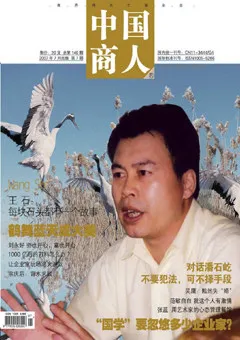長遠生財茂 發展利中祥

那時,長發祥的后面是作坊,如顧客需要在他們這里裁衣,后堂的裁縫脖子上掛著根皮尺,會聲音宏亮地跑出來招呼:老祖宗……
說老西安,不能沒有“長發祥”。
西安的“老字號”,遠沒有北京、天津那么多,也沒有湖廣和滬杭的“老字號”那么宏大氣派。西安有著“周秦漢唐”“十三朝古都”等諸多的輝煌標志和燦爛符號,但就是缺乏與其輝煌和燦爛同步同趨、同題同意的歷史遺存。西安是一個近乎“傳說”的城市。
透過古典的門板
一個人或者一個地方,我想只要它進入了“傳說”,就必然散放出某種氣息。這種氣息往往具有巫婆“放蠱”的作用,還有說書匠搖唇鼓舌“話說”出的境界,另外就是歷代帝王和圣賢根據自家需要,反復添加和刪改的一部部“史鑒”、“史稿”。如今的西安,沒有太多“老字號”,也沒有足夠古典的“老派”經營模式和營銷理念。我曾無數次地做過試驗:倘若從今天的《西安地圖》上抹去大雁塔和四角城樓,那么這座“千年帝都”立馬就會混同于中國的隨便哪一座城市。不論是海外游客還是國內的學者,他們傾注于西安的那種熱衷,只是在讀了許多和聽了許多關于西安的歷史故事之后,對自己從行為到精神的某種“放蠱”;在“放蠱”中陶然于唐風漢韻,陶醉于宮殿宮廷。歷史在西安是“空在”的破碎,完全依靠游客和研究者在心里彌補和縫合。
我曾經無數地做過另一個試驗:站在西安城南的樂游原上,俯瞰西安,一堆由鋼筋和水泥堆砌成的仿清仿明建構,一堆幾近破敗的磚頭和瓦片結構出“古典”。我在心里暗罵:這哪兒是典籍和傳說里的西安古都,簡直就是一座“磚瓦窯”。
這樣,我在尋訪老西安的時候,尤其重視依稀尚存的幾家“老字號”的研究。我想:它們是西安歷史的真實存在,是歷史的實在“遺存”;它們從觀念和形態、經營和規模等諸多方面,提供給我的是進入實在的“老西安”的古典形式的最好方式,也是唯一的方式。
我這里打開“長發祥”,像剝開桔子那樣綻放出它的香氣和令人饞涎的桔肉和桔汁。

從 “皇商”到“老字號”
在西安,如今依然有“大尺子的長發祥”、“仁義忠厚的長發祥”等等傳說。在這些傳說里,長發祥一次次地復活,并且在復活當中加深人們對故舊生活的思念。故舊生活,往往透過時間傳達給我們一種溫存、溫潤與溫暖,傳達給我們一種生活的自然亮度、生存的本真姿態和生意的確切含意。
長發祥是“長遠生財茂,發展利中祥”的縮意。至于這兩句老詩的來例,今無考。但是這兩句老詩卻實在是概括了“老派陜商”的商業經營特色,涵蓋了“老派陜商”那種“毛毛雨也能濕透衣裳”的持之一恒、不求速達的商業效益追求。長發祥,一個十足工穩的以經營呢絨綢緞、布匹綾羅的老字號的名稱;長發祥,一個時代的商業風度、營銷理念與商德商譽形象濃縮。
長發祥創建于光緒28年(公元1902年),原址在河南開封,開辦者是河南朱仙鎮的一個落榜秀才,名叫馮康瞿。關于馮康瞿我在朱仙鎮、開封以及西安的各史志、史料館里,沒有找到太多相關的資料。但是有一筆記載卻把馮康瞿與“長發祥”緊緊地連系在一起,并且賦于馮瞿康與長發祥某種“皇商”的意味。
馮康瞿是清王朝內閣大臣徐世昌的大表兄。進入民國,徐世昌出任過為期短暫的“民國代總統”,是個莫衷一是、眾說紛紜的人物。但是,徐世昌卻是一個地道的民族主義者,有濃郁的鄉土情結,倡導民族工業發展、呼吁“廢除科考”,推行“量材錄用”。在康、梁“變法”時期,徐世昌是最積極的支持者和擁護者。在徐世昌出任內閣大臣其間,他的大表兄馮康瞿在京城應試,這時馮康瞿41歲,徐世昌39歲。馮康瞿在數度“榜上無名”之后,心情郁悶地與表弟商量,打算回到家鄉,過“歸隱林泉”的生活,打算在家鄉“尋田問舍”,報效桑梓。這時一慣思想激進的徐世昌苦口相勸,勸馮康瞿回家鄉振興民族經濟,“背靠朝廷”,為家鄉父老做“衣被天下”的生意。
這樣,落榜秀才馮康瞿回到開封,在那里開辦了以經營呢絨綢緞、布匹桑麻為主的“長發齋”,網絡和結識了開封城里的各路神仙,以充沛的貨源和繁多的花色品種,確立了它與上流社會與大眾百姓的生活聯系。開業時間大約在光緒29年冬天,齋號的匾額出自徐世昌手筆。在清末及民國的種種傳說里,“長發齋”的最初資本都是由徐世昌“捐贈”的。馮康瞿本是一介書生,是“不善經營、無能理財”的一介書生,這樣馮康瞿回到家鄉朱仙鎮,請出遠房表弟丁竹青出任掌柜。
丁竹青是“長發齋”的第一任掌柜。丁竹青飽讀詩書,有著遠通近控、熟稔國政的諸多特點,他賦予創業階段的“長發齋”,一種“鄉幫”特點:“長發齋”開業之際,滿堂的領東、相公及雜役,均為來自朱仙鎮的本門族兄和遠房表親。事實證明,這種鄉幫化、家族化的管理方法,大力地推動了“長發齋”的發展,使其之后的“分號”聯銷聯營模式成為可能,為日后的飆升與發展奠定了令人信服的基礎。進入民國,尤其是在徐世昌出任“民國代總統”的短暫時期,長發齋一躍而起,先后在河南鄭州開設了“長發祥”、“義豐永”、“祥記”等三家字號。這時,丁竹青向股東馮康瞿提出告老還鄉,踏上了寂寞冷清的回鄉土路。這種“全身而退”賦于長發祥大旗之下的商業經營,一種接力與薪火相傳的意味。但是,丁竹青在離任之前,也給各字號里的領東和二掌柜留下了“無才不養金玉”的用人用賢規矩。這樣,“笤帚把出身”(也就是學徒出身)的第二任掌柜來式如開始領東長發祥,使長發祥再一次進入了騰飛階段。

來式如為人智慧,精通商略,為長發祥制訂了完備的經營方法,并使其方法制度化、標準化、規范化。在來式如領東期間,經歷了巨大的社會動蕩和數次的衰落和迂回。
在1934年隴海鐵路通抵西安之前,歷任陜西省主席都傾心地方經濟發展,提倡“招徠”、鼓蕩“陜商”走出去,啟發“陜幫”開胸懷。1928年,陜西省主席宋哲元先生就曾邀請過開封長發祥來陜經營。1933年陜西省主席楊虎城先生在火車即將通達西安的時候,再次面向全國,發出“招徠”吁請。可以說,長發祥是在積極地響應楊虎城先生的“招徠”政策的基礎上,前來陜西尋找機會的。至于當時楊虎城對各路商幫的承諾,那是過去了的那個時代的事情,是那個時代陜西各級長官對“振興陜西,扶助農桑”的拳拳之舉。馮玉祥主陜期間,也發表過近似于捶胸蹲足、捶頭打腦似的“萬民講話”。對陜商和陜幫的閉關自守、墨守成規等一系列陋習,提出了十分懇切的批評。
1940年,西安長發祥已擁有“十萬大洋“的積累,并先后擠垮了“老九章”“大綸”等同行同業,以其霸主姿態,領跑西安綢緞及布匹銷售行業。
1934年冬天,河南長發祥落定在西安竹笆市,開始了臨街商賣、惠顧城鄉的商品經營活動。原來河南的幾家長發祥旗下的字號,后來均在日寇鐵蹄之下,毀于戰火。1944年因西安商業經營中心東移,長發祥遂遷東大街現址。長發祥和它滿堂的河南籍商人,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難之后,陪著笑臉,傾情傾心地和陜商交流與融通,傳下一段段佳話。
1953年,長發祥領東來式如,積極響應社會主義對工商業者的改造,投身社會主義建設。
如今,長發祥是響名叮當的“老字號”。但“老字號”又是什么呢?是一塊閃閃放光的金字匾額嗎?是聲名顯赫的美聲美譽嗎?
都不是。“老字號”是一群人的滄桑蒼茫的人生故事,是一家企業沉浮與掙扎的歷史故實。
“日月滾金球”
1934冬天,一幫土衣土貌的河南籍商人,站在了西安城樓的下面。他們肯定沒有想過:這里是他們最后的歸宿,這里是他們的子子孫孫起根發苗的地方。那是一個民族面臨考驗的特殊年頭,軍閥混戰,經濟衰微,國政廢弛;街市上過往著什百為群的難民,過往著無以數計的傷兵兵痞、土匪強人。不難想見,長發祥領東來式如拜會各路“神仙”的情境:那時的西安城,有著太多的“山頭”,官商一家、官匪一家、官紳一家,城雖不大,但城里的每個角落都潛藏著足以使初來乍到的長發祥“閉門”與“關張”的這樣那樣的黑勢力、惡勢力。長發祥是如何面對陜幫陜商,是如何扎根百姓,是如何確立了在西安城的理想位置呢?
長發祥首先選擇的是忠厚忠誠的對待陜幫的態度,其次選擇了“顧客就是財神”的經營風度。另外,長發祥十分重視領東、掌柜以及相公的業務能力,培養出了一批“商賣場上”和“財貨行當”的經營高手和理財高手。
長發祥的店堂經營模式,不同于老派陜商在店堂里敬供行當祖師和“關二爺”(關公),長發祥在本應當是神龕的店堂沖門位置,長年設置著八仙桌,茶幾茶椅、炮臺煙、龍井茶,任城鄉顧客隨便享用。八仙桌的上面是品藍緞子上繡的五個斗大的金字:日月滾金球。透著和諧與融洽,透著俚俗與親切。
在老長發祥的門前,永遠都袖手站著捧著笑臉、穿著棉袍的二掌柜。長發祥二掌柜的笑臉,深深地扎根在每個老西安人的心里,成為長發祥的特色符號,使老西安人久久難以忘懷。這個二掌柜不只是簡單地迎來送往,他站在店門前,和往來的四鄉騾馬大車打招呼,和車上坐著的大姑娘、小媳婦打趣,給騎著驢來買嫁妝的新娘子拴驢,攙扶城鄉的那些小腳老太太,給坐在八仙桌邊的官紳富紳點煙鍋,另外,二掌柜甚至還給那些鄉下進城的大戶人家的“老祖宗”捶背。可以說,一個干凈漂亮的二掌柜,灑脫得就像一陣春風,制造出了“賓至如歸”的情境,然后才是掌柜的雙手低垂至膝的“請安”,相公目不斜視的“捧茶”和麻溜的一路小跑的幾個圓頭圓臉、睜目豁眼的相公娃的“捧樣”。那時的長發祥,顧客不用站在柜臺前選貨,只需要往八仙桌邊一坐,掌柜和相公娃就基本清楚了顧客的要求。在老長發祥,每個相公娃必須經過三年嚴格的學徒,學徒期間不能“頂生意”,只能掃地、抹案、捶背、端茶,其余時間才能跟著師傅學習“三準”基本功。所謂三準就是:眼準、手準、心準。在漫長的幾十年經營過程上,長發祥沒有發生過一例把綢緞撕“毛邊”的,更沒有過一例“缺尺短寸”的事故。相反,長發祥本著“舍小求大”的經營理念,長期實施“滿尺長寸”的營銷方式,也就是你買每一尺綢緞,我舍給你一寸。所以,長發祥在西安有著“大寸子的長發祥”商業美譽。
在長發祥,買賣成交之后,相公捧著賬單收款,那賬單是桃紅色的,透著喜氣,上面印著“吉祥富貴”,“萬事遂意”等吉祥話語。那時長發祥的后面是作坊,如顧客需要在他們這里裁衣,后堂的裁縫脖子上掛著根皮尺,會聲音宏亮地跑出來招呼:老祖宗,可把我想日踏了!(西安土話:你把我想死了的意思)然后才請安,躬身量體,等等。
另外,長發祥的“禮票”也是它商業推廣、擴大經營的重要手段。所謂“禮票”,就是凡有饋贈親友禮品者,可先在商店內賣好“禮票”,讓親友持票選樣拿貨。那時西安的各行各業,都有在年關上、喜慶時給朋友和員工散發長發祥“禮票”的講究。禮票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長發祥商德商譽的傳播方式和重要標志。
可以說,長發祥的經營思想里體現著一個重要的傳統情結,這就是舍得。
可以說,長發祥生動地理解了“長”對商業經營的作用,沒有“短、平、快”的對待商業活動,沒有急功近利的把商業活動處理成“一次性消費”。
長發祥奉行對顧客:一要敬好,二要周全,三要誠信無欺。所以,從1934年到1953年,長發祥始終是西安人民生活的朋友和顧問,深得城鄉人民的熱愛。
從“無才不養金玉”到“柜考”
從商是一種高級的人生經驗,它需要的元素遠比從政從文、從醫從工要復雜,而且復雜得多。一個優秀的商人,他的大腦要像化學實驗室的燒杯:耐酸耐堿耐火燒。他的手腳要像雜技演員: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他的表情要像政客一樣從容、要像演員一樣嫵媚、要像圣人一樣莊嚴。可以說,一個成功的商人,基本上就是一個孫悟空,不僅要有七十二變的能力,重要的是他賦予商業活動,某種德與品、智與靈,幾近賞心悅目的神仙境地。
來式如這個由“相公娃”、二掌柜一路成長起來的“領東”,在老掌柜丁竹青“無才不養金玉”的價值觀作用之下,榮登領東寶座,并繼承這個價值觀念,積極推行對相公的“柜考”制度,確保了長發祥的服務質量和員工素質。
店東認為,商賣要有成效,員工素質是首要的決定因素。所謂“無才不養金玉”,也就是沒有有本領、有德性的店員,商賣就得不到大的發展。在長發祥當三年學徒期間,不能上柜“頂生意”;學徒第一年,干雜活,抹案掃地,學規矩(放屁都要找個沒人的地方);學徒第二年,開始學卷布、折布、擺貨、捆扎、認貨;學徒第三年,學寫字、珠算、綢緞知識、應酬、行當秘語和待客語言。三年學徒期滿,要經過嚴格的“柜考”,柜考最殘酷的是要“闖四關”:一、讓學徒蒙上眼睛,用手感來鑒別毛、絲、棉、麻、葛、縐等產品及產地;二、不論顧客胖瘦高矮,要一口報準看體算料的數量;3、根據布料的幅面和顏色及尺寸,能隨意自如地報價、折壘和捆扎;4、學徒期滿,必須能夠算出所售布料的利潤,而且必須做到“一口清”。在老長發祥,商品標簽正面是銷售價,背面用密碼寫得有成本價,密碼用“長遠生財茂,日月滾金球”組成,每個字代表一個數碼。若能闖過四關,學徒才有“頂生意”的資格。老長發祥十分重視品行、禮儀、廉恥,以“寡廉鮮恥”與“枉口嚼舌”為相公人生的大忌。老長發祥的相公娃,一律不準吸煙、不準喝酒、不準賭博、不準和不三不四的男女來往,甚至上柜臺時身上都不允許揣錢。老長發祥還有一條鐵律:親友和熟人來買布,要讓其他相公接待。長發祥的相公都很懂規矩,模樣也都周正,很得城里城外太太、姨太、小姐、丫環的喜愛。那時,許多太太小姐,不買布也經常到長發祥逛一逛,轉一轉,忽閃著眼睛,上上下下打量著店里的一個個憨頭瓷腦的相公娃,在內心里縱情暢美。
另外,長發祥在經營理財方面,也有自己的道行,它的商品幾乎無一不是蘇、杭、川、廣廠家的最新貨色。1944年,長發祥在全國各地駐有16個“莊客“,所謂“莊客”其實就是采購員。這些“莊客”都是相公出身,有著超人的對綢緞及布匹布料的認識與判斷,并能夠就綢緞與布匹的顏色與花樣,做出流行與否的準確判斷。長發祥一慣堅持“源頭進貨”的原則,從不在“批頭莊”(轉手轉賣及批發市場)進貨,確保了商品的品質,同時降低了成本。
另外,長發祥在老西安是尤其重視品牌宣傳的企業。每到年關,長發祥大肆宣傳,雇來鼓樂隊,吹吹打打、沿街號叫,并向路人饋贈手帕、香胰子、雪花膏,以此擴大影響、以廣招徠。來式如領東有句商業名言:貨不壓柜利自生,錢不存柜利自來。為此,長發祥在30年代和40年代,經常舉行“拍賣活動”,推銷積壓貨。從利益最大化考慮,長發祥在40年代抗戰期間物價暴跌、生意蕭條,許多商家瀕于破產之際,別出心裁地投資于“行商”(游商),采取“賒銷”給無業“貨郎”的方法,解決了無數逃難流民的生活,并積極推動了長發祥在“亂世年代”的穩步發展。昨天還有老人給我說:1947年,西安街上的貨郎比現在街上賣《華商報》的報童還多,賣得都是長發祥的貨色。
現在的長發祥是位居鬧市中心的一幢九層高的商業大廈。名字還叫長發祥,還經營綢緞緞和布匹,但已混同于金碧輝煌和富麗堂皇的許多“商廈”和“購物廣場”,找不到它歷史的遺韻和魅人的絕響。
想起長發祥,我的耳邊立馬回蕩起了那遠逝的市聲和市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