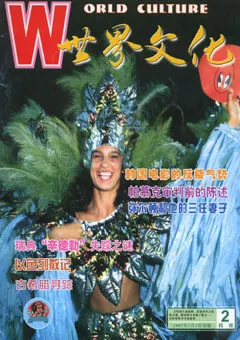韓國電影的反叛氣勢
將近一個世紀以來,好萊塢以強勁的勢頭橫掃了整個世界電影市場。面對好萊塢的“氣勢洶涌”,素有“藝術電影基地”的歐洲也無力回駁,尤其是亞洲電影長期處在一種在夾縫中求生存的狀態中。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第五代”導演脫穎而出,以歷史敘事作為對現實發言的方式以及以語言的陌生化方式,構成對好萊塢“權力話語”的顛覆,成為特定而短暫的歷史契機所造就的文化奇跡。而到了90年代,韓國電影以其異軍突起的氣勢取代了中國的歷史寓言敘述,成就了別樣的亞洲電影景觀,并成為亞洲乃至世界影壇的一支主力軍。
據不完全統計,“韓國國產電影占本土電影份額在1998年是25.1%,到1999年所占份額為39.7%,到2002年幾乎占本土電影市場的一半,并于2003年首次超過50%達到53%”,從1999年到2003年,5年的票房冠軍均為韓國國產電影(依次為《生死諜變》、《共同警備區》、《朋友》、《家門榮譽》、《殺人回憶》)。2004年的《實尾島風云》與《太極旗飄揚》更是氣可吞天,上映不久就突破了1000萬觀眾大關。值得注意的是,在如萬花筒般折射出豐富的高麗文化的韓國電影中,自1999年以來,相繼出現了《生死謀變》、《共同警備區》、《實尾島風云》以及《太極旗飄揚》等政治題材商業化大片。其中,《生死諜變》以550萬觀眾人次打破了當時橫掃世界影壇的《泰坦尼克號》的記錄并贏得當年電影票房冠軍;《共同警備區》入選柏林電影節,并奪得2001年法國多佛亞洲電影節大獎;《太極旗飄揚》在2005年韓國第25屆青龍電影節上一并卷走包括最佳男主角、最佳攝影、最佳技術和最佳票房等多個獎項,而《實尾島風云》奪走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兩個大獎。這種致力于政治題材商業化的影片目前已成為韓國電影的一道亮麗別樣的風景線。
走出禁區的政治題材
用“百無禁忌”來形容韓國電影的創作自由度和創作思想觀念是最恰當不過了。禁忌好似太陽下的陰影,自電影成為沖破地平線的旭日開始,禁忌便如影隨形了。韓國電影界具有那種沖破禁忌的反叛氣勢,這當然跟韓國現行的各種制度是分不開的。
韓國電影在90年代以前長期處在一種低迷狀態中,并受于日本的管制之下。在1984年韓國電影市場全面開放,尤其是1986年政府被迫采用的“自由化”電影政策,使原本由舊電影法保護的20多家電影公司獨占國內電影市場的局面被打破,產生了一百多家規模小卻靈活多變的電影公司,但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仍然嚴重的制約著韓國電影的發展與創新,在遵從舊的審查制度前提下,乏味無趣的電影題材、蒼白無力的電影思想、平淡庸俗的電影畫面充斥著整個韓國電影市場,結果是韓國電影依然無力抵御好萊塢等外來電影。因為“在藝術中起決定作用的,開拓通向觀眾道路的是藝術家的目光、思想和靈魂,而不是技術材料或其他因素”。然而,在1996年,韓國宣布電影公映倫理委員會的審查違反憲法,結束了延續多年的電影審查制度,這為韓國電影提供了較為寬廣的題材空間和表現空間,于是,在韓國電影界出現了“百無禁忌”的繁華景象。譬如《兩個警察》系列揭露的是警察的違法勾當;而《美麗青年金太一》批判了上個世紀70年代的軍事獨裁體制;《花瓣》揭露的是80年代遭到鎮壓的“光州事件”。
在“百無禁忌”的創作狀態下,韓國電影剛正不阿的對于傳統的歷史視野進行糾正,開始致力于一種民族主義的訴求,一種對高麗文化的反思和探索,對歷史和政治的矛盾進行定位,“真正的民族電影應該是吸取民族文化精神的精髓,植根于民族現實的土壤,用一種積淀了民族審美經驗和感情的藝術形式去關懷民族和這個民族的各個個體的生存、發展、進步”。韓國電影人正是深切的明白這個道理,并親身體會到了韓國這個國家的獨特:作為一個幅員有限的半島國家,其狹小自然環境、備受欺凌的歷史、尤其與同一民族的朝鮮因歷史原因制度不同而產生的政策差異等,其中,南北民族分裂的苦痛宛如一把利劍深深的刺在高麗人心中,并成為韓國的獨特民族心理和民族氣質。于是,對于半島歷史和未來的思考,對歷史厚度的描繪與對戰爭的反思,都凝聚在這類政治題材商業化影片的民族情感中,揭開歷史塵封已久的檔案,從歷史和人性的角度出發質疑長期的分裂和敵視,描敘“三八線”的存在給朝鮮半島和她的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痛苦。
故事是加工了的生活素材,“新的電影素材應該去挖掘,而不是去編造”。這類影片的題材大都取自一個因民族分裂所發生的真實的事件,而后,經過藝術加工便成為今天這一個個動人心弦的故事。《實尾島風云》就是取自于1971年8月23日發生在漢城的“實尾島暴動事件”,通過對那群死囚部隊的建立與毀滅以及其表現出對國家、對民族的崇敬和熱愛,對家人、對朋友的情義,從而對黑暗勢力進行了強烈的諷刺和批判,對壓抑人性、毀滅人性的做法表現出強烈的不滿和譴責。那野性殘酷的孤島生活,森林里的搏斗,沙灘上鐵絲網上毫無人性的集訓,人們的無奈與迷茫、團結與背叛,無不震撼人心,表現出濃厚的人性啟示。在《共同警備區》中,原本屬于兩個不同國家、不同意識形態的四個人卻萌發出令人敬佩的友誼,兄弟之情,其實這正是韓國跟朝鮮原本是兄弟的象征!愛恨糾纏,信任與猜忌,50年分裂的苦痛與血脈相連的統一愿望同時扎根于他們的內心深處,四個人的交往有誤會也有融合,有隔閡也有理解,但不變的是骨肉相連的兄弟之情。勇闖禁區,面對苦難的歷史和殘酷的現實,不避血腥、不畏陰暗、不懼疼痛,將歷史最真實的一面毫無忌憚的展示在我們面前,讓我們感覺到了導演那堅硬強悍的神經,敢于正視歷史和現實的疼痛和污穢,恰逢其時地刺中了當下現實中人們的心理特征和要求統一的愿望,在主題及題材選擇上具有相當普遍的社會意義,矛頭直指國家政治、社會民族等敏感領域。
“電影產生于意識形態,同時也作用于意識形態”。作為反映社會意識形態的電影,作為表達創作者的創作思想和創作主旨的電影,韓國確實做到了“百無禁忌”,表達了絕大多數觀眾的意愿和思想,并通過激活膠片上的質感和色彩準確記錄歷史和現實顯為人知的一種人性心理與生存狀態。
藝術和商業的雙重成功
自從愛森斯坦首次明確提出“電影是一種企業”,藝術和商業就似乎成為電影兩種不可兼得的矛盾對立面,如何將藝術和商業進行有效的平衡成為電影創作界、電影理論界爭論不休和探討的話題。馬爾丹說:“對于電影來說,真正嚴重的影響它的其實是它的商業性。”而賈克·瓦倫堤卻說:“電影制作是藝術和商業的聯姻。”藝術與商業兩者都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不應該厚此薄彼,而韓國電影在這點上相對來說做得比較成功,無論是表現愛情的唯美抒情影片(郭在容的《愛有天意》與《俄的野蠻女友》、許秦豪的《春逝》與《外出》等等)還是致力于表現小人物生存狀態的低成本小制作影片(金基德的《漂流浴室》與《撒瑪利婭少女》、李滄東的《綠洲》與《薄荷糖》),或政治題材影片,從其國內獲得的高票房以及在國際上獲得的一系列獎項就可以充分證明。尤其是其政治題材的影片,對歷史的沉重和現實的殘酷進行了審視和挖掘,盡量表達出其對社會狀況的敏銳洞察和思索,由對民族分裂苦痛的呈現上升到對歷史現狀和人性的反思,這種具有哲理思辨和人生寓意的主題,都是在商業化制作和銷售等包裝下完成的。
在全球化勢不可擋的今天,第三世界有些國家導演往往傾向于用西方“他者”的眼光作為創作目標,試圖按照西方人的視野來展示一個具有異國情調的東方,甚至有時為了滿足西方社會那種獵奇心理而偽造民俗,在虛構和變形中構成“歷史的虛假性”。當然,這與第三世界國家在后殖民語境下,作為亞文化要求獲得西方主流文化的承認是分不開的。因為在西方世界所形成的強大的話語支配領地中,第三世界的文化知識不能不屈就在邊緣地帶的地位,無法取得與西方話語平等的合法性,結果是第三世界在構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歷史時候承受著深深的無力感,然而,韓國作為亞洲國家卻很完整的保持著個性而不被西方所牽引,韓國電影因之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甚至已經成為展現韓國民族和高麗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韓國電影善于運用本土化策略“以小博大”,致力于對本國民族性不遺余力的挖掘和表現,并銳意展現本國獨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需求,擺脫好萊塢式的題材雷同化和工業流水線的標準化制作的桎梏,樹立起本國獨特的電影風景。姜帝奎的《太極旗飄揚》描寫的是南北戰爭中一對親兄弟在無意中被抓去當兵,哥哥為弟弟早日回家而義無返顧的沖向戰爭前線而弟弟因擔心哥哥安危試圖阻止哥哥,這種在對立行為中產生了無奈、悲哀的誤會,于是由浩大的南北戰爭置換為兄弟之間的關乎前進與阻止間的矛盾,以及由此體現出的那種血脈相連的親情,對民族分裂給普通人帶來的深沉的苦痛。鎮泰與鎮錫這對兄弟原本應該生活在幸福之中,卻被置身于殘酷的戰場上,這是命運的捉弄還是歷史的誤區?導演在詢問,觀眾也在詢問,但無論如何我們都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兄弟兩人從相依為命并肩作戰,到反目成仇相互刺殺,這種兄弟戰爭才夠殘酷,夠震撼人心,而鎮泰從反對戰爭到瘋狂殺戮,從對戰爭絕望到最后一剎那的人性復蘇,其中所呈現的人性異化變換歷程和戰爭分裂的后果,帶給觀眾空前震撼的悲劇力量。韓國的歷史應該是比較獨特的,從過去一個和睦友好的統一民族分裂成今天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南韓與北朝鮮,從一個落后的并受盡歷史屈辱的農業國家變成今天先進的工業文明國度,在這段歷史里,韓國社會意識觀念是怎樣的?韓國民眾的民族心態又發生了那些變化?不平凡的歷史給今天物質富裕的人們又帶來了哪些影響?而這正是韓國電影目前所要致力描繪的,這就是韓國的本土文化根基所在,事實證明,韓國確實成功地做到了。《生死諜變》中相愛的人卻要刀槍相對;《共同警備區》中友好的朋友在面對面時卻要裝做互不相識,最后這段感情被人給殘忍的扼殺了。
其次表現在商業上。一是韓國將“拿來主義”與“抄遍百家”運用得嫻熟自如,爐火純青。其實這并不與創新相背離,就如同蜜蜂采集百花一樣,在最后釀成自成一家的獨特甜蜜。天才導演威爾·奧爾遜在仔細研究日本導演黑澤明的《羅生門》后,受其獨特的敘事手法啟示而創作出代表現代電影開端的《公民凱恩》,但我們誰也不會說奧爾遜缺乏創新,而抄襲黑澤明的影片。韓國電影在開始“拿來”式創新之后,便形成了自成一家的各色電影,其中就包括政治題材商業化電影。康佑碩的《實尾島風云》就是靠一樁歷史疑案來滿足人們的獵奇心理,類似于好萊塢經典影片《刺殺肯尼迪》(對當年美國總統肯尼迪被暗殺的事實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索,由此揭露了美國司法部門的黑暗以及對美國政客爭權奪利的復雜與黑暗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切中了民族分裂這個既定的現實,表現了一種屬于那些生活在朝鮮半島上背負著民族分裂歷史包袱的人們特有的歷史悲情。而《太極旗飄揚》采用了與《拯救大兵瑞恩》、《野戰排》、《現代啟示錄》等好萊塢經典戰爭大片頗為相似的敘事模式以及類似的戰爭大場面,如巨資構建的外景地,大場面調度,槍林彈雨的激戰,血腥的戰場,大量晃動不定、構圖不規則的手持攝像的運動鏡頭等等,給觀眾以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呈現出一種奇觀化場面,并將波瀾壯闊的戰爭場面與感人肺腑的感情描繪和人性刻畫相結合,體現出一種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以及對歷史的厚重審視和戰爭的深沉反思。
二是類型的雜糅性和多元性,將引發觀影欲望的眾多商業片類型元素融合到一起,這樣就保證了影片在諸多層面上融及觀眾的神經,吸引觀眾的眼球。“類型是可以非常具有伸縮性的,有彈性的”,如把動作暴力元素、言情、喜劇、懸疑等諸多元素融合在一部影片里,具有極大的觀賞性。《生死諜變》的成功就在于由朝鮮半島南北分裂的真實事件改編而成,并具有新穎性和敏感性。俊男美女的纏綿悱惻的愛恨情仇,節奏強勁動感十足的槍戰搏斗場面,以及情節發展的懸疑神秘感等等這些類型元素的完美融合,具有極強的視覺沖擊力和情感感染力。同樣,《共同警備區》也把偵探懸疑元素加了進去,我們誰都想知道這樁疑點重重、撲朔迷離的懸案的真相到底是怎樣的,為什么當事人韓國土長李秀赫與朝鮮被襲方唯一幸存者吳敬必中士在遞交的調查書上對同一事件作出了不同的描述?對真相的好奇欲望促使觀眾用心的去看,在觀看過程中,觀眾感受著導演對于事實真相描述的悲哀與苦痛,因為創作者們并不是為了娛樂而娛樂,并不是為了商業而商業,而是盡力在商業的包裝下融入歷史社會的分析以及人性的思考。
其實,藝術多一點或是商業多一點并不重要,只要影片能反映出創作者的創作思想與創作主旨,以何面目示人又有什么關系呢?中國導演路學長說得好“我特別怕提藝術片與商業片的區別。我覺得一部好的電影,不管它是哪種類型的,只要是發自內心的表達你對生活的真實感受,你對生活的誠實態度,這才是最關鍵的。而韓國的政治題材商業化影片正好引證了路學長導演的這個觀點,該類型電影遵循了經典借鑒+藝術創新+商業運作這個創作模式,并已經演練為經典成功的模式,解決了商業性與藝術性平衡這個難題,以藝術家的眼光和角度對素材進行選擇與加工,對題材思想的表達方式進行探索,又以商人的感覺和思維出發進行包裝,盡可能迎合觀眾需求,以此獲得藝術和商業的雙重成功。
“今天的電影已久不再是語言和演出,而變成風格和思考。”韓國政治題材商業化電影正是因為具有獨特的風格和深沉的思考而成為韓國電影里的一朵璀璨的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