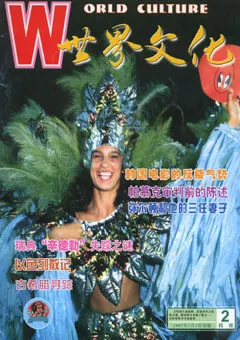以色列散記
難以評述的“隔離墻”
1998年5月,以色列前總理內塔尼亞胡訪華期間,面對長城感慨地說:“以色列也需要這樣巨大的墻來保障它的人民的安全。”當時,站在他身旁的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回答說:“能給以色列人真正安全保障的是和平,而不是混凝土墻。”
然而,以色列的領導人卻并未聽取朱總理的勸告,2002年6月沙龍領導的以色列內閣以25票贊成,1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修建“隔離墻”的計劃。那投唯一的一張反對票的是工黨領袖佩雷斯。其實,最早提出修建“隔離墻”方案的卻是以色列工黨。他們建議沿1967年“六五戰爭”前的分界線,即國際上公認的“綠線”修建一條“隔離墻”,以防止激進分子向以色列滲透,制造爆炸事件。但此建議遭到以定居者為代表的極右翼的反對,他們主張將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大約150個定居點全部圈入以色列一側,這等于將吞并幾乎所有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領土。后來,由于爆炸事件屢屢發生,讓以色列防不勝防,迫于壓力,沙龍政府終于批準修建“隔離墻”。
記得1998年11月,我們應邀訪問以色列期間,無論是在特拉維夫或耶路撒冷,無論是在公園門口、公共汽車站,或超市的櫥窗里,到處都張貼著提醒發現可疑爆炸物時,撥打預警電話的招貼畫:遠看是一只美女的眼睛,走近了,便發覺那黑色的瞳孔竟是一枚檸檬狀的炸彈!下面有一臺紅色的電話機和報警電話的號碼。那時,人們看見人行道邊的垃圾箱,都遠遠地繞著走,因為好幾起爆炸事件,都是恐怖分子將爆炸物放在垃圾箱中引發的。那次訪問期間,我們曾經遭遇過兩次爆炸事件,兩次都發生在耶路撒冷。一次是中午,以色列外交部兩位副總司長在一家餐館宴請我們,賓主剛剛坐下,附近兩聲沉悶的爆炸震得餐館玻璃門窗都在顫動。我們相互對看一眼,出于禮貌,誰也沒有表示驚詫。主人卻哈哈一笑,說:“在以色列,經常會聽到這種聲音,只當它是搖滾樂吧!”一句幽默,打破了彼此的尷尬。另一次是在晚上,在我們旅館附近的一家餐館用餐,剛進門,身后便響起急促的腳步聲,我們忙閃在一邊,只見幾個治安警察提著沖鋒槍奪門而入。后來被告知是那家餐館接到警告電話,說餐館里有爆炸物。我們只好乘出租車去別的餐館就餐,路上聽陪同說,那警告電話十之八九是惡作劇,但警察局接報后,又不能不派來治安警察和清除爆炸物的專家。
后來,由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沖突急劇升級,一方動輒動用坦克、飛機、大炮,或武裝直升機“定點清除”,一方則用土制火箭、路邊遙控炸彈以至“人體炸彈”還擊。以暴易暴,愈演愈烈。為阻止“人體炸彈”頻繁地從西岸滲入以境,沙龍政府下令加緊“隔離墻”建設。盡管沙龍一再聲稱:“隔離墻’的修建完全是為了安全目的,沒有任何政治上的意義。”然而事實卻沒有那么簡單。從2003年6月開始的第一期工程看,“隔離墻”并非像以色列政府聲稱的那樣沿著“綠線”修建,而是普遍向東延伸到巴勒斯坦地區,有的地方縱深達到6~7公里,將20%左右巴勒斯坦在西岸的土地“圈”入以色列一邊。而且,在修建時恣意砍伐巴勒斯擔人的橄欖樹,搗毀他們的住房、家禽養殖場、牲畜圍欄,或截斷道路、水源,甚至將一些巴勒斯坦村莊直接“圈”入以色列一方,以致使不少巴勒斯坦人處于與外界無法聯系的孤立的“隔離區”內,剝奪了他們生活來源與生存權力,迫使他們不得不搬遷……
巴勒斯擔人把以色列修建的“隔離墻”斥之為“種族主義的隔離墻”,是以“反恐”為籍口,在未經巴方同意,也沒有國際社會參與監督的情況下,以“圈地”方式大肆侵吞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并造成既成事實,最終達到阻止巴勒斯坦建國的目的。阿盟秘書長穆薩強烈譴責以色列這一舉措,認為它是冷戰時期柏林墻的翻版,只會對巴以和平進程產生無可估量的負面影響。2003年年底,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將“隔離墻”問題提交國際法院。國際法院裁定:以色列修建“隔離墻”違反國際法,必須立即停止包括東耶路撒冷及其周圍地區在內的被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與修建“隔離墻”,拆除現已存在的建筑框架,并有義務補償因在被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修建“隔離墻”造成的一切損失。
然而,對聯合國的各項相關決議,以色列都不予置理,對國際法院的裁決,自然更不加理會。
又幾年過去。國際上有關“隔離墻”是是非非的爭執也一直沒有停止過。這次有機會應邀出訪以色列,自然希望見識見識那耗費了近10億美元修建的長達360余公里的“隔離墻”。
我們原以為“隔離墻”只是報刊上看到的8-10米高的預制水泥墻,來以色列后,才知道“隔離墻”因地域不同,也有不同的形式。在居民密集的城鎮,“隔離墻”主要是8-10米高聳的水泥墻,配以壕溝、電網及電子監控設備。而在非居民區,例如我們從瀕臨地中海的古城凱撒尼亞經哈德拉東去,前往拿撒勒途中,從撒馬尼亞山俯瞰圖勒凱爾姆所看到的橫穿西岸北部地區的“隔離墻”,便是一道2-3米高的電網,兩側各有近20米寬的松土地帶,配備電子監控設備與巡邏直升機。這種“隔離墻”在成本上要低于水泥制式的“隔離墻”,由于它遠離村鎮,一旦發現非法潛入者的腳跡,立即循蹤追擊,潛入者同樣難以逃脫。
據同我們座談交流的以色列專家和陪同我們參觀、游覽的導游告訴我們,自從“隔離墻”修建后,以色列安全狀況得到明顯改善,巴勒斯坦激進分子的“人體炸彈”襲擊已經大為減少,由多時每月十幾次下降到年均2-3次的“可接受水平”。1998年我們訪問時,那張幾乎無處不在的提示警惕可疑爆炸物的招貼畫,已經不見蹤影,人們對路邊的垃圾箱也不再神經過敏了。以色列政府也頓感壓力驟減,可以松一口氣了。
然而,“隔離墻”對巴勒斯坦人造成的危害,卻是不爭的事實。就拿我們看到的這一段由電網構筑的“隔離墻”來說,它把一條由加利利地區通往圖勒凱爾姆的公路完全“圈”在以色列境內,巴勒斯坦人無法再使用這條公路了。而地處圖勒凱爾姆四周農墾區的村莊,有大片的橄欖林、果園與農田,是巴勒斯坦經濟與社會最繁榮的地區之一,由于以色列修建“隔離墻”時,強行分割、穿越,將“隔離墻”兩側17-20米內的農村基礎設施,以及果樹、農田恣意搗毀、砍光、犁平,或一股腦兒“圈”入以色列一側。致使大量巴勒斯坦成年人失業和兒童失學,甚至連生病也無處求醫。許多農田、果園由于水井和水渠被“隔離”而荒廢。它所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的嚴重后果,確是難以估量的。
連以色列的媒體與專家、學者也一針見血地指出:“隔離墻”顯然是一道政治墻,是橫亙在實現以巴人民和解道路上的新障礙。與其說是為了反恐,毋寧說是從根本上剝奪巴勒斯坦人建國的權利;耗費幾十億謝克修建和維護“隔離墻”,而讓和平變得遙遙無期是得不償失……
2006年12月15日,第61屆聯合國大會根據即將離任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建議,以壓倒多數通過了就以色列修建“隔離墻”給巴勒斯坦人造成的損失登記造冊的決議。
面對“隔離墻”,人們不能不問:它究竟“隔離”了什么?
兩粒石子
在收到以色列前駐華大使南月明女士贈送的拉賓夫人利婭·拉賓回憶錄《最后的吻》中譯本時,我們正趕寫散文集《走進迦南地》。我們曾準備在這本書出版后,再拜托南月明大使轉贈利婭·拉賓。因為書中不僅收錄了1995年拉賓逝世時,我們在開羅寫的《受命打通“地獄之門”的人》,還收錄了我在1998年再訪以色列后寫的紀念拉賓的《讓太陽升起》……
不料就在散文集編成將行付梓時,竟傳來利婭·拉賓病逝的噩耗。我們不得不懷著悲痛,補寫了一篇《愿逝者永恒》。在這篇文章的結尾,我們寫道:
利婭·拉賓的回憶錄《最后的吻》的封底上,有一幀彩色照片:利婭獨自坐在拉賓的墓石上,背靠著黑色的碑石,就像倚著拉賓強有力的臂膀。碑石上放著一粒粒前來拜謁者祝福逝者永恒的小石子。如果有一天,我們再去以色列,一定去赫茨爾山,把兩粒北京帶去的小石子,輕輕地放在他們黑白兩色的碑石上……
吊唁者將一粒粒小石子放在逝者墓上或碑石上,表達對逝者的緬懷與祝福,是猶太人的習俗。這源于《圣經》上的律條:不得用活物(包括鮮花)祭奠死者。我們本著“入鄉隨俗”的理念,用猶太人祭掃的方式,只為表達我們對逝者的敬重。
這次應邀訪問以色列之前,我特意在北京我們居住的小區里,揀了一粒自的、一粒黑的兩粒小石子,行前仔細地用小塑料袋裝好,放在貼胸的衣袋里,帶到以色列,帶到赫茨爾山。
赫茨爾山在耶路撒冷西部,距猶太人大屠殺博物館亞德瓦謝姆不遠。這里是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倡導、與實踐者西奧多·赫茨爾的長眠之地。1896年他出版的專著《猶太國》,為后來以色列國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他也被猶太人公認為以色列建國之父和“新時代的摩西”。遺憾的是,他也像摩西一樣,率領百十萬奴隸走出埃及,在西奈半島的沙漠中盤亙40年,終于將他們引領到耶和華應允給他們先祖的“迦南地”,自己卻未能走進。赫茨爾抱病為實現猶太復國主義理想苦苦探求,在終于看到一線曙光的時候,卻被病魔奪去了生命。他在遺囑中要求把他埋葬在維也納他父親身邊,“直到猶太人民把我的遺骸送到巴勒斯坦”。1949年,猶太國——以色列建國第二年,猶太人民終于按照赫茨爾的遺愿,將他的遺骸從維也納遷到以色列,隆重地安葬在耶路撒冷最高的山頂上,這座山也因之易名為赫茨爾山。
我們是在參觀完猶太人大屠殺博物館后,來赫茨爾山瞻仰拉賓夫婦陵墓的。汽車沿著蜿蜒曲折的山路向山頂駛去,路邊是排列整齊的大片的墓地,凱姆博士介紹說,這里長眠的是歷次中東戰爭中陣亡的官兵。車在一個小停車場下,我們步行走過以色列著名人士與政府要員的墓地,從一塊塊并排平躺著的墓石上鐫刻的姓名,可以知道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澤耶夫·亞博廷斯基,“六五戰爭”時的首相列維·艾希科爾,以及以色列老資格的女政治家、前總理果爾達·梅厄夫人等等都長眠在這里。盡管他們生前社會地位十分顯赫,但他們的墓地卻都非常簡樸,沒有歐洲陵園里常見的華麗的雕像與裝飾。這大約也緣于《圣經·創世記》所云:“你本是泥土,仍要歸于泥土”。以及猶太人不得崇拜偶像,不得向偶像跪拜的宗教理念。
同以色列其他政要的陵墓相比,拉賓夫婦的陵墓便顯得氣派多了。它在赫茨爾山的一個小山頂上,白色玄武巖的墓石上有一座十分獨特的墓碑,是他們的朋友、以色列著名的建筑師摩西·薩法戴設計的:約一米見方的一黑一白兩塊厚重的玄武巖并放在一起,正面鏤空的倒置的圓錐體使黑白碑石組成一個大寫的V字。黑、白碑石上用希伯萊文分別鐫刻著伊扎克·拉賓夫婦的名字,下面有一個圓形的燃點長明火炬的石甕。墓碑造型簡潔、凝重,肅穆、莊嚴,據說黑色代表剛毅,白色代表純潔,象征著拉賓夫婦的精神與人格。
我們來到墓前,我踏著石階,將從北京帶來的兩粒石子,恭恭敬敬地放在黑白兩色的墓碑上。
我默默地站在墓前,望著黑白兩色的碑石,百感交集。拉賓是在1995年11月4日夜晚,在特拉維夫市中心廣場(后易名拉賓廣場)上舉行的一次有十萬人參加的和平集會上,被一名極右翼的猶太青年刺殺身亡的,迄今已經整整11年了。利婭·拉賓在《最后的吻》中,面對當時的以巴和中東局勢,就曾不無遺憾地說:“現狀簡直讓伊扎克在墓中不得安生……”如今又幾年過去,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伊拉克戰爭之后,無論是巴格達、加沙、約旦河西岸,或黎以邊界以至整個中東,無不是沖突迭起,亂象叢生!拉賓為之付出鮮血與生命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中東和平,非但沒有實現,反而更加遙不可及。誰來繼承拉賓的“和平遺愿”,高擎起他的和平火炬呢?連日的研討、座談會上,這也是專家、學者們絞盡腦汁,也未能解答的議題。
但我聽說,半個月前,拉賓遇刺11周年的晚上,十萬以色列民眾依舊自發地匯集在特拉維夫的拉賓廣場,舉著燭光,默默悼念這位高擎和平火炬的偉人。他點燃的和平之火,依舊在他們心中熊熊燃燒。
就在我們準備離開拉賓夫婦的墓園時,忽然來了一群以色列青年軍人,他們是結束休假返回軍營之前,相約來這里憑吊他們心中的這對偉人的。看著他們,我沉甸甸的心緒不禁釋然了。我想,拉賓點燃的和平火炬是不會熄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