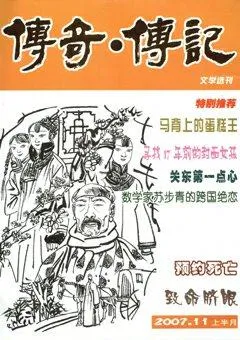蟋蟀斗
民國十年,德州金牛灣珠寶行門口,掛出一張海報,上書:立秋時節,金牛灣屆時將舉辦一場蟋蟀斗,地點設在泊秋堂,尊請各路英雄齊聚,共搏一尊金圣手佛。
海報貼出沒多久,民眾爭相傳閱。蟋蟀斗雖不新鮮,但有組織的蟋蟀斗,在德州鮮有。掌心寶中有玩物的各家早已按捺不住內心的竊喜。
人堆里,少年寒纖讀閱那張海報后,當下數了指頭,離立秋還有九天光景,他便把鴨舌帽放低,擠出人群,徑直來到惠澤藥堂門口,藥堂老板商子雄正在噼里啪啦地打黑珠子算盤,猛一抬頭,見寒纖在藥堂外徘徊,便支過小徒,把寒纖叫進藥堂來。
“怎么?你娘的病還不見好轉嗎?”商老板停住手中的活,看著少年寒纖問道。
寒纖把帽子拿在手上,謹慎地回說:“回商老板,病稍有好轉,昨兒已把最后一帖藥煎了。”說完臉紅地低下頭來。
商子雄當即明白他的話,怕是沒錢拿藥。商子雄吩咐小徒,照前幾次的藥方,拿了幾帖藥。寒纖感恩戴德,說一定報答商老板的恩情,這藥錢他會還的。
回到家中,熬了藥,端上一熱碗,侍候著母親賀氏喝下后,寒纖便拿過書柜里的一本發黃的小冊子。
賀氏咳嗽數聲,問:“纖兒,你又在讀你爹留下的孤本了?”寒纖掩上卷本說:“金牛灣將于立秋在泊秋堂舉辦一場蟋蟀斗,贏者可得一尊金圣手佛!娘,我一定要找到爹記載的赤弓。”賀氏搖頭道:“真是家門不幸,纖兒,難道你不記得當年你爹是怎么死的嗎?”
賀氏的丈夫寒子賓當年酷愛養斗蟋蟀,終因玩物喪志,在一次泅水渡過德州河對岸去捕一只戰神赤弓時,被連日來洶涌的河水沖走,淹死在德州河里,那年寒纖才三歲。寒子賓雖沉迷于蓄養蟋蟀,卻也頗有心機,寫下一本《戰神記》,書中詳寫了如何培養蟋蟀戰神。當年寒子賓有個朋友,便是藥堂老板商子雄,寒子賓蓄養蟋蟀所食的餌料,皆通過藥堂而來。寒子賓從藥堂購得幾味藥材,配成蟋蟀最好的食物,食量精,食后能助筋力,翅翼锃亮,鳴聲清脆飽滿。只可惜寒子賓出師未捷身先死,現此孤本正拿在少年寒纖的手上。
依據書中記載,戰神赤弓出沒之地,須取背陰的瓜果園地,在殘棄的瓦楞片羽下。德州河對岸便是記載曾捕獲三只赤弓之地,只是如今要到河對岸無需再泅水,自有一獨木橋可供行走。寒纖肩背柳條編織的蟈蟈籠,走上獨木橋,來到這片家父曾經掘伏蟋蟀之地。
由于對蟋蟀天生的好感,寒纖的鼻子特別靈敏,小小生靈翅翼間所散發出來的氣息,指引著寒纖的手觸去。踩踏在散亂的青苔瓦楞間,寒纖已擎捉數只蟋蟀,可惜這幾只仍只是平平之輩,啼音欠缺力度和柔韌度,身上的斑紋雖染有赤色,然粗劣曲直,并非戰神赤弓,他一一放走了。
待到一輪淺月出現在天上,夏末的晚風吹過德州河,涼氣漸來。寒纖懷抱蟈蟈籠,靠在一枚頑石邊上,看淺月迷朦。他在苦等月下赤弓的出沒。
地畔處,有一聲嘹亮的蟋蟀鳴聲響起,特別雄渾有力。只一聲,就隱遁了。寒纖專等著那廝再啼一聲,可是久等,卻沒有下文。
赤弓在未進入蟈蟈籠之前,屬于烈性一族,并不是好捕捉的,只有一次機會,所以要瞅準時機,一旦入蟈蟈籠,赤弓即刻會卸去雄威,偃旗息鼓,要待到主人給它喂過三頓食后,才漸漸回升斗志。
月下德州河,靜得幾乎聽到河水流淌聲,猛一抬頭,德州河上有個泅水之人,上得岸來,奇怪的是此人衣物并沒有濕掉。在月下,略可看清此人穿一襲青衫,戴的也是一頂鴨舌帽,手上提一盞蟈蟈籠模樣的橘子燈,腰間卻別有一桿小竹竿,竹竿尾掛吊一個真正的蟈蟈籠,悠悠地晃。
寒纖正欲與此人對話,卻見來人笑笑對寒纖低語道:“你也是來捉蟈蟈玩兒的嗎?”寒纖點了點頭,放開了懷中緊抱的蟈蟈籠。
“那跟我來吧!”來人輕提手中的橘子燈籠,在前面引路。寒纖也只好起身,尾隨其后,來人提燈停住的角落正是剛才寒纖聞得嘹亮啼鳴音的所在。來人遞過橘子燈,讓寒纖提著,自個兒卻掘伏在地,面前是一撮青草掩映下的一片墨瓦。月光下,墨瓦黑得如一口深井。
來人的手似有魔力,中指在墨瓦上輕輕一敲,墨瓦竟然陷下去一個圓孔,說時遲,那時快,來人腰間的蟈蟈籠不知何時已安放在那片漏瓦孔上,卻聽蹭的一聲,有物從漏孔蹭入籠中,來人輕輕反轉蟈蟈籠,蓋好籠蓋子。
“這招真神!”寒纖心內卻惋惜呀,畢竟好貨讓陌生人給逮走了。
來人卻笑道:“非也,這只是損招,非絕招,你見過釣赤弓入甕的嗎?可惜這月色比我這橘子燈還慘淡,不然,再與你釣上一只赤弓。烏云將至,要興風雨了,小兄弟你還是先回去吧,與你相識一場,這只籠中赤弓就與你當個見面禮。”說完,遞過蟈蟈籠來,獨個兒提著橘子燈走向原路……
寒纖抬頭望天,陰云密布,陰風漸起,前面不遠處,提橘子燈之人,越行越遠,見那燈光消失在德州河上。
寒纖起身往家趕,行走在獨木橋上,卻未見德州河上有橘子燈光,只見閃電騎著野馬在天空狂舞,煞是嚇人。心內卻暗想,剛剛那人真是奇怪,有橋不走,還泅水而渡,實在木呆。
推門而入,見賀氏未曾睡下,正靠在床幃上,翻一本書。
“娘,你怎么沒睡,藥呢,我去煎藥。”寒纖掩藏好蟈蟈籠子,忙著去煎藥。
賀氏道:“纖兒,我做了個夢,你爹說托人幫你找到一只赤弓,讓你好生蓄養,這本書還給你,娘想通了,何事都有個度,只要你掌握好這個度,仍會是一個有作為之人。”
寒纖呆愣住了,趴在賀氏的懷中哭了起來,任委屈的淚水奔泄而下。
隔日,天晴,寒纖到惠澤藥堂賒得幾味藥材,配成精飼,飼與籠中蟋蟀,三頓后,見籠中果真伏著一只赤弓,蟋身周體強健,赤色飽滿,翅翼锃亮,觸須堅韌,翼鞘所發之聲實在是嘹亮。
依據《戰神記》記載,寒纖定時給赤弓彈羽,用一根極細微的棕蓑衣毛挑馴角逐,九日時間很快就過去,轉眼立秋也就來了。
泊秋堂門口,眾人擁出金牛灣珠寶行老板金晉顏來,各人依序在泊秋堂英雄棧領了斗勇招牌,招牌是一枚星樣,上有蟋蟀品種及個塊身重諸品項。擁擠的廳堂,粗略算了一下領到招牌的玩家,應在六十位之上。寒纖算是最文弱的一員,戴著鴨舌帽,手中捧著黑瓦陶罐。
金老板放話了:“今日斗膽在此,引各路豪杰亮家底,旨在對德州玩蟋蟀之風的懷舊,另以一尊金圣手佛當為禮資,獎給優勝者,也算是老朽生日之一大盛事!”原來今日是金老板的六十大壽。
泊秋堂的英雄棧共設五個賽席,席位分別取名金木水火土,賽席上各放一個金盥。每個席位分得十余張招牌,各人先組成兩兩相斗之勢。
寒纖分在木席,木席的金盥內,瞬間落下二只蟋蟀來。甲乙玩家所養的蟋蟀懸殊奇大,甲玩家的蟋蟀黑色,身壯體肥,乙玩家的則略顯小了些,卻顯得精悍驃勇。金盥內,二個黑點各占一局點,當兩蟲觸須相碰,即見發威,張牙怒發,立即廝咬,沒幾個回合,小的竟然勝了大的。甲主人只好收了殘局,撤出金盥來。
寒纖見到金席上有張熟悉的面孔——正是惠澤藥店的商子雄。商子雄也看見了寒纖,特意向寒纖點了點頭。商子雄的手中,有個碧瓦陶罐,料想是家寶了。
各席廝殺得正酣,金老板依席巡視,并沒有真正讓他耳目一亮的一品蟋蟀出現。
待殺到午時,再看金木水火土各席,才分得眉目出來,金席惟剩商子雄的黑龍,木席上也惟剩下寒纖的赤弓,另有火席上陳老板的劍煞勝出,土席上一位八旬老者的射日勝出,水席上的沒有贏家,蟋蟀雙雙戰殘金盥內,實是悲壯矣。
午時休息一刻鐘,讓各方家的王者養精蓄銳,英雄棧便引一女子,坐在聽音堂為眾人彈撥起古箏來。
這時,金老板命伙計端出一紅絲綢蓋著的托盤來,眾人的目光牽引至此,都明白此物定是金圣手佛了。何謂金圣手佛,乃是金佛一尊,一直是金牛灣最有品味的一尊金佛像,佛拈千指,氣定有神,普渡眾生,境界非凡。
金老板親自揭開蓋在金圣手佛上的紅絲綢,英雄棧頓時明光四射。
接下來,眾人屏住呼吸,卻見黑龍勇斗劍煞,赤弓伏降射日,于金盥內,翻江倒海,掀起嘶鳴滿盥。
“精彩!實在精彩!”陳老板明知他的劍煞已斷脊折翼卻不禁為商子雄的黑龍喝彩,看來黑龍的表現絕佳。
八旬老者冷汗直冒,料不到他久經沙場的射日一遇到赤弓,蔫了。
金老板叼著煙斗走出廳堂,眾人明白,最精彩的較量來到了。只剩二個名角了,便是商子雄的黑龍,寒纖的赤弓。五個金盥早已收攏在一起,換了一個更大的金盥當戰場,锃亮如新。
“商老板,我……”寒纖結舌道。商子雄把寒纖的鴨舌帽戴正,低下頭耳語道:“其實緬懷子賓兄最好的方式就是這場決斗,不論你贏抑或我贏!”
但是,局勢的發展卻有點始料不及,風卷殘云,不過如此,赤弓雖勇,卻敵不過黑龍一翼遮天。赤弓妥協地躲在一邊喘氣,這不是寒纖要的結局。寒纖呆愣住,耳邊卻猶自響起商子雄的話:“其實,我早知會贏你,這秘訣就在藥材的配方上!”原來,商子雄給寒纖幾味藥材,分明少了一味,使赤弓無法支撐到最后。
寒纖悲憤之際,猛地憶起家父《戰神記》中,隱有記載,如若斗蟲頹靡,遇熱血可復發血性。寒纖惡盯住金盥內,突然胸中難受,果真噴出一口熱血來,一滴灑在赤弓身上,那廝卻立馬還魂似的驚覺起來,再扯觸須,猶掛戰旗,張牙怒發。黑龍沒料到赤弓來一招惡地反撲,正自鳴得意,卻被赤弓硬折下一支翅翼來,被咬得暈頭轉向,斷肢缺牙,戰神赤弓則昂頭舞須高鳴不已。
商子雄臉上的烏云驟然襲來,沒辦法,殘局已定,勝者當屬赤弓。
金老板捧出金圣手佛來,不禁嘆道:“蟋蟀‘鳴不失時’,所以謂信;‘遇敵必斗’,所以謂勇;‘折肢斷筋,守死疆場’,所以謂忠;‘寒則歸宇’,所以謂識時;‘敗則不鳴’,所以謂知恥。此乃蟋蟀之五德也!”
眾人鼓起掌來,包括商子雄,只是臉上漸泛慚愧之色。
〔責任編輯 徐 卉〕
〔原載《三月三》總第278期〕